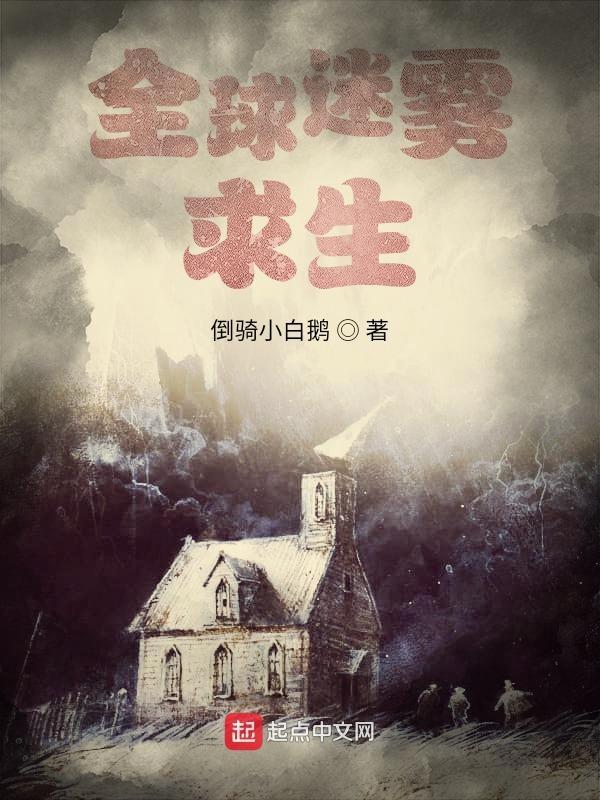奇书网>活着就是恶心原文 > 林娜 被训练的微笑(第6页)
林娜 被训练的微笑(第6页)
老人微微笑:“信善就好,比信神管用。”
那句话像一根针,扎进她心里。从那天起,她开始每天给病人擦手、剪指甲,甚至为那些无人探视的病人留一盏灯。有人说她多事,她笑笑:“我不信报应,但信被看见。”
疫情中,她见了太多生死。有人死在呼吸机上,有人痊愈后给她塞红包。她都一一拒绝,只留下那句:“活着就好。”
顾行之在2021年春回到兰河。他的研究课题从“伦理学与他者”延伸到“灾难中的道德经验”。他再次找到林娜,希望采访她关于疫情的经历。
那天,他们坐在医院外的长椅上。阳光很淡,风吹着树影。顾问她:“你害怕死亡吗?”
她说:“怕。但怕过几次之后,就不怕了。死,其实没那么吓人,虚假的活才可怕。”
顾沉默。她又说:“你研究人性,我活在人性里。以前我说这句话是炫耀,现在我明白了,人性有时候脏、有时候亮,但总要有人看它一眼。”
顾写下这句话,后来把它作为章节的标题。
那年冬天,林娜被安排照顾一个重症病人——一个中年男子,瘦得像被掏空。病人几乎不说话,只在夜里低声问:“我是不是要死了?”
她安慰:“不会,明天会好。”
病人苦笑:“你也学那一套?”
她愣住。
“我以前也是做保险的。”病人喘息着说,“后来全赔光了。我以为我卖的是保障,其实卖的是幻觉。”
林娜沉默了很久,说:“我也是。”
病人看着她:“那我们算同业。”
两人相视而笑,那笑有种奇异的温柔。
病人死在两天后。她在走廊上等遗体车时,心里涌起一种莫名的平静。她想,也许他比自己先得到了解脱。
2022年春天,城市逐渐恢复。她搬回老城区,租了一个十几平的小屋。每天早上去市场买菜,傍晚在巷口晒衣服。偶尔邻居喊她去帮忙量血压,她就带着旧听诊器跑过去。那听诊器是她做护士时留下的,她擦得很亮。
她不再上网,不再看理财广告,也不再看所谓的励志短视频。晚上,她读些旧书:《论语》《尼采》《海明威》。有时看得困了,就靠在窗边睡去。梦里,她常梦见母亲在院子里晒被子,阳光透过棉布,是温的。
那年夏天,顾行之的新书出版——《他者的回声:灾难中的伦理》。他寄给林娜一本,扉页上写着:“致林娜,一个教我理解希望的人。”
她翻开书,看到一段文字:
“希望不是商品,不是信仰,而是一种静默的行动。它存在于那些无声的照料、那些被忽视的手势之中——那是人类最真实的伦理。”
她合上书,心里一阵发热。
2023年的秋天,她在医院门口等公交。车没来,天边的夕阳像血一样,风吹得人想哭。她忽然看见一个年轻女孩走过来,穿着职业套装、拿着宣传单。女孩笑着说:“阿姨,买保险吗?理财型的,收益高。”
她愣了几秒,笑着摇头:“谢谢,不用了。”
女孩递给她一张单页,她接过,看了一眼,笑容僵在脸上——那公司的LOGO,是她当年离开的那家。
她看着那女孩,忽然想起自己二十多岁时的样子,笑容同样被训练得完美。她轻声说:“姑娘,路不好走,别把笑全用在工作上。”
女孩没听懂,点点头走了。
林娜站在原地,手里的传单被风吹走。她抬头望天,那一刻,夕阳照在她的脸上,皱纹清晰,却柔和得像一片旧纸。
她忽然想起顾行之在采访时说的那句话:“有时候,伦理不是选择,而是坚持。”
她轻声回应:“我在坚持啊。”
夜色降临,她慢慢走回那间狭小的出租屋。路过一家理发店,玻璃门反出她的倒影。那笑容淡淡的,没有被训练过,也没有表演的痕迹。她对着玻璃轻轻说:
“这次,我的笑是真的。”
她走进夜色,街灯一盏一盏亮起。
风吹过她的发梢,吹过她走过的那几十年——
从理发店到洗头房,从讲台到病房,从虚假的希望到真实的照料。
她的命运,像这城市的灯,一度闪烁,一度熄灭,却仍顽强地亮着。
林娜不知道未来还会怎样,但她终于明白了一件事:
人的尊严,不在于被看见的光,而在于在黑暗中仍能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