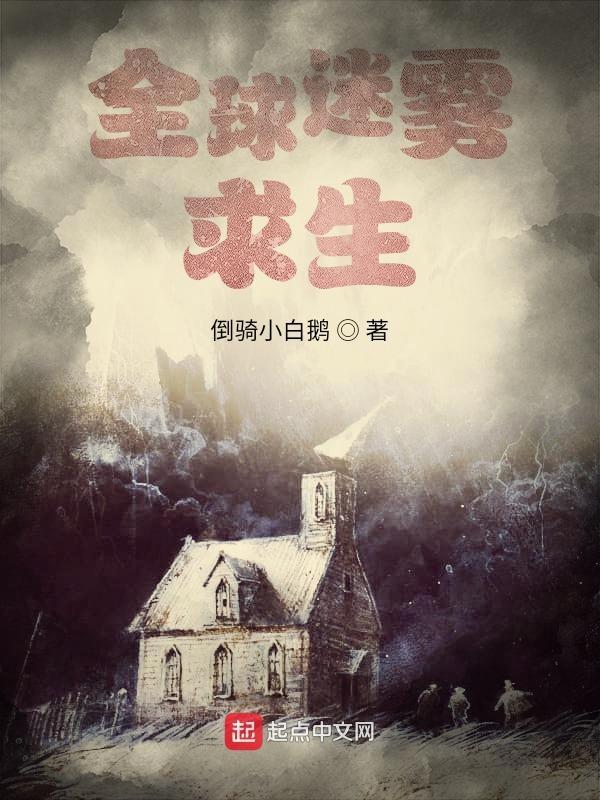奇书网>活着电影免费观看完整版 > 韩建国 城市的听众(第6页)
韩建国 城市的听众(第6页)
“你怎么形容夜里的兰河?”我问。
“像一台大洗衣机。”他笑,“把每个人的衣服扔进去。失业青年的帽子、陪酒女的口罩、骑手的手套、病人家属的被子、老人的钥匙、保洁员的围巾……机器转一夜,到了早上,把衣服拎出来晾一晾,白天的人就可以穿着去生活。只有我们这些守夜的人,知道衣服上那些洗不掉的印子。”
他把收音机重新打开,另一首老歌响起。歌词简单,反复唱“别问我从哪里来”。
“顾老师,你觉得你写这么多——有用吗?”
“有些人读到,也许能在某个夜里听见自己。”
“那就够了。”他说,“我当二十多年听众,也想当一次扩音器。”
太阳像被谁轻轻推了一把,从桥的边缘升出来。我们把车停在黄河东路的尽头。
“睡两小时,再接早高峰。”韩建国说,“活着就是两头接:夜里接沉默,白天接喧哗。”
他把车窗摇下一半,风把烟味吹散,车里只剩录音机细小的磁带声。那声音像一条小小的河,在更大的河边慢慢流。
我关掉录音机,合上笔记本。
在这个城市里,凌晨的乘客一个接一个地离开车门,却把他们的呼吸留在了我和韩建国的记忆里。
我忽然想起那个失业青年说的——“我怕去的地方一直在换名字。”
是的,地方在换名字,行业在换规则,人在换面具,只有“活着”这个词,不换。
“师傅,回头见。”我说。
“顾老师,回头见。”他冲我摆摆手,像一个一直在路口执勤的老兵。
车离开时,我看见他在后视镜里扭头,看了一眼黄河。那一眼里,包含了他这二十多年听过的所有故事——失业、陪酒、送餐、住院、独居、清扫、抽成、直播、沉默与爱。
他像城市的耳朵,而我不过是把耳朵里积攒的风吹进纸上。
天亮了,夜里的喘息渐渐退去。
但我知道,它们不会消失,只是换了地方继续——换到工地、写字楼、手术室、直播间、保安亭、辅导班、快递柜和每一辆起步的出租车上。
它们等着下一次寂静,把“活着不易”这件事,重新说一遍。
(三)白日的影子
天亮得很快。五点半的黄河东路像是被谁泼了一桶淡白的水,风一吹,街面上便起了微尘。韩建国趴在方向盘上眯了二十分钟,闹钟一响,他抖抖肩,发动引擎。收音机播着早新闻,语调匆忙:“今日兰河最高气温二十九度,房地产政策调整——”
“又调了。”他嘀咕,“昨天的风还没吹干,今天的楼价又湿了。”
太阳升起时,街头的影子开始变硬。白天的城市,比夜晚更像一张紧绷的网——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格子里努力呼吸。韩建国习惯在早上跑一波“早高峰”,他说那是“人间最密集的时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办公楼的乘客:程序之外的生活
七点整,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从街边咖啡店跑出来,一边系领带一边喊:“师傅!去省发改厅!”
他坐进车里,立刻掏出电脑,开始打电话:“老刘,方案改成‘优化民生结构’,别写‘削减支出’——听起来不好听。”
韩建国透过后视镜看他,忍不住问:“你们天天改这些字,有意义吗?”
“意义?当然有啊。”青年笑得机械,“写错了就会有人丢饭碗。我们叫‘文字救国’。”
电话一通接一通。到达单位门口时,他从钱包掏出两张票子,又塞回去,改用扫码。
“现金看着脏。”他说,“扫码干净。”
下车时他顺口问:“师傅,你跑了多少年?”
“二十多年。”
“真不容易啊。”年轻人叹一声,“我爸也是出租车司机。他总说‘要懂规矩’,结果老了,车报废,人也报废。我不想那样。”
他合上电脑,冲门卫微笑。
韩建国目送他进门,喃喃道:“现在的人比我们更懂规矩,可规矩也更会吃人。”
我在后座做笔记:
“程序之外,不再有生活;语言之内,不再有真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