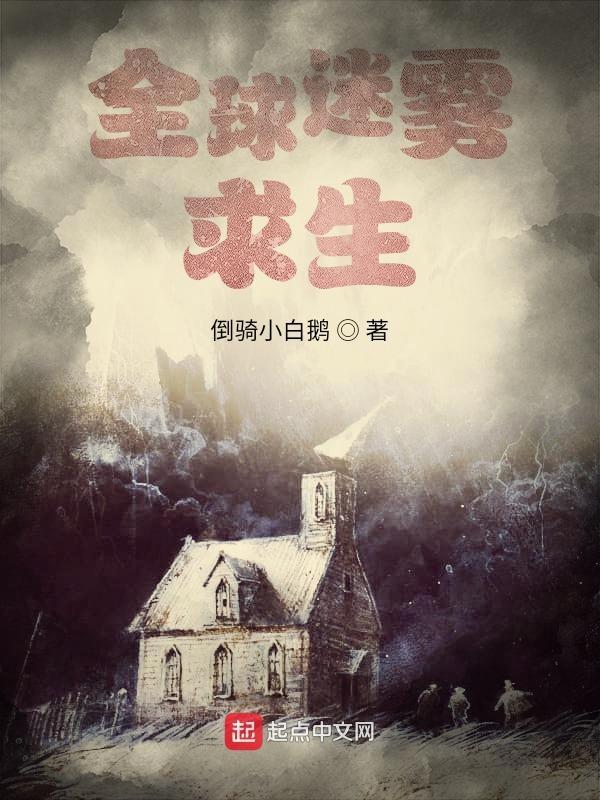奇书网>80年代创业忙momocha > 织网伊始(第1页)
织网伊始(第1页)
回到第三机床厂,许蔓华没有急着去工会汇报,而是先将自己反锁在借用的杂物间里。她摊开本子,将这次物资交流会的所见所闻、买到的信息、预定的鞋底、以及苏晓梅这个名字,仔仔细细地记录下来。
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脑海中的思路也越来越清晰。
苏晓梅提供的,是点状的信息。而她许蔓华要做的,是将这些点,与自己已有的渠道连接起来,织成一张网。
她首先处理鞋底的事情。拿着预定单据和从苏晓梅那里得到的橡胶三厂联系方式,她找到李大姐,详细汇报了此次“调研”的“成果”。
“李大姐,这次去交流会,收获很大!我了解到红旗砖窑厂急需耐磨鞋底,工人们现在穿的布鞋太不顶用了。正好,市区橡胶三厂有一批计划外的次品鞋底要处理,价格非常划算!我就想着,这不正好又能帮砖窑厂解决困难,又能帮橡胶厂消化库存吗?就用咱们的经费预付了定金,预定了一百双。”她将过程描述得顺理成章,重点突出“解决困难”和“价格划算”,弱化了自己主动搜寻和谈判的行为。
李大姐拿着单据,有些惊讶于许蔓华的效率和胆量,但听到价格确实远低于市场价,又能给工会工作添彩,便也点头支持:“行,蔓华,你考虑得很周到!这事你跟进好,等货到了,还是按老规矩,跟砖窑厂那边对接。”
第一步顺利。这意味着,她通过“工会互助”这个平台,成功地进行了一次跨区域的、非本厂积压品的资源匹配。虽然利润依旧微薄(差价会进入工会账户,她个人只有少量补贴),但模式验证成功!
接下来,是关键的一步:联系苏晓梅。
周末,她按照记忆中苏晓梅留下的模糊地址,找到了市郊一片低矮的平房区。几经打听,才在一个狭窄的胡同尽头,找到了苏晓梅的家。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昏暗潮湿,除了一张床、一个旧桌子和几个装满了笔记本的破箱子,几乎家徒四壁。
苏晓梅对于许蔓华的到来有些意外,但脸上依旧是那副疏离的平静。
“苏晓梅同志,冒昧打扰。”许蔓华开门见山,“上次在交流会,你的信息服务帮了我大忙。这次来,是想和你谈谈合作的可能。”
“合作?”苏晓梅挑了挑眉,示意她坐下(屋里只有一张凳子)。
“对。你收集信息的能力很强,但我发现,你的信息大多集中在这次交流会和一些零散的厂矿。覆盖面还可以更广,信息也可以更深。”许蔓华看着她的眼睛,真诚地说,“而我,有第三机床厂工会这个平台,可以接触到更多稳定的需求和供应渠道,尤其是机械配件、原材料这方面。但我们缺乏系统化的信息搜集和整理。”
苏晓梅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她,等待下文。
“我想,我们可以合作。”许蔓华抛出构想,“你负责更广泛、更深入地搜集信息,不仅仅是积压物资,还包括各厂的生产能力、潜在需求、甚至一些政策动向。我负责利用平台进行对接和落地。收益我们可以分成。”
这是许蔓华能想到的,在当前约束下,最能调动苏晓梅积极性,也能最大限度为自己(间接)创造价值的方式。她无法给苏晓梅发工资,但分成模式,可以将苏晓梅的利益与“互助”项目的规模和成功率绑定。
苏晓梅沉吟了片刻。她是个极其理性的人,许蔓华的提议,显然比她自己单打独斗、在交流会摆摊更有前景和稳定性。
“怎么分成?”她问到了核心。
“信息由你提供,对接和协调由我负责。最终促成‘互助’后,产生的‘差价’或者‘服务费’(进入工会账户前,我们私下协商一个比例),你我三七分。你三,我七。”许蔓华给出了一个经过思考的方案。她需要拿大头,因为她承担了平台风险、沟通成本和后续的协调工作。
苏晓梅飞快地心算了一下。这比她自己卖信息一次五毛一块要划算得多,如果能促成大宗交易,收益可观。
“四六。我四,你六。”她还价,“而且,我需要预支一部分钱,买纸笔,还有去外地搜集信息的车费。”她指了指自己窘迫的环境,毫不掩饰自己的经济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