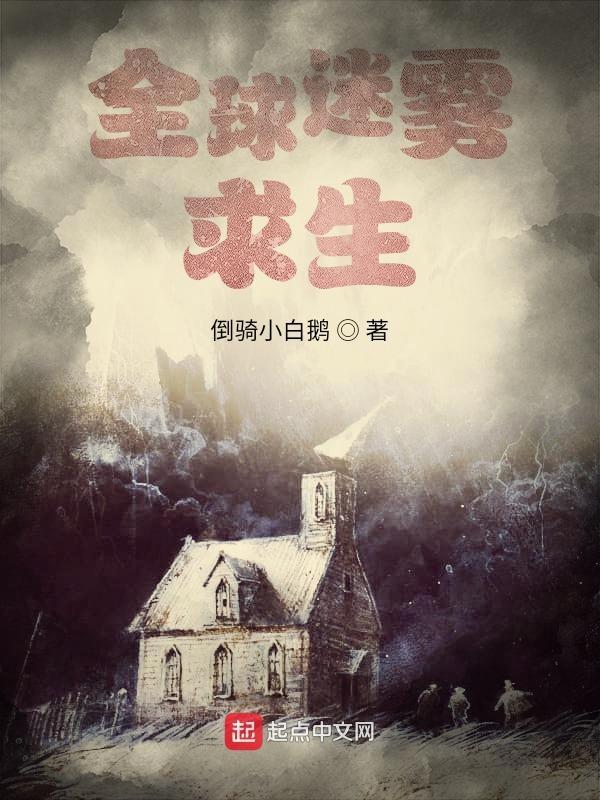奇书网>诗集传序 > 詩序02(第1页)
詩序02(第1页)
詩序02
【纂疏】孔氏曰:「魯桓十一年,祭仲立突而忽奔衛,一爭也。十五年,突使祭仲壻雍纠殺祭仲,仲知之,殺雍纠,突出奔蔡,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高渠彌弑忽而立公子亹,是三爭也。十八年,齊人殺子亹、高渠彌,祭仲逆子儀於陳而立之,是四爭也。魯莊公十四年,傅瑕殺子儀而納突,是五爭也。」先生《初解》曰:「五爭首尾二十年。」姑備參考。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東萊呂氏曰:「『君之澤不下流』,廼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附益之。」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風大行,莫之能救焉。鄭俗**亂,乃其風聲氣習流傳已久,不為「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也。
齊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豈亦以謚惡而得之歟?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同上。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奔,不能以禮化也。此男女**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其曰「君臣失道」者,尤無所謂。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挈,縣挈之名。壺,盛水器。蓋置壺浮箭,以為晝夜之節也。漏刻不明,固可以見其無政,然所以「興居無節,號令不時」,則未必皆挈壺氏之罪也。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此《序》據《春秋》經傳為文,說見本篇。
【纂疏】孔氏曰:「襄公諸兒,僖公祿甫子。」鄭氏曰:「襄公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劉濟曰:「《春秋》桓三年書夫人至自齊,十八年公與夫人如齊,莊元年夫人遜于齊,二年、四年、五年、七年皆書夫人會齊侯,大夫執鴈,知去就為義,宜其去而不顧也。」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未見其為襄公之詩。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義與《還》同,《序》說非是。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亂,為二國患焉。「桓」當作「莊」。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播其惡於萬民焉。此亦刺文姜之詩。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此《序》得之。
魏
《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此未必為其君而作。崔靈恩《集注》「其君」作「君子」,義雖稍通,然未必《序》者之本意也。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國小而迫」、「日以侵削」者得之,餘非是。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國削,則其民隨之,《序》文殊無理,其說己見本篇矣。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禄,君子不得進仕爾。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餐,《序》言「刺貪」,失其旨矣[43]。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此亦託於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辭,未必直以碩鼠比其君也。
【纂疏】孔氏曰:「蠶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猶重斂[44],漸漸以税,使民困也[45]。」《解頤新語》曰:「蠶食喻重斂者,莫切於此。鼠食物且食且驚,四顧不寧,喻貪畏者莫切於此。」
唐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河東地瘠民貧,風俗勤儉,乃其風土氣習有以使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可知矣。《序》所謂「儉不中禮」固當有之,但所謂「刺僖公」者,蓋特以謚得之。而所謂「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者,又與詩意正相反耳。況古今風俗之變,常必由儉以入奢,而其變之漸,又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於初,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尤恐其無是理也。獨其「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者為得之。然其所以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者,又初不為此也。
【附錄】唐自是晉未改國號時國名[46],自作《序》者以為刺僖公,便牽合謂『此晉也而謂之唐,乃有堯之遺風』,本意豈因此而謂之唐?是皆鑿說。賀孫。
【纂疏】鄭氏曰:「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楊氏曰:「晉之為晉久矣,風俗之成非一日之積,《蟋蟀》之詩,風之變也。《左氏傳》曰:『季札觀周樂歌,至於歌《唐風》,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深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此詩蓋以答《蟋蟀》之意而寬其憂,非臣子所得施於君父者。《序》說大誤。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詩文明白,《序》說不誤。
【纂疏】東萊引先生《初解》:按《左傳》《史記》,晉穆侯之太子曰仇,其弟曰成師。穆侯薨,仇立,是為文侯。文侯薨,昭侯立,封成師於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本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成師卒,謚曰桓叔。《左》惠二十四年,晉封桓叔于曲沃;惠三十年,晉潘父弑昭公,迎桓叔,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此可以見國人之心也。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