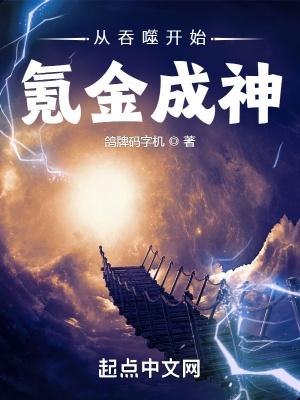奇书网>唐代史学转型 > 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1(第1页)
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1(第1页)
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1]
唐代有两部历史著作在中国史学史上极负盛名,一是刘知幾(661—721年)所撰的《史通》,一是杜佑(735—812年)所撰的《通典》。《史通》着意于对史学活动的反省,意在做出评论和总结;《通典》则注重于沟通史学与社会的联系,意在推动史学的经世致用。刘知幾和杜佑分别生活在唐盛世和唐中叶,他们的历史撰述以不同的风貌和成就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特点。本文仅就《通典》的方法和旨趣做初步的分析,不当之处,祈请学术界同志批评指正。
一
杜佑的《通典》跟它以前的历史著作比较,在史学方法上有很大的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和逻辑的一致。
恩格斯在讲到对经济学的批判时指出,“逻辑的研究方式”实际上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二者是一致的。他说: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2]
恩格斯在这里所阐明的,是历史发展和人类思想进程的一致性的原则。然而,就历史家个人(当然,也包括其他任何个人)来说,其认识能力究竟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反映客观的“历史过程”,则是千差万别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歧异,对历史上思想资料积累和继承的多寡,以及对现实生活经验的总结和吸收的程度,等等,都可能造成这种差别。这种差别,毫无疑义地要表现在历史家研究历史,撰写历史的方法上。
《通典》问世以前,最有影响的历史著作莫过于《史记》和《汉书》。因此,考察《史》《汉》的史学方法,对于我们认识《通典》的史学方法究竟在何等意义上取得了重大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启发的。司马迁在谈到他著《史记》的具体方法时说: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3]
这里说的纪、表、书、世家、列传,反映着社会历史的五个方而,也是《史记》一书的五个层次。在司马迁看来,他所制定的纪、表、书、世家、列传,是有其自身的逻辑的,不论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司马迁所提出的逻辑和客观历史进程是什么关系呢?它们在多大的程度上达到了一致呢?依我的浅见:《史记》写了大量的、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物的活动和思想,写了政治、经济,写了天文、地理,写了有关的制度;其中,有许多是光辉的篇章,也有不少卓识。但是,从它的纪、表、书、世家、列传这五个方面或五个层次来看,还不能说它基本上(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和逻辑的一致。不错,这五个部分是相互补充、相互联系的,但这种联系毕竟不同于客观历史进程中的那种联系。
班固断代为史,撰写《汉书》百卷,他的方法是:
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按:以上指帝纪、《百官表》及《诸侯王表》)。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按:以上指《天文志》《五行志》《律历志》)。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按:以上指《地理志》《沟洫志》《古今人表》及《郊祀志》)。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按:以上指《艺文志》和人物列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按:以上是说《汉书》文字的典雅和内容的宏富)。[4]
这一段话,集中反映了班固撰写《汉书》的逻辑方法,即首叙帝、王、百官,天文、五行、律历次之,地理、沟洫、郊祀又次之,艺文又次之,末叙各种人物。班固提出的这个逻辑,同样也没有反映出客观的历史进程。但是,有一点是应当注意到的,就是:班固在表述他的逻辑方法时,好像比司马迁表述自己的逻辑方法更清楚一些,而这主要表现在班固对《汉书》十志的作用的认识上。
《史记》和《汉书》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但如果从历史和逻辑的一致这一要求来看,从它们所反映出的史学方法来看,证明它们还处在史学发展的早期阶段。这并不奇怪,因为它们都是中国封建社会成长时期的史学著作。
《通典》产生于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它的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所能够继承的历史上的思想资料,所能够接触的当时的社会思潮,都比马、班时代广泛得多、丰富得多、深刻得多。这些,都会反映在杜佑对社会历史的观察和分析上,反映在他研究、撰写历史的方法上。
先从宏观方面考察。杜佑明确地指出: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5]
杜佑的这一段话,是用大手笔勾画出的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在杜佑看来:应当通过教化去达到“致治”的目的,而“教化”,则应以食货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一套选举办法和职官制度;礼、乐、兵、刑,乃是职官的职能;州郡、边防是这些职能在地域上的具体实施。因此,作者在《通典》中首先论述经济制度;其次依次论述选举制度和职官制度,礼、乐制度,战守经验,刑罚制度;最后论述地方政权的建置和边防的重要。
这里应当指出两点:
第一,杜佑把《食货》置于《通典》各门之首,然后分别论述了上层建筑的一些重要方面。作者这一研究和表述历史的方法,可以说是在根本点上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杜佑这一方法的理论根据是:“《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6]乍看起来,这些理论根据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只是集中了古代思想家在同一问题上的一些思想资料的片断而已。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杜佑之前的所有历史家,都没有像他这样重视前人的这些思想资料,并把它们作为首先必须研究社会经济制度的理论根据。仅此而论,杜佑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7]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说的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科学的唯物史观,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前,人们是不可能提出的。但是,在中国哲学史和史学史上,唯物史观的萌芽是早就存在的。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杜佑已朦胧地意识到物质生活本身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的《通典》一书以“食货为之首”的见识和方法,是中国中世纪史家“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8]的天才尝试。杜佑虽然从他的先辈那里继承了某些思想资料,但他对它们都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并赋予它们新的含义和新的生命。本来只是某些思想片断,而在杜佑这里却成了一种史学观点和史学方法,成了一种学术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毫无疑义,杜佑取得了他的前辈们所不曾达到的思想成果。
诚然,这一新的思想成果,与其说是思维发展的必然结果,毋宁说是历史现实的必然产物。《通典》以“食货为之首”的思想和方法,无疑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唐代自安史之乱(755—763年)以后,不仅政治上从极盛的顶点跌落下来,社会秩序极不安定,而且社会经济也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危机,国家财政十分窘迫。对于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变化,盛唐以后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诗人在他们的著述、作品和言论里都有强烈的反映。而整顿社会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则是人们关注的重大问题。于是,在肃、代、德、顺、宪、穆、敬、文、武等朝的八九十年间,讨论经济问题的学者纷至沓来,相继于世。其中,比杜佑略早或大体跟杜佑同时的,有刘晏、杨炎、陆贽、齐抗;比杜佑稍晚的,有韩愈、李翱、白居易、杨于陵、李珏等[9]。刘晏的理财,“常以养民为先”[10]。杨炎倡议和实行的两税法,以及朝廷围绕实行两税法所展开的激烈的争论,是唐代经济制度史上很重要的事件。陆贽的经济思想在某些方面跟杜佑很相近,他认为:“建国立官,所以养人也”,“故立国而不先养人,国固不立矣;养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养矣”[11]。这些政治家的经济改革活动和经济思想,都是当时的历史现实的产物。而这样的历史现实、经济改革和经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启迪着杜佑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杜佑在《通典》里以“食货为之首”,正是一个卓越的历史家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回答了现实所提出的问题。《通典》之所以在根本点上反映了历史和逻辑的一致,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从《通典·食货》以下所叙各门来看,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也是很显然的,反映了作者对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各部门的关系及其重要性的认识。杜佑认为,在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各门中,职官制度是最重要的,所谓“行教化在乎设职官”,就是着重强调了这一点。选举制度是为职官制度服务的;而礼、乐、兵、刑等则是各级官吏代表最高封建统治者行使的几种职能,这些职能主要地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教化,一是刑罚,所谓“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就是这个意思。至于州郡,需要各级官吏“分领”;边防,也需要各级官吏处置:这是实施上述各种职能的必不可少的环节。由此可以看出,杜佑所叙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各个部分,大致有三个层次:一,选举、职官;二,礼、乐、兵、刑;三,州郡、边防。这三个层次,把封建国家在政治领域的几个主要方面都论述到了,反映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卓越的认识。
现在,我们再从微观方面考察。杜佑《通典》对封建社会历史的观察和分析,一方面是用大手笔勾画轮廓,另一方面是对每一领域作细致的解剖,而于后者也同样略见其逻辑的研究方法,体现出历史同逻辑的一致。以《食货典》而论,它共包含12卷,即:(1)田制上;(2)田制下,水利田,屯田;(3)乡党,土断、版籍并附;(4)赋税上;(5)赋税中;(6)赋税下;(7)历代盛衰户口,丁中;(8)钱币上;(9)钱币下;(10)漕运,盐铁;(11)鬻爵、榷酤,算缗,杂税,平准(均输附);(12)轻重。人们不能不注意到,这是一个很严密的逻辑体系。作者首先叙述土地制度,因为土地是封建经济中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其次叙述与这种封建土地制度相适应的农村基层组织;再次叙述以这种土地所有制形态为基础的赋税制度;复次叙述历代户口盛衰,这关系到劳动人手的多寡和赋税的数量;最后从第八卷以后,叙述到货币流通、交通运输、工商业、价格关系,等等。这样一个逻辑体系,极其鲜明地反映了作者研究封建社会经济的几个层次:从基本的生产资料出发,依次叙述劳动组织形式、赋税关系、人口关系和其他社会经济关系。在这里,作者研究问题的逻辑方法,跟封建经济的特点是相吻合的。因此,可以认为:“《通典·食货门》,从生产论到流通,从土地关系论到一切社会经济关系,这种逻辑体系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最能反映社会经济中基本问题的”。[12]毫无疑问,这又体现出杜佑的卓识。
然而,杜佑的这种卓识,并不仅仅限于他对“食货”所做的剖析,在《通典》其他各门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例如,《职官典》包括22卷:首先论历代官制要略(第一卷),然后分别论述三公、宰相、尚书、御史、诸卿、武官、东宫官属、王侯封爵、州郡、散官(第二卷至第十六卷),最后论禄秩和秩品(第十七卷至第二十二卷)。作者从京官论到外官,从职事官论到散官,从禄秩论到秩品,逻辑体系十分严密。值得注意的是,杜佑即便在这样一个具体的领域里,也是采用鸟瞰全局和剖析局部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如他论宰相,首先是把这个官职放在整个职官的全局中加以考察,其次才对这一官职进行细致的分析。而进行细致分析的时候,则是层层推进,条分缕析。如作者在《宰相》条下,列子目“门下省”“侍中”“中书省”“中书令”;进而于“侍中”之下又分细目“侍郎”“给事中”“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起居”“补阙”“拾遗”“典仪”“城门郎”“符宝郎”“弘文馆校书”等。作者用这种研究方法,把历代职官制度剖析得清清楚楚,洪纤无失。《通典》全书除《兵典》一门外,其他各门,亦多类此。
总之,不论是从宏观方面还是从微观方面来考察,可以说《通典》都有其自身的逻辑体系。这个逻辑体系,是作者观察和分析历史、特别是观察和分析现实社会所取得的成果。对于这个成果,当时人的评价是:“若使学者得而观之,不出户知天下,未从政达人情,罕更事知时变。为功易而速,为学精而要。其道甚直而不径,其文甚详而不烦。推而通,放而准,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不假从师聚学,而区以别矣。非聪明独见之士,孰能修之。”[13]“(杜佑)阅天下之义理,究先王之法志,著《通典》二百篇,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立言之旨备焉。”[14]这些评论,虽有过誉之处,但这里说的“推而通,放而准,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诞章闳议,错综古今”,却都不失为中肯的评价。当然,我们的认识还有超出前人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是把《通典》一书及其逻辑体系放在客观历史和作者主观认识之相互关系的位置上来考察的。通过上面的分析,是否可以认为,杜佑研究历史,并不是按照某种传统的思想模式(特别是儒家的思想模式)来铸造历史;恰恰相反,他大致上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来撰写历史。虽然他也照例要受到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局限,但跟他的那些杰出的前辈或同辈比起来,他毕竟又朝着历史的真实向前跨越了一步。因此,是否可以进而认为,杜佑《通典》所反映的逻辑体系,是那个时代历史家对客观历史之认识所达到的最高成就。
杜佑之所以能获得这样的成就,是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的。第一,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经过将近千年的发展,至唐代中叶已臻于完备,这就为历史家进行系统的总结提供了可能。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15]对这样的文物制度做出总结,并考镜源流,厘清脉络,阐明得失成败,本是历史提出的课题。第二,杜佑的历史见识,是他能够完成这个课题的主观条件。李翰说杜佑“雅有远度,志于邦典,笃学好古”,是“聪明独见之士”[16],这当然不是凭空吹捧的谀辞。《旧唐书·杜佑传》谓:杜佑“敦厚强力,尤精吏职”;“性嗜学,该涉占今,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要之,宦途的实践,渊博的学识,对史学的兴趣和时代的责任感,是造成杜佑这种历史见识的内在因素。第三,前人的思想资料,特别是同时代的一些政治家、历史家、学者的思想的启迪,是杜佑获得如此成就的又一个原因。第四,这是最直接、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唐代中叶以后的社会动乱,尤其是封建国家财政收入日益窘迫的现实,把作为政治家和历史家的杜佑,推到了他应当占据的位置之上。关于这一点,本文下面还要详细地加以论述。
二
杜佑的卓越史识,固然反映在《通典》写作方法的成就上,但这仅仅是从史学发展的一个方面即史学如何反映一定的经济、政治这个方面来考察的。如果从另一个方面即史学如何反作用于一定的经济、政治这个方面来考察的话,那么,杜佑的卓识,还有其更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主要表现在他的历史撰述的旨趣上。
为《通典》作序的李翰[17],因为“颇详旨趣,而为之序”,可以说是深得《通典》要旨的第一人。有的论者认为,杜佑在大历初年请李翰为《通典》作序,是想借助于李翰作为左补阙的官职及其名气,以扩大《通典》的影响。这无疑是把李翰的《通典序》理解得过于狭窄了。李翰说:
在李翰看来,杜佑撰《通典》,绝非为了追求广见博闻,高谈阔论,为史学而研究史学;反之,他是为了“经邦”“致用”而撰述《通典》的。“度其古”是为了“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最后还是要落实到“举而行之,审如中鹄”上。因此,《通典》跟一般的“文章之事,记问之学”迥然不同。此即李翰所窥见的《通典》一书的旨趣所在。这同上文所引另一个杜佑的同时代人权德舆所说的《通典》“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是完全一致的。
当然,考察一部史书的旨趣,更重要的还要看作者撰述的目的。杜佑撰述《通典》的目的,在《通典》自序、《上〈通典〉表》以及他后来撰写的《理道要诀》自序、《上〈理道要诀〉表》中,都有明确的说明。在《通典》自序里,他开宗明义地写道:“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这几句话,集中地反映了《通典》一书的旨趣所在。杜佑在《进〈通典〉表》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撰述旨趣,着重指出两点:(1)《孝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多属空泛言论,“罕存法制”,使人不得要领。(2)历代前贤论著,大多是指陈“紊失之弊”,往往缺少“匡拯之方”。因此,他主张:“理道不录空言”,必须“探讨礼法刑政”[19],仅仅停留在对最高统治者的“规谏”上是远远不够的,要研究“政理”的具体措施[20]。杜佑的这些看法,贯串着一个主旨,就是“理道”。他在贞元十九年(803年),辑录《通典》要点,另成《理道要诀》33篇(一说32篇),“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21]。《理道要诀》可以认为是《通典》的“简本”或缩写本,杜佑用“理道要诀”名之,可见他撰述《通典》的主旨本在于此。说“《通典》的精华是‘理道’的‘要诀’”[22],可谓切中肯綮。
杜佑说的“理道”即“治道”,同李翰《通典序》说的“经邦”“致用”是一致的。李翰自称“颇详旨趣,而为之序”,当是实话。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像杜佑这样明确地宣布,其历史撰述就是“征诸人事,将施有政”,为现实“理道”服务的,在他以前的史家中,几乎还不曾有过。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来看,杜佑以前的史家,主要是通过他们的历史撰述来反映客观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从而给人们提供丰富的历史借鉴。据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23],但这只是孟子的说法;孔子是怎么讲的,人们并不清楚。而所谓“乱臣贼子惧”,主要也是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上来说的,还谈不到具有“经世”的意义。司马迁是伟大的史家,他撰《史记》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要“述往事,思来者”,设想和成就都是很高的,但他却宣布要把《史记》“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24],也不是要用它来“经邦”“致用”。至于班固撰《汉书》,本是为了证明“汉绍尧运,以建帝业”[25],格调就低得多了。陈寿著《三国志》,时人称为“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26]。其实,他着力宣扬的不过是皇权神授的思想和封建伦理观点,苍白的历史观和政治观决定了他不可能考虑“经邦”“致用”的问题。杜佑不赞成前人“多主于规谏而略于体要”[27]的撰述宗旨,把历史撰述跟“理道”直接联系起来,这是对史学作用认识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当然,这绝不是说杜佑以前的历史撰述是脱离现实,不为现实服务的。恰恰相反,《春秋》以下的任何一部史书,都是和现实有密切联系的,都是在一定程度上为现实服务的,而且在有些方面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例如,西汉初年的政治家、思想家、历史家在总结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方面,唐初的政治家、思想家、历史家在总结隋亡唐兴的历史经验方面,都有比较深刻、系统的见解;《史记》《隋书》分别集中了这方面的成果,特别是《隋书》总结的历史经验,对于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政治是有直接的影响的[28]。杜预说孔子作《春秋》,“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29];司马迁“述往事,思来者”;唐初李渊《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说“多识前古,贻鉴将来”[30];等等,都包含着要以史学为现实和将来服务的思想。这样的例子在史学上是很多的。那么,杜佑在把史学和现实直接联系起来这个问题上,比起他的前辈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我以为至少有两个方面:(1)从认识的自觉程度来看。杜佑宣布他撰《通典》是“征诸人事,将施有政”,为“理道”服务,表明他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有较高的自觉性,这是中国古代史家对史学的社会作用之认识的一个飞跃。(2)从撰述的内容来看。杜佑对“术数之艺”“章句之学”,“文章之事,记问之学”,都没有很大兴趣。故《通典》一书“不录空言”,专事“探讨礼法刑政”;“事非经国礼法程制”者,不录。这样,《通典》在内容上就突破了“规谏”“劝诫”的窠臼,更讲求实际,其所叙历代典章制度,多与现实有直接联系。这是杜佑不同于他以前的史家的又一个重要之处。
诚然,杜佑以史学著作“理道”“施政”的经世致用的主张,并不是他思想上固有的模式,而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潮流的反映。杜佑生活在唐中叶的变乱时期。从玄宗后期起,至宪宗末年,朝政的紊乱,朝廷和藩镇割据势力的斗争,藩镇之间的斗争,以及民族间的矛盾、斗争,是这一时期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特征。由于变乱的不断发生,人民流离失所,生产遭到破坏,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则是这一时期经济上的特征。唐中叶变乱的转折关键是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而其影响所及,则终唐之世。然而,正是这样的社会变乱,造就了一大批人才。中唐时期,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接踵而至,形成了继唐初之后又一个人才高峰。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政治家如陆贽、李吉甫、裴度,军事家如郭子仪、李晟、李愬,理财家如刘晏、杨炎,思想家和文学家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诗人如杜甫、白居易,等等。他们大多是一些思想进取、锐意改革的人。他们的言论、行事、著作和作品,大多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和特征。杜佑和他的这些同时代人一样,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的人,而他的“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的政治胸怀和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也都可以从他们那里找到同好或共鸣。史称:理财家刘晏力主“富其国而不劳于民”[31],“体国安民之心,不可没矣”[32]。政治家陆贽“以天下事为己任”,对“理道”“理兵”“足食”有许多切中时弊的建议,他的“经国成务之要,激切仗义之心”[33]对当时和后世都有极大的影响。柳宗元、刘禹锡都是“永贞革新”的积极参加者,这次革新虽然失败了,但他们的改革精神是应该肯定的。特别是柳宗元的政论、史论、杂文和其他作品,都贯穿着“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34]的宗旨。白居易在宪宗元和十年(815年)写道:“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35]白居易的这种文学思想,无疑也是中唐时期的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李吉甫当国,史称其“该洽多闻,尤精国朝故实,沿革折衷,时多称之”;他撰的《六代略》《元和郡县图志》《元和国计簿》和《百司举要》等书,都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的特点,用他的话说,就是“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36]。清代学者孙星衍说李吉甫主要行事“皆切时政之本务”,所著诸书“悉经世之学”[37],是很中肯的。上面所举这些事实证明,在唐代中叶,倡导并致力于经世之学者,绝非三两个人而已;经世之学,至少在地主阶级的一些有识之士中,已逐渐形成一种倾向。而杜佑正是这种倾向在史学领域的先驱和突出代表,《通典》一书可以认为是开中国史学史上经世史学的先河。
杜佑的经世致用的主张,在《通典》一书各部分内容中都有具体的反映,兹撮述其要点如下:
(一)经济思想方面。杜佑经济思想之最重要的方面,首先是他认为物质经济生活是一切政治措施的基础。他在给部帙浩繁的《通典》所写得极其简短的序言中,用画龙点睛之笔勾勒出他的“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的经济思想和《通典》在编次上以“食货为之首”的撰述意图,序言末强调了“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尤其显示出他对序言中所写的这些话的高度重视。有的研究者认为:杜佑的这种认识和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基础对建筑在其上的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的主要的决定作用”[38]。这种评价是并不过分的。我们可以认为,在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的认识上,杜佑是中国古代史家中第一个达到这种成就的人。其次是《通典·食货典》的逻辑体系,反映出杜佑对封建社会经济各部门及其相互联系的认识,已经达到了基本上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程度。如果说以上这两个方面主要地表现为认识上的价值的话,那么以下几个方面则反映了杜佑经济思想在实践上的意义,即:(1)谷、地、人,是从经济上达到“治政”的三个关键。他说:“谷者,人之司命也;地者,谷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谷则国用备,辨其地则人食足,察其人则徭役均:知此三者,谓之治政。夫地载而不弃也,一著而不迁也,国安而不动,则莫不生殖。”[39]在杜佑看来,只要解决好粮食、土地、劳动人手这三个问题,就能达到“国用备”“人食足”“徭役均”的目的,社会经济才能不断发展。(2)在经济政策上要处理好“国足”和“家足”的关系。他认为:“国足则政康,家足则教从”;家足的办法不是逃税而是土著,国足的办法不是重敛而是相反的做法[40]。杜佑还说:“宁积于人,无藏府库。百姓不足,君孰与足?”[41]认为“家足”是“国足”的基础,“国足”不能离开“家足”,这样社会才能安定。(3)在财政思想方面主张“薄敛”和“节用”。杜佑说:“夫欲人之安也在于薄敛,敛之薄也在于节用;若用之不节宁敛之欲薄,其可得乎?”[42]他高度评价了唐代开国初的“薄赋轻徭”的政策在稳定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多次指出“厚敛”必然导致社会的动乱和政权的败亡。因此,他主张国家应该“省不急之费,定经用之数”,改变当时“甲兵未息,经费尚繁”的状况。杜佑的这些具体经济主张,都是为了避免“赋阙而用乏,人流而国危”[43]的局面的出现。
(二)人才思想方面。杜佑认为,人才对于管理国家政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说:“为国之本资乎人,甿人之利害系乎官政。”[44]他不认为政治的好坏只是“明君”或“昏君”一个人的事情,即所谓“君不独理,故建庶官”,所以“官政”如何,于“国本”关系极大。这是杜佑人才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他在人才思想方面的具体主张是:(1)以教育促进人才的成长。杜佑认为:“上材盖寡,中材则多,有可移之性,敦其教方善;若不敦其教,欲求多贤,亦不可及已。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这里有两点是值得重视的:一是人才不是“天生”的,是要靠教育的手段才能得到的;二是今人并非不如古人,人才都是在政治活动的实践中造就成的。(2)反对以言取士。杜佑对魏晋以来的取士制度颇持批判的态度,他主张选拔人才,要注意到“行备,业全,事理,绩茂”这样几个因素,即着重从其实际才能方面进行考察,那么真正的人才就会被选拔出来。所以,他坚定地认为:“以言取士,既已失之;考言唯华,失之愈远。若变兹道,材何远乎!”(3)主张采用多种办法和途径选拔人才,鼓励人才发挥作用。杜佑认为,在人才问题上,“诚宜斟酌理乱,详览古今,推仗至公,矫正前失。或许辟召,或令荐延,举有否臧,论有诛赏,课绩以考之,升黜以励之。拯斯刓弊,其效甚速,实为大政,可不务乎!”这里,他提出了一套综合的人才管理办法,包括古今的经验教训,当事人的公正态度,考核制度和升黜制度。杜佑把这看作是一件“大政”,足见他对人才问题的重视。正因为如此,他极不赞成“行教不深”而“取材务速”的急躁做法和“以俄顷之周旋定才行之优劣”的轻率态度。
(三)吏治思想方面。杜佑的吏治思想有两点是很突出的,一是省吏员,一是用有才。他在《通典·职官典》后论中引用唐睿宗时监察御史韩琬的话说:“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称其人,须人不虚其位。”[45]又引他自己在唐德宗建中年间的“上议”说:“详设官之本,为理众庶,所以古昔计人置吏。”所以他认为历史上那种“约人定员,吏无虚设”的办法是正确的。杜佑从经济的观点和财政收入的具体状况考虑,认识到维持一个庞大的官吏队伍,对封建国家本身来说实在是一个严重的负担,是一个“大弊”,不改革是不行的。这就是杜佑关于省吏员的基本出发点。他断然说:“有才者即令荐用,不才者何患奔亡!”在他看来,在“并省官吏”的改革中,起用“有才者”,沙汰“不才者”,是很正常的事情,有什么需要担心的呢!这是他的用有才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