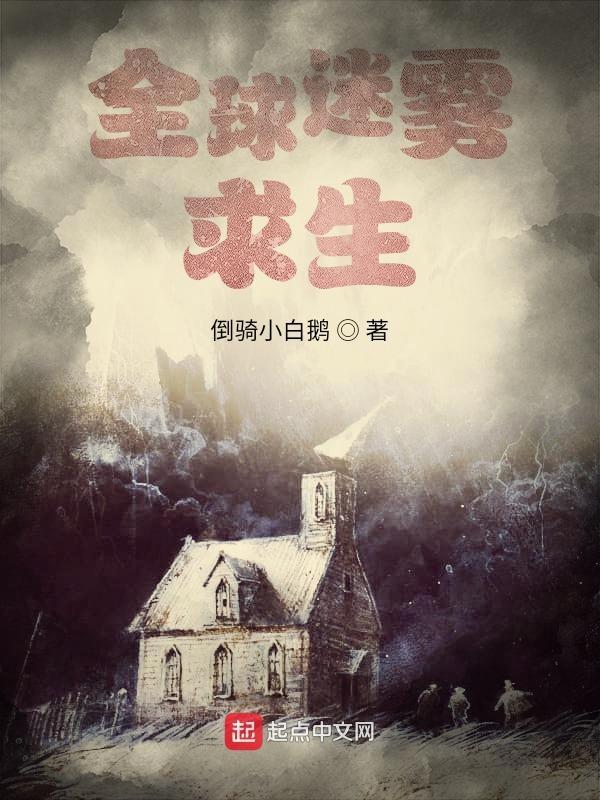奇书网>中国古代史学的终结者 > 发展中的重要转折(第2页)
发展中的重要转折(第2页)
《通典》继承先秦以来礼书的传统和《史》《汉》以来“正史”书志的体例,创立了典制体通史的格局。它以典章制度为中心,附以诸家言论,总为一书,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本朝玄宗天宝之末。全书分为九门: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时人亦称为“分门书”。每门之下分若干子目,子目之下更有细目,条分缕析,结构严谨,浑然一体。《通典》创造了综合性的典制体通史形式,奠定了独立的制度史撰述的基础,扩大了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的领域。
分门和会通是《通典》的两个显著特点,而它的分门则自觉不自觉地反映了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杜佑在《通典》自序中着重阐述了他对分门的逻辑认识: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敌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12]
“教化”同“衣食”的关系是精神同物质的关系,而以衣食为“本”。这是杜佑关于国家职能的总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而有各种制度和设施,其中又“以食货为之首”。这些认识,在历史理论上是前无古人的。杜佑的历史理论,在全书的叙、论、说、议、评、按中,有极充分的反映;而历史进化思想和传统门阀观念的冲突,也反映出杜佑的历史观和社会观的矛盾。
《通典》因其续作屡代不绝而被称为“十通”之首,在史学上有崇高的地位。
四、通史撰述的复兴趋势
《史记》以通史的成就饮誉汉魏两晋南北朝,然数百年间关于通史方面的撰述则甚为寥落。梁武帝曾命史家吴均等撰《通史》六百卷,北魏元晖也召集史家崔鸿等撰《科录》二百七十卷,这两部通史都没有流传下来。唐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至中晚唐形成通史复兴的趋势,成为古代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盛唐时期,有虞世南撰《帝王略论》,这是一部关于历史的通论,它的价值在于运用比较的方法而展开评论,今有敦煌文书抄本和日本国镰仓时期抄本,均为残卷。有韩琬撰《续史记》一百三十卷和萧颖士撰编年体汉隋间通史,这两部书都失传了。
中晚唐时期,除杜佑撰典制体通史外,还有许嵩撰《建康实录》二十卷,编年体,今存;韩潭撰《统载》三十卷,传记体,已佚;高峻撰《高峻小史》六十卷,纪传体,已佚;马总撰《通历》十卷,编年体,今存后七卷;陈鸿撰《大统纪》三十卷,编年体,已佚;姚康撰,《统史》三百卷,编年体,已佚。这些书,除《建康实录》是通记三国·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史事外,其余都是贯通古今的著作。其中,《统载》“采虞、夏以来至于周、隋,录其事迹善于始终者六百六十八人为立传”[13];《高氏小史》“一以《太史公书》为准”[14];《统史》“上自开辟,下尽隋朝,帝王美政、诏令、制置、铜盐钱谷损益、用兵利害,下至僧道是非,无不备载,编年为之”[15]。加上《通典》,这四部书分别采用了传记、纪传、编年、典制等不同的体裁,通史撰述,蔚然大观。
通史撰述发展中的这一转折,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体裁多样,二是产生了名作,三是开拓了历史撰述领域,四是发展了史学上的会通思想。
[1]魏徵等:《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8页。
[2]魏徵等:《隋书》卷五十六《杨汪传》,卷七十五《儒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394、1715~1716页。
[3]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恩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57页。
[4]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67页。
[5]郑樵:《通志二十略·艺文三》,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528页。
[6]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70页。
[7]参见刘知幾:《史通》原序与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271页。
[8]刘知幾:《史通》卷四《序例》,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1页。
[9]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1页。
[10]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1页。
[11]杜佑:《通典》《进〈通鉴〉表》及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书首第1页、正文第1页。
[12]杜佑:《通典》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13]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五《国史部·采撰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85页。
[14]高似孙:《史略》卷四,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0页。
[15]刘昫等:《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