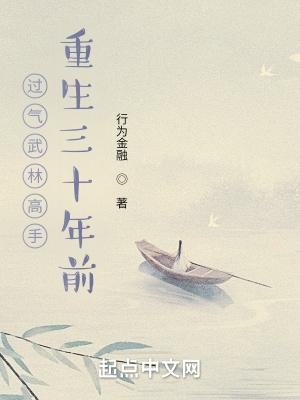奇书网>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 第二节 社会科学解释的复杂性研究路径(第1页)
第二节 社会科学解释的复杂性研究路径(第1页)
第二节社会科学解释的复杂性研究路径
一、当代社会科学解释的基本观点
19世纪中后期建制化的社会科学开始形成,在寻求社会科学解释制度的合法性中,形成了两个主要方向:实证主义和诠释学。实证主义认为,社会科学要取得和自然科学一样的成就,必须采用在自然科学中已获得成功的实证方法;而诠释学方法则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完全不同,它是一种纯粹意识领域的思维活动。这两种方法体现了解释与理解的对立。
由此出发,在当代关于社会科学的解释问题上,表现出以下几方面观念上的差异。
第一,把社会科学解释简单划分为归纳解释和演绎解释,或经验解释和理论解释。经验解释是在一定的经验规则性的基础上,对事件做出解释和预测;而理论解释则是在对事件过程和内部机制假定的前提下,推出该事件的复杂结构。事实上,在具体的解释实践中,很难划分二者的明确界限。对事件的经验解释,应该由关于经验规则性的理论解释来补充;而演绎解释则需要得到关于假设及其应用的经验支持。由于社会科学现象的多样性和不可重复性,以及与相关主体及环境交互作用的非线性,不可能在确定的规律和理论基础上做出解释。因此,社会科学解释必定是归纳解释和演绎解释的有机结合:在经验观察和理论推理的基础上,实现既具有可检验性,又具有逻辑精确性的社会科学解释。
第二,在社会本质上形成了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两种社会观:个体主义认为社会是个体的集合,个体之间本质上没有差别;而整体主义认为社会结构具有独立性,不可还原为个体的信念和目的。这两种观念导致了对规范和价值作用的不同认识。科林伍德(R。G。gwood)、德雷(W。Dray)和冯·赖特(G。H。vht)等人认为,合理的社会科学解释必须包含规范,因为它是社会科学所固有的。与之对立的亨普尔、亨德森(D。Henderson)等人则认为,可以将规范解构为主体的信念和倾向,比如意向性行为的解释并不涉及规范。事实上,这只能证明规范在个体心理层面上没有解释力,而不能证明其在社会维度上缺乏解释力。
由此,与社会科学解释对应的,有微观解释和宏观解释之分:宏观解释是在群体层次上对社会群体的某些特征或构成要素的相互作用的描述;微观解释是对主体的倾向和行动在个体层次上的描述。个体行动的规范性只有在群体活动中才能体现出来,因此群体层次的宏观解释不能还原为个体层次的微观解释。要求群体解释与对构成群体的单个个体的解释集合对等,实际上预先假定了每个个体可能的状态和排列都是可实现的。而事实上,个体倾向的随机分布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是社会科学解释独有的特征,其本质上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论在社会解释中的具体体现。
第三,自然主义解释观和反自然主义理解观的对立,是社会科学解释中一个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争论。其对立的核心前提是对社会科学规律存在与否的争论。自然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中存在规律,并且其发挥作用的方式与自然科学规律别无二致;反自然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开放性和研究主体、对象的能动性,决定了社会科学规律没有普适性,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只有通过对构成它们的意义的诠释学理解才能进行。事实上,一方面,因为社会现象所固有的多重因果关系,社会科学规律本质上是受限的,但这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并不影响它的适用性以及解释和预测;另一方面,一些统计规律,甚至是人为制定或约定俗成的规则,同样可以起到解释和预测社会行为的作用。这两种解释观都过度依赖对科学本质的假定。反自然主义错在声称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包含对有意义的现象的诠释,自然主义则狭隘地否认了理解等所发挥的作用。[18]
与自然科学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和环境相比,社会科学研究更加多样化。这使得在不同的社会科学解释模式中,寻求统一的逻辑特征异常困难。但这种科学解释的多样性,“既非偶然也非随机……任何单个主体的持存都依赖于其他主体提供的环境,即每种主体都安顿在以该主体为中心的相互作用所限定的合适生态位(niche)上”[19]。这种多样性是探讨社会科学解释的前提。
二、社会科学解释的本质
各种解释机制和模式内部存在的问题及相互之间的对立冲突,体现了对社会科学解释的内涵、本质和特征的认识差异。
首先,是关于社会科学解释的目的问题。
解释涉及对问题的回答,利特尔(D。Little)将这些问题分为“为什么必然”和“如何可能”的问题。[20]“为什么必然”的问题涉及证明某一事件、规则性或过程在特定环境中是必然的或可预测的,即确定被解释项出现的初始条件和因果过程。这种对产生被解释项的充分条件的描述是决定论的。“如何可能”的问题通常与复杂系统,如复杂的神经网络、社会组织、经济体制等的行为有关。在具体的社会科学解释实践中,解释项所描述的条件一般只是增加了被解释项出现的可能性,而不是必然会导致被解释项的出现。因此与非决定论的社会系统相关的解释问题,基本上都是“如何可能”的问题。
社会现象的非决定论性质使得社会科学解释并不需要为被解释项提供准确可靠的解释和预测,而只是在一定的可行范围内和程度上,对被解释项的内部机制和动力学给予说明。因此,社会科学解释不一定是“科学的”解释,但一定是符合语境的解释。
其次,是关于当前社会科学解释的模型。
(1)因果解释模型。它假定被解释事件是其他先在事件或条件的结果。原因和结果通过规律连接起来,因此规律或无例外的概括成为两个变量之间必然联系的先决条件。因果解释还包括功能解释、结构解释和统计解释等形式。
总体上看,因果解释模型过分强调客观原因,而忽视作为行动理由的人的需要、目的和心理动机,因此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历史学家通常关注的是单个特殊事件;二是相关规律并不是解释特定事件的必要条件。而且,在复杂社会现象和系统中,因果推论有多种表现形式,如单一因果判断、类因果关系、因果相关陈述以及概率性因果陈述等,所以不能一概而论,简单地将原因和结果通过规律直接连接起来。事实上,社会科学中因果推论的基础是社会现象和系统中的因果机制:C产生E,意味着有一个因果机制主导着从C的出现到E的出现。[21]
此外,对社会现象或系统的因果解释,除了要求揭示其基本的因果机制外,还必须证明单个的机制(微观层次上)如何运行,以及单个的机制如何被联系起来(宏观层次上)。这样,微观层次影响宏观层次,宏观层次再反过来影响微观层次。系统论解释以这种方式成为个体主义解释和整体关联解释的一个替代。[22]但要注意,社会科学中连接原因和结果的特定因果机制,与特定个体的信念、要求、力量和约束相关,在具体的解释活动中其特征和表现不同。
(2)意向性解释模型。从个体角度看,社会变革基础的核心因果过程源于理性—意向性行为。人类作为一种意向性生物,在理性基础上活动。因此,如果假定各种社会环境中的个体都能在其信念和目标的基础上做出慎重选择,那么就可以把大量社会现象解释为这些选择的综合结果。但这个前提是有争议的,因为个体在其环境中做出的理性选择是不完全的:一是有些环境超出了个体的理解,受到其习惯、技术能力等的限制;二是个体在同样的选择环境中可能有不同于其他个体的价值和目标;三是个体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掌握所有与理性选择有关的知识。这就是西蒙(H。Simon)所说的“有限理性”。这样所构造的理想的理性选择模型与实际社会现象或问题几乎无关,起不到任何指导、解释和预测作用。其问题在于:一方面,它把规范所发挥的解释力瓦解为对主体信念和倾向的描述,把解释集中于个体而忽视个体活动的社会环境是其错误的根源;另一方面,阐述主体动机的好坏是解释其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需要将个体置于其活动的群体背景下,借助规范性标准来予以评价。因此,规范像工具理性、道德命令和实践准则一样,是解释的一部分。[23]
(3)诠释学解释模型。上述两种解释模型强调了概括和归纳在社会解释中的重要性,与此不同,诠释学解释模型强调不同文化独特性的作用。诠释学理论认为,社会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对有意义的人类实践的解释。这种方法强调理解和解释之间的区别:解释涉及确定一个事件的基本原因,而理解涉及发现一个事件或实践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的意义。[24]自然科学与客观的因果过程相关,而社会科学与有意义的行动和实践相关。前者可以得到客观描述和解释,后者需要检释和理解。因此,解释是自然科学的目标,而理解是社会科学的目标。[25]泰勒(C。Taylor)指出:社会科学必须是诠释学的,只依赖于客观因素,如因果关系、社会结构、抽象理性等的社会研究必将失败。[26]他把诠释学解释模型作为社会科学解释的严格标准来看待,这样就把因果解释和理性选择解释拒斥在外了。诠释学框架对于社会科学的某些问题的确是一种合适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社会科学都必须采用这种解释模式。在很多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社会结构和抽象理性等发挥着关键性的解释作用。从本质上来讲,诠释学模型混淆了“行为规范模型”(themodelforbehavior)和“行为模型”(themodelofbehavior)。[27]前者就是诠释学模型所关注的特定语境中,社会因素对行为的规范及其所表达的意义,后者是对主体行动的客观描述。因此,如果说意向性解释模型忽视了规范在社会科学解释中的作用的话,那么诠释学模型则过分强调了规范的作用,而忽视了客观因素在解释中所发挥的作用。
这几种主要的社会科学解释模型的特征和表现形式各有不同,充分反映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在具体的社会科学解释实践中,认识各种解释模型的使用范围和边界,重视和吸收各种解释模型,是社会科学研究本质的必然要求。
由此可见,在社会科学解释确立的科学合法性标准之中,模型化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模型是针对原型而言的,原型是指人们在社会活动和生产实践中所关心和研究的实际对象,在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常常用系统或过程等术语来表达,如社会经济系统。模型来源于原型,但不是对原型的简单模仿,是人们为了认识和理解原型而对其所进行的一种抽象和升华。模型是理论或现象的精确“反映”,是科学的“催化剂”,有助于加速科学的发展进程。模型逐渐成为理论和数据之外,能够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发挥独立影响的要素,能够建立形式化的计算或数学模型,已经像理论和数据的普遍必然性与客观性一样,成为具有科学地位的衡量标准。因此,社会科学制度合法化很重要的基础之一就是模型化。
最后,是关于规律在社会科学解释中的作用。金凯德(H。Kincaid)和罗伯茨之间关于社会科学中是否存在规律的论战,基本反映了当代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之间,对规律在社会科学解释中的作用的看法。需要明确的是:(1)社会科学规律的存在及作用,是社会科学解释存在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即在某些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和主题中,社会科学规律的发现和确立有助于社会科学解释的实现,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科学解释都以社会科学规律的存在为前提;很多社会科学解释只是描述性的,或只是对一些社会科学问题做出的简单回答。(2)社会科学解释的科学合理性并不以规律的普适性和可预测性为标准。虽然严格的具有普适性的规律对于解释和预测社会现象有重大意义,但在很多成熟的具体社会科学学科中,统计规律或设限规律对社会科学解释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因此,明确规律在社会科学解释中发挥的作用,不仅有助于为社会科学规律的合理性进行辩护,更有助于确定好的社会科学解释所应该具有的一些基本标准和逻辑特征,避免因错误的规律观而导致对某些社会科学现象或问题的解释出现偏差。
规律一般是统计规则性或设限规律,在社会科学解释中的作用具体体现在:(1)统计规则性可以为我们接受或拒绝一个因果假设提供经验基础。构建一组可观察变量,它们对应于所研究现象或问题的核心范畴,那么根据这些可观察变量的相互关系,就可验证所假定因果关系的合理性,但这种验证不是结论性的。(2)设限规律可以揭示一系列复杂社会现象潜在的规则性。在反复的实验和对比中,找到构成现象的要素中那些真正相关且互相影响的,以这些要素为基本变量,就可形成对潜在的因果过程的假设。这个过程中所发现的要素之间的协变性是研究因果假设的一个有效工具。
三、社会科学解释的复杂性模型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从复杂性视角对社会现象和系统的内部动力学运行机制进行分类,揭示在对社会现象进行的科学解释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社会机制及其运行过程,同时分析在复杂性科学中取得重要进展的“基于Agent的建模”方法(Agent-BasedModeling,ABM),从而为社会科学解释提供一种复杂性模型的研究视角。
1。社会现象和系统的复杂性分类
社会科学的主体、对象以及方法都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因此,在社会科学现象和系统的内部动力学运行机制的基础上,根据其复杂性、可预测性及生成复杂结构和形式的能力,对社会科学现象和系统进行分类,是构建社会科学解释模型的前提。
图8-1是对所有实在的内部动力学运行机制的简单分类。因为社会现象的多变性,这里仅着重考察动态现象和系统。
图8-1社会现象和系统的复杂性分类图[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