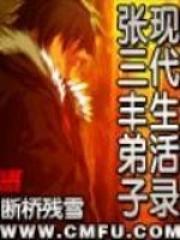奇书网>当代社会科学哲学导论 > 第一节 社会科学的哲学困惑及其解决方案(第1页)
第一节 社会科学的哲学困惑及其解决方案(第1页)
第一节社会科学的哲学困惑及其解决方案
一、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哲学困惑
哲学与社会科学共享着许多极其普遍的核心概念、原理和问题,它们联系密切,其中一些部分相重叠。首先,所有的社会科学都使用哲学概念,比如事物、属性、过程、假设、真理等;其次,所有的科学都预先假定一些极其普遍的原则,比如无矛盾的逻辑原则、外部世界现实的本体论原则和世界的可知性的认识论原则。而且,哲学家的工作必然会对社会科学家处理社会事实和分析社会理论的方式产生影响,包括积极的或消极的;实证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新康德主义、实用主义、现象学和分析哲学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强大影响就足以证明这一点。[1]另一方面,社会科学中实际上也存在着大量的哲学争论。[2]
邦格认为,这些问题都需要两个领域的合作才能解决;然而事实却是,大多数社会科学家从未深刻地检验过他们的哲学,这就造成了他们哲学中的混乱。这些混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社会科学研究中核心概念的混乱
社会科学家共同体一致认为,社会科学与逻辑学、数学等形式科学不同,它研究的是社会事实,属于事实科学。然而,关于什么是社会事实,甚至事实一词的含义,人们都未形成一致性看法:或认为它指示一个事件,或将它等同于数据,或看作一个特殊的真命题。而在后现代主义思想中,事实要么等同于符号或隐喻,要么被看作是社会建构或社会惯例,这就造成了社会科学中事实与真理概念的混乱。对社会事实的认识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自然主义者认为,社会事实是与自然事实一样的存在;社会生物学家把社会事实看成是一种特殊的自然事实;唯心主义者,尤其是解释主义者,将社会事实置于自然之上;个体主义者认为,“社会事实的基本单元是个体的人,只有个体独立存在”[3],他们否认拥有自身属性的超个体实体的存在,否认对集体研究的合法性,或者说,他们认为这样的事实都只是个体行为的集合。与之相反,整体主义者仅仅把外在于个体或者个体之上的事实看成是社会的。像这种对基本概念的混乱认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比比皆是。
2。社会科学认识的混乱
关于对社会事实的解释,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实证主义者认为,解释一个事实就是将其归入一个一般化概括之中,即从某些解释项中推出被解释项,对社会事实的解释只需要求解释项和被解释项中包含一些社会谓词即可;解释主义者则认为社会事实所需要的仅仅是理解,或者叫“理解性”解释,即理解行为者的目的和意义即可。
方法论个人主义者认为,“解释社会事实始于个体,对社会事实的解释最终必须根据个体的行为和目的作出”[4],社会事实乃是个体行为的集合,对社会事实的解释就是对个体行为解释的集合;他们推崇自下而上的解释模式。而方法论整体主义者则认为,社会事实有其自身独特的突现属性和完形属性,只能从整体这个层面来进行解释,因此,对社会事实的解释非但不能还原为对个体行为的解释,相反,对个体行为的解释必须基于对社会事实的解释,从而主张自上而下的解释模式。对社会预测、经验操作等其他社会研究过程的分析亦存在类似的混乱状态。
3。现有社会科学哲学理论领域的混乱
现有的社会科学哲学领域中存在着纷繁众多的理论形式,并彼此争论不休,主要有以下三种。
(1)在社会科学哲学的本体论领域,关于社会实在的性质,不同的社会科学哲学流派有着不同的看法。唯物主义者承认社会事实的实体性存在,认为所有的社会事实都是具体实体的状态或者状态变化;唯心主义者则否认社会事实的实体性存在,认为社会事实要么是理念,要么是理念的体现。具体而言,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事实是存在的,它们是可感实体,新实证主义者则把社会事实看成是精神实体;结构语言学派认为社会事实是语言或者如同语言一般的存在;解释主义则把社会事实看成是文本或者如同文本一般的存在,它们处于历史文化的变动之中。
(2)对处于社会科学哲学本体论的核心位置的社会的本质问题,争论最多的就是“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根据个体主义,社会只是个人的集合体,因此所有的社会研究都最终是对个体的研究,他们把关注点集中于个体,要么否认社会关系和社会系统的存在,要么声称它们都完全可还原为个体和个体行动。整体主义则认为,社会是超越其成员的一个整体,它只能在整体层次上被理解,个人是社会的产物,其一切都决定于社会。此外,还存在着社会自然主义和历史文化主义之争。社会自然主义,包括环境决定论和生物决定论,强调社会与自然的连续性,把社会看成是自然的一部分,把现实“等同于自然的唯物主义素朴形态和原始型”,认为“人类只不过是复杂的猿,人类社会仅仅在复杂性上与蚁穴有所不同”[5]。历史文化主义则把社会与自然相对立,强调社会的非自然特征和人造性。
(3)在社会科学哲学的认识论领域,主要存在两组对立的理论形式:直觉主义和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和理性主义。直觉主义认为人类有能力在不进行分析的情况下,即时把握事物和理念,拥有关于事物的某种知识,而且这种知识是绝对可靠的,不需要证据和检验;而经验主义则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源于经验,尤其是源于知觉,因此所有的知识都必须是经验上可检验的。实用主义以行动为中心,认为行动是所有知识的来源、内容、检验标准和价值所在,而理性主义则是相信理性。此外,还存在科学实在论与各种主观主义之间的争论,包括约定论、知识建构论、相对主义、解释主义等。
二、精确化社会科学的理论诉求
邦格分析了上述状况,指出当今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众多核心要素都是模糊不清的,社会科学和传统哲学一样深受模糊性之害。他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中潜在的概念、原理和假设的真假,可以并且应该被确定,这对于引导好的社会科学来说是极其重要的。[6]针对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哲学困惑,邦格提请社会科学家们批判地反思这些混乱,借助逻辑和数学手段对其重新加以表述,使之消除模糊性,达到精确化和明晰化,以期对社会科学加以改造和重新定位。
1。社会科学核心概念的精确化
邦格对事物、属性、事件、因果关系等社会科学核心概念的含义做出明确规定,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数学工具对其进行精确化处理,力图实现社会科学研究中概念的形式化。这方面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
(1)邦格把属性表示为事物的数学函数,把所有属性的集合表示为事物的状态函数,并主张除存在之外的所有属性和变量都可以被量化。这样,状态函数就成为一个n元组的数值函数,从而用状态函数值即可表示在任一给定时间的一个系统的状态,状态函数的值域则构成了表示事物的状态矢量空间,可用来表示这一类事物所有可能状态点的集合。此外,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将事件看成是用数量或性质描述其变化的时间点事件,邦格把事件定义为一个状态变化,将状态变化看成是过程,从而用状态序列来表示事件,即通过有序对偶〈初始状态,最终状态〉来记述和描写事件。事件可用一个连接初始状态和最终状态的箭头来表示,过程或者历史可被表示为一连串状态,或者一条连续轨迹。
(2)关于因果关系,传统观点认为因果关系连接事物、属性或者状态,可用y=f(x)这样的函数关系表达,表示两个属性之间有伴随关系或者恒常连接关系。邦格主张因果关系连接事件,只有事件的变化才能被因果地联系起来,因此,因果关系必须用dy=f(x)·dx表达,以表示属性变化之间的一种协同关系,而这种关系不能等同于恒常连接。尤其是在社会科学中,智能动物的状态不仅取决于其环境,而且还取决于其历史,它们可能还包含着期望值(目的或者动机)以及为了实现期望的计划。因此,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因果决定论机制,社会科学中虽然也寻求因果关系,但却要复杂得多,因为它不是因果决定性的,社会事件充斥着大量的偶然性。
2。社会科学实践和理论分析的精确化
(1)邦格将形式化的表征大量用于社会科学现实问题的研究,实现分析的客观化、形式化、数学化,提升社会科学的可信度和精确度。例如,对社会学中的指标——贫困指数,邦格先假定贫困就是指不依靠过度劳动、乞讨、犯罪或公共福利的情况下无能力满足基本需要,然后假定测量个人通过其诚实劳动能满足第i种基本需要的程度si是可能的。这样,个人在i方面的贫困度pi就可定义为pi=1-si。个人总的贫困指数便可定义为该个体总的n种基本需要的平均值:P=(1n)∑ipi=(1n)∑i(1-si),由此就将贫困指数转变成一个客观指标。[7]
(2)邦格还通过形式化的分析来处理理论问题。对个体主义的弊病,邦格也是通过数学和逻辑分析来揭示的。他根据个体主义的观点假定社会是个体的集合,得出个体之间的二元关系无法通过个体来定义的悖论。同理,在能够作出“个体b属于社会团体G”这样一个陈述之前,我们必须已经持有社会团体G这个观念,这显然与个人主义的基本要求相悖。[8]通过这样的处理,社会科学中的很多问题便能够更为鲜明地得到呈现。
3。邦格精确化社会科学的思想来源
邦格在其早期的哲学思想中就已经明确提出哲学的精确化要求,他的精确化社会科学思想可以说是其科学唯物主义思想和科学方法论思想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