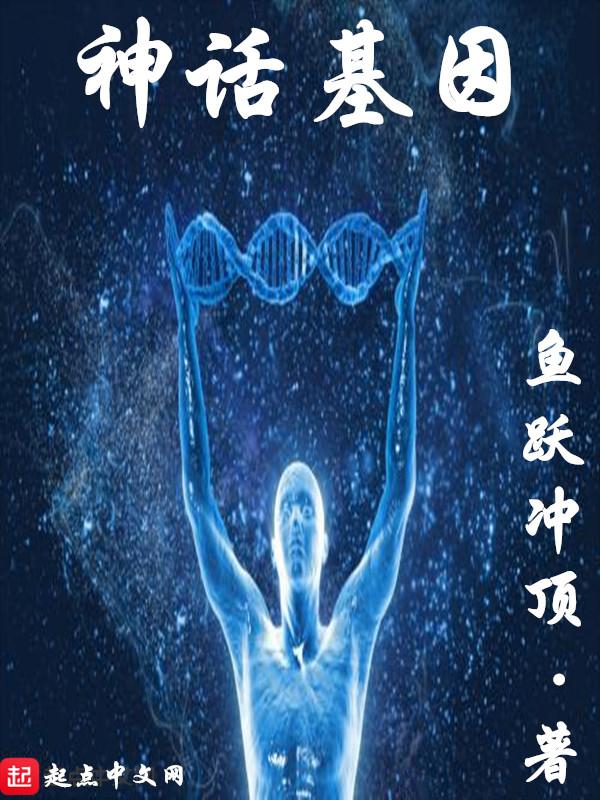奇书网>闻一多诗文集 > 女神之时代精神(第2页)
女神之时代精神(第2页)
啊!这又是何等的嫉愤!何等的悲哀!何等的沉痛!——
汪洋的大海正在唱着它悲壮的哀歌,
穹隆无际的青天已经哭红了它的脸面,
远远的西方,太阳沉没了!——
悲壮的死哟!金光灿烂的死哟!凯旋同等的死哟!胜利的死哟!
兼爱无私的死神!我感谢你哟!你把我敬爱无暨的马克斯威尼早早救了!
自由的战士,马克斯威尼,你表示出我们人类意志的权威如此伟大!
我感谢你呀!赞美你呀!“自由”从此不死了!
夜幕闭了后的月轮哟!何等光明呀!……
(三)《女神》的诗人本是一位医学专家。《女神》里富有科学的成分也是无足怪的。况且真艺术与真科学本是携手进行的呢。然而这里又可以见出《女神》里的近代精神了。略微举几个例——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序诗》)
否,否。不然!是地球在自转,公转,(《金字塔》)
我是X光线的光,
我是全宇宙的energy[21]的总量!(《天狗》)
我想我的前身
原本是有用的栋梁。
我活埋在地底多年,
到今朝才得重见天光。(《炉中煤》)
你暗淡无光的月轮哟!……早早同你一样冰化!(《胜利的死》)
至于这些句子像——
我要把我的声带唱破!(《梅花树下醉歌》)
我的一枝枝的神经纤维在身中战栗。(《夜步十里松原》)
还有散见于集中的许多人体上的名词如脑筋、脊髓、血液、呼吸……更完完全全是一个西洋的doctor[22]的口吻了。上举各例还不过诗中所运用之科学知识,见于形式上的。至于那讴歌机械的地方更当发源于一种内在的科学精神。在我们的诗人的眼里,轮船的烟筒开着黑色的牡丹,是“近代文明的严母”,太阳是亚波罗坐的摩托车前的明灯;诗人的心同太阳是“一座公司的电灯”;云日更迭的掩映是同探海灯转着一样;火车的飞跑同于“勇猛沉毅的少年”之努力。在他眼里机械已不是一些无声的物具,是有意识有生机,如同人神一样。机械的丑恶性已被忽略了;在幻象同感情的魔术之下它已穿上美丽的衣裳了呢。
这种伎俩恐怕非一个以科学家兼诗人者不办。因为先要解透了科学,亲近了科学,跟它有了同情,然后才能驯服它于艺术的指挥之下。
(四)科学的发达使交通的器械将全世界人类的相互关系捆得更紧了。因而有史以来世界之大同的色彩,没有像今日这样鲜明的。郭沫若的《晨安》便是这种[23]的证据了。《匪徒颂》也有同样的原质,但不是那样明显。即如《女神》全集中所用的方言也就有四种了。他所称引的民族,有黄人,有白人,还有“有火一样的心肠”的黑奴。他所运用的地名散满于亚、美、欧、非四大洲。这在西洋文学里不算什么,但同我们的新文学比起来,才见得是个稀少的原质,同我们的旧文学比起来更不用讲是破天荒了。啊!诗人不肯限于国界,却要做世界的一员了;他遂喊道——
晨安!梳人灵魂的晨风呀!
晨风呀!你请把我的声音传到四方去罢!(《晨安》)
(五)物质文明的结果便是绝望与消极。然而人类的灵魂究竟没有死,在这绝望与消极之中又时时忘不了一种挣扎抖擞的动作。二十世纪是个悲哀与兴奋的世纪。二十世纪是黑暗的世界,但这黑暗是先导黎明的黑暗。二十世纪是死的世界,但这死是预言更生的死。这样便是二十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的中国。
流不尽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