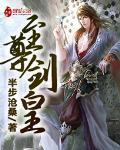奇书网>春宽梦窄包邮价格 > 土囊呤(第2页)
土囊呤(第2页)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历史上,末代皇帝丢了江山之后,含愤自杀的寥寥可数。因为“知耻近乎勇”,若是一无廉耻,二乏勇气,就不会像明朝的朱由检那样煤山自缢,选择“殉国”一途。退而求其次,就是变装出逃。可是,出逃又谈何容易!到了穷途末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变成“率土之滨,莫非敌臣”了,往往是没有跑出多远,就被人家递解回来。于是,就出现了第三种选择,索性白旗高举,肉袒出降。这在大多数亡国之君,被认为是较为理想的。他们的逻辑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如果新的王朝宽大为怀,只要脸皮厚一点,还有望混上个“安乐公”“归命侯”当当,可以继续过那种安闲逸豫的日子。
其实,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甜蜜蜜的幻想,历史上多数“降王”的日子都不好过。当了亡国贱俘以后,如果像前秦苻坚、南燕末主慕容超、大夏王朝的废主赫连昌、后主赫连定那样,很快就都死在胜利者的刀剑之下,所谓“一死无大难矣”,倒还罢了;假如类似南唐李后主和北宋徽宗、钦宗父子这样,投降之后沦为俘虏,一时半刻又能喘上几口活气,那就免不了要受到终身縻押,心灵上备受屈辱不算,身体上还得吃苦受罪,结果是“终朝以眼泪洗面”,那又有什么“生趣”之可言呢!
三
历史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像宋太祖不问任何情由,只因“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便蛮横地灭掉南唐一样,金太宗攻占汴京,扑灭北宋,也是不讲任何情由的。而且,南唐的李后主和北宋的道君皇帝,都是诗文兼擅,艺术造诣超群,“好一个翰林学士”;却都不是当皇帝的“胚子”,他们缺乏那种雄才大略和开疆定国的本领。最后,只能令人慨叹不止:“做个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做君王。”巧还巧在,他们败降之后,又分别遇到了宋太宗和金太宗两个同样凶狠、毒辣、残忍的对手。当宋太宗用牵机药毒死李后主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料到,一百五十七年之后,他的五世嫡孙赵佶竟瘐毙在金太宗设置的穷边绝塞的囚笼之中。
说来,历史老仙翁也真会作弄人。它首先让那类才情毕具的风流种子,不得其宜地登上帝王的宝座,使他们阅尽人间春色,也出尽奇乖大丑,然后手掌一翻,啪的一下,再把他们从荣耀的巅峰打翻到灾难的谷底,让他们在无情的炼狱里,饱遭心灵的折磨,充分体验人世间的大悲大苦大劫大难。
但这样说,绝不意味着赵佶之流的败亡,自身没有责任。恰恰相反,他们完全都是咎由自取。可以说,赵佶的可悲下场,他的大起大落,由三十三天堕人十八层地狱,受尽了屈辱,吃透了苦头,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
记得小时候读过一本《帝鉴图说》,据说是明、清两朝皇帝幼年时的史鉴启蒙课本。其中选载了五十多个帝王的善政与恶行。在三十六件恶行里,宋徽宗自己占了三件。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信用奸人,穷奢极欲。这个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无道昏君,在位二十五年间,整天耽于声色狗马,吃喝玩乐,荒**无度。凡是在这些方面能够投其所好的人,不管是朝中大臣,宫廷阉宦,还是市井无赖,他都予以信任和重用。蔡京奸贪残暴,无恶不作,却能四次人相,祖孙十一人同时担任朝廷命官。王黼多智善佞,五年为相,所蓄金帛珍宝和娇姬美妾之多,几乎能与皇帝媲美。宦官童贯和梁师成,一个掌握兵权达二十年之久,成为北宋末年的最高军事统帅;一个掌管御书号令,权势熏天,连宰相都得把他当作父亲看待,因而有“隐相”之称。他们互相勾结,排斥异己,操纵了朝中的大权。而徽宗则乐得优游岁月,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蔡京还挖空心思,从《易经》中找寻根据,以“丰亨豫大”相标榜。说当前朝廷的宫室规模,同国家的富强、君德之隆盛不相配称,极力怂恿徽宗要“享天下之奉”,勿“徒自劳苦”。他们知道徽宗特别嗜好奇花美石、珍禽异兽,便勒令各地搜括、进献,一时间,贡奉珍品的船只在淮河、汴水中首尾相接,称为“花石纲”。当这些花石运到都城之后,蔡京又鼓动皇上兴建豪华的延福宫,分门别类放置。并用六年时间,在平地修起一座万岁山(亦名艮岳),周长十余里,高峰达九十步。山间布满了亭台楼阁,开掘了湖沼,架设了桥梁。他们确定了一条营造的标准:“欲度前规而侈后观。”就是说,其富丽堂皇不仅达到空前,还要能够绝后。
童贯从市井中物色到一个善于饲养禽鸟的薛翁。他人园之后,便仿效皇帝出游的架势,每日集中大量车舆卫队,清街喝道,在万岁山中巡游。车上张设黄罗伞盖,并安放巨大的盘子,满盛着粱米,任凭过往的禽鸟随意啄食。飞禽饱食后便翔集于山林之中,自由来去,绝对不许捕杀。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飞禽习惯了与游人狎玩,立于伞盖之上也不再畏惧。一天,徽宗临幸万岁山,霎时,有数万只禽鸟听到清道的声音,迅速飞集过来,铺天盖地。薛翁于御前奏报:“万岁山禽鸟迎驾。”徽宗喜上眉梢,当即委之以官职,并给予厚重的赏赐。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看过一出名叫《皇帝与妓女》的新京剧。剧作家宋之的根据《三朝北盟会编》《宋人轶事汇编》和《李师师外传》,把“靖康之祸”中徽、钦二帝伙同朝中的投降派,残酷镇压主张抗金的将领和民众,甘心为侵略者效劳的种种恶行搬到了舞台上。妓女李师师和宋徽宗以及朝中几个奸臣、抗金将领吴革、代表民众的李宝等都有交往,剧情便以她为线索一步步地展开,再现了当时错综复杂、内外交织的矛盾、斗争。当然,由于戏剧本身是文学创作,有些情节出于合理想象,未必与史实尽合榫卯,但它往往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集中,更典型。五十年过去了,剧中有些情节至今还深深地印在脑子里:
金兵攻下开封之后,钦宗签下了降表,吴革率兵勤王自陕北前线归来。就在他节节胜利,杀得金兵马仰人翻,即将活捉敌军渠帅的关键时刻,朝廷却以“破坏和议”的罪名,要捉拿他归案。吴革“情愿做不忠之鬼,不愿做亡国之臣”,抗命杀敌,结果,却被伪装助阵、实为内奸的投降派范琼从背后施放冷箭射倒。当时,台下观众悲愤填膺,传出一片唏嘘之声。
另一件事发生在金军的囚营里。羁押中的道君皇帝,像个丑角演员似的,强装出笑脸,陪同金军将领们踢球打弹,斗鸡走狗,或者吟咏歌功颂德的诗篇,背地里却心态悲凉,愁苦万状。这一切,被天真善良的妓女——其时也遭捕人狱,陪伴歌舞的李师师偶然见到了。出于同情和信任,她便把刚刚获得的一个信息透露给他。原来,吴革在结义弟兄李宝等的悉心护理下,箭伤得到了康复,他们策划在元宵节时,趁着金人歌舞狂欢之际,带领一些勇士潜人金营,同三千在押囚犯里应外合,刺杀金军统帅,大张义旗,重整旗鼓。届时,李师师通过献歌侑酒,加以配合。
可是,李师师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无道又无良的亡国之君,竟然把她出卖了。结果,一场精心筹划的义举,最后以吴革等被捕杀、李师师当场自刎而告终。赵佶及其左右侍臣的“逻辑”是:万一举事失败,他们必然会受到牵累,到那时,想要屈辱苟活亦不可得;即使侥幸成功,最后起义军把金人赶出去,得利的也不是他这个太上皇,而是南朝的现任天子。综上分析,于是得出结论:“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够了,无须再罗列其他了。看来,让这样一个无道昏君,在荒寒苦旅中亲身体验一番饥寒、痛苦、屈辱的非人境遇,也算得是天公地道了。
四
其实,对一般人来说,苦难本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是锻造人性的熔炉。一个人当缺乏悲剧体验时,其意识往往处于一种混沌、蒙昧状态,换句话说,他们与客观世界处于一种原始的统一状态,既不可能了解客观世界,也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而对于赵佶之流来说,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
一则故事说,徽宗当了太上皇之后,逃避金兵,跑到镇江。这天,游览金山寺,见长江中舟船如织,因向一位禅师问讯:江上有多少只船?禅师答说,只有两只,一只是寻名的,一只是逐利的,人生无他物,名利两只船。显然其中寓有讽喻的深意。但在当时的赵佶,是无法理解的。史载,李煜在囚絷中,曾对当年错杀了两个直臣感到追悔。且不知赵佶经过苦难的折磨之后,对于自己信用奸佞、荒**误国的行为,有没有过深刻的反思。
据传,他在五国城写过这样一首感怀抒愤之作:
杳杳神州路八千,宗枋隔绝几经年。
衰残病渴那能久,茹苦穷荒敢怨天!
古代圣人有一句很警策的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看来,岂“敢怨天”云云,倒还算得上一句老实话。
有资料记载,钦宗赵桓在流放中也填写过一首《西江月》词:
历代恢文偃武,四方晏粲无虞。权奸招致北匈奴,边境年年侵侮。一旦金汤失守,万邦不救銮舆。我今父子在穹庐,壮士忠臣何处?
词句直白、浅露,水准不高,达意而已。但是,如果真的出自赵桓之手,倒是从中可以看出,他在历经劫难之后的些微觉醒。
1135年4月,赵佶卒于五国城,年五十四岁。二十六年后,赵桓也在这里结束了他屈辱的一生。生前,他们都曾梦想能够生还故国。《纲鉴易知录》载,在燕山时,徽宗曾私下嘱托侍臣曹勋,要他偷逃回去转告康王赵构(即宋高宗):便可即位,救出父母。羁押中的康王夫人邢氏也曾脱下金环,使内侍交给曹勋,说:请为我向大王转达“愿如此环,得早相见”的愿望。曹勋回去以后,即向高宗奏报,应迅速招募勇士绕行海上,潜人金国的东部边境,偷偷接奉上皇从海道逃归。结果,不但意见未被采纳,曹勋本人还被放往外地,九年不得升迁。原来,这里面有一种非常微妙、隐秘的内情。
高宗赵构乃徽宗第九子、钦宗的弟弟。1127年4月,徽、钦二帝被俘北去,5月,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后来迁都临安,建立了被称为南宋的小朝廷。他同乃父乃兄一样,也是最怕同金兵交战的。他所信用的汪伯彦、黄潜善和充当金人内奸的秦桧,都是些主张逃跑和屈膝投降的人。除此之外,他还有一块心病,就是如果抗金成功,父亲、哥哥就会返回,那实在是难以接受的事实。明人陈鉴有诗云:
曰短中原雁影分,空将儇子寄曹勋。
黄龙塞上悲笳月,只隔临安一片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