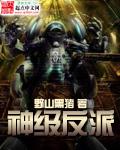奇书网>春宽梦窄豆瓣 > 生命的承诺(第2页)
生命的承诺(第2页)
霞客走的地方更多,却唯独漏掉了张家界。古代许多寄兴林泉、钟情山水的诗人,如谢灵运、李白、王维、孟浩然、陆游等,都和此地缘悭一面。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往者已矣,但来者可追。今天,张家界的朋友正在做有效的补偿工作。比如,他们在著名景点黄狮寨的最高处,修了一个六奇阁,凭栏远眺,可以纵览山、水、云、石、动物、植物之奇观,并请羊春秋教授撰联:“名动全球到此真堪三击节,势拔五岳归来不用再看山。”隽景佳联,交相辉映。
“但肯寻诗便有诗”,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我很欣赏他们的这番话:“在几千年的秦风汉雨中,我们的祖先错过了太阳,今天,我们再不要错过月亮与星辰。要在我们的手里,把张家界的山水文化推上一个新的层次。”
五
是的,同一切资源一样,文化资源颇有待于开发。我从他们提供的资料中,得知这里有张良墓,据道光三年修纂的县志记载,张良得黄石公授书后,从赤松子游,殁后归葬于此。听说,张家界的得名即与此有关。据我所知,陕西留坝县有祭祀张良的留侯祠,门旁竖有“留侯辟谷处”的石碑,里面还有回云亭,取功成身退,返回云山之意。这也同样是传说。似可两说并存,因为不大可能也没有必要,硬要去对它辨个虚实真伪。
张家界还流传着当年秦始皇驱山填海,把赶山鞭留在这里,化为金鞭岩的神话。此外,还有惟妙惟肖、石相天成的“儒士藏书”“天书宝匣”等景观,都引起了四方游客的浓厚兴趣。
一时,我也发思古之幽情,即兴为上述两个石景题写了三首七绝:
祛老天书匿碧虚,山深未走始皇车。
可怜不得长生术,难免沙丘伴鲍鱼!
秦火虽严却也疏,深山犹自有天书。
当时若果张良见,肯向桥头纳履无?
千载攻书立险峰,今时犹见古儒生,
凭虚欲问经纶策,地哑天聋唤不应。
第一首,是讥刺秦始皇的。说,为了逃避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士们把书册藏匿在高耸云天的大山里,其中就包括秦始皇到处寻觅的传授祛老长生术的天书。只是由于他的征车没有到过张家界,结果,长生术未能到手,最终难免死于河北的沙丘。“伴鲍鱼”也是用典。秦始皇死后,丞相李斯恐怕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不发丧,将尸首放在韫辕车里。当时正值暑夏,死尸腐烂发出了臭味。为了迷惑人,便把同样发臭的鲍鱼放在车上。这里有调侃的意味。
第二首,引用汉初名臣张良的故实。张良少时,曾在桥上为黄石公纳履,黄遂授以天书,说“读此则为帝王师”。后来,果然辅佐汉高帝刘邦得了天下。这里说,尽管经过一番“秦火”,深山里也还藏有天书。如果张良当时得以见到,那他就不必卑躬屈节地给黄石老人拾鞋纳履了吧?
我觉得,饱蘸历史的浓墨,在现实风景线的画布上着意点染与挥洒,使自然景观珞上强烈的社会、人文印迹,可以把游观者带进悠悠不尽的历史时空里,有助于他们从较深层面上,增强对现实风物、自然景观的鉴赏力和审美感。
六
当然,我也认为,即使没有任何社会人文景观,张家界也仍然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那种原生状态、荒情野趣,未经人工雕饰的自然天籁,同样是美的极致,是“心物婚媾后所产生的婴儿”(朱光潜语)。问题的症结所在,是如何珍惜它,保护它,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方天造地设的美的净土——这世间最宝贵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道理很简单,自然创造是一次性的,既没有副本,也不能复制。而且,自然美是易碎品,一旦毁坏了就万难补偿。而审美又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现象,没有人的欣赏,任何自然美都无从谈起。于是,就产生出一个悖论:发现了自然美,有时却意味着同它告别;欣赏的同时往往带来人为的践踏。就这个意义来说,张家界开发得晚,未始不是它的幸运。
在我的印象中,张家界是前所见到的管理得最好的风景区。可是,以后会怎么样呢?对此,我也表示了忧虑与担心。因为在其他很多地方,下述情况确实存在:人们向往于“诗意地居住”,但是,由于我们的行为并不那么“诗意”,“居住”的结果竟与初始的愿望相左。许多风景区都曾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而一经住进,很快就变成不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了。
临歧握别时,主人嘱咐我们放心,说:“为保护好张家界的生态环境,我们已经做了生命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