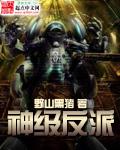奇书网>古游录 内在线看 > 南鹞(第1页)
南鹞(第1页)
南鹞
世人只知曹雪芹的《红楼梦》,而不知《废艺斋集稿》。这是曹雪芹另一部天才著作。雪芹是想用这部作品帮助贫穷、废疾无告的人们,学一种维生的技艺。《红楼梦》涉及绘画、医学、建筑、手工艺等,《废艺斋集稿》叙及图章、风筝、编织、脱胎、织补、印染、雕刻竹制器皿、扇股、烹调八类技艺,可见曹雪芹博于技艺。
写《废艺斋集稿》是由《南鹞北鸢考工志》起意的。曹雪芹的朋友于景廉从军伤足退伍后无以为生,儿女忍饥挨饿,向他求助,他亦困顿,遂教以风筝的技艺,后来于竟以为业,维持数口之家。由此,曹雪芹才产生“以艺济人”的意绪,遂援笔。他在自序中道:“意将旁搜远绍,以集前人之成;实欲举一反三,而启后学之思。乃详察起放之理,细究扎糊之法,胪列分类之旨,缕陈彩绘之要,汇集成篇,斯以为今之有废疾而无告者,谋其有以自养之道也。”
以艺活人,风筝已不是玩物了。刘氏风筝传承百年,恰合了曹雪芹撰写《南鹞北鸢考工志》的本意。世人皆认为汉字风筝在民初已失传,不料温州刘家还善其技,传承曹子遗风,亦见久藏的民间精神。而人生起承转合之处,恰是这些看似无用之物,给了生命一线希望。
一
“正月灯,二月鹞,三月麦秆作吹箫……”
初春,九山湖旁的树枝头还灰扑扑的一点新芽的影子也没有,松台山上早练的人们已汇入山下蝼蚁般的人潮。刘力坚用脚尖轻轻踢起一点尘土试试风,然后跑起来,手中的“福”字像它自己要飞一样,迫不及待地往空中一跃,手中的线被风快速地抽走,手随之潇洒地一扬,风筝就猛地扎下去又浮上来,而后扶摇直上,越飞越高,掠过树木,向着远处楼宇密集的街市飘去。
春天于刘力坚来说就是放鹞日,从东风浮动,一直到初夏的第一场透雨落下,春天似乎也是被他放走的。
“这是老祖宗传下的瘾。”五十三岁的刘力坚,身体圆墩壮实,皮肤黝黑,说完后,嘴角往上一拉,笑容天真纯然。这只福鹞是从他的曾祖父刘益卿手上传下来的,刘力坚已是刘氏风筝的第四代传人。
刘力坚拿一块石头将线轴压住,福鹞就稳稳地飘着了。红色的“福”字衬着老城像某种岁月的底版。从高处俯瞰老城,那些大街小巷像雕版师刻出的一条条河谷。每一条河谷里都流淌着五颜六色的河水,这些彩色的河水被两岸吸进去又吐出来。
刘力坚出生在福鹞下那片瓦屋像鱼鳞一样密集的街区——鼓楼街,那里曾是小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鼓楼街因鼓楼而得名。鼓楼也叫谯楼,建于五代后梁开平年间,是吴越王钱镠的儿子钱传瓘占据温州后,为确保长治久安,在修缮外城的同时,增筑了内城(也称子城)。原有东南西北有四道城楼,现在只存南门的谯楼了。明清以前,谯楼上设“铜壶刻漏”与“更鼓点”,朝夕按时“擂鼓打锣”遥传四方,内外赖以作息,故市井习称为“鼓楼”。鼓楼经历过宋赵构泛海而来南奔入城的灾难式荣耀,也经历过特殊年代被当作食堂烟熏火燎的难堪。现在的城楼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重修的建筑。城楼的飞檐把古城的气息渲染开来,唤醒历史的记忆。
“我家在鼓楼街九十号。清末民初,阿太和阿爷开‘永古斋’刻字店,阿太扎鹞阿爷刻字,现在是我姐在卖毛线。”
少年的刘力坚,常常穿过鼓楼到人民广场上放鹞。鹞吃着空气发出的“窸窸窣窣”声,在进入鼓楼洞时扩张成的大片“稀里哗啦”声,至今还在他的身体内回响。现在的鼓楼街商铺主要经营布料和绒线,主顾大多是中年以上的妇女,她们依旧扯布裁衣、买线织毛衣。这两种保留体温的东西,仿佛也可以保留岁月的流光。这条街也全凭这些老资格的人,才有了存在的理由。我甚至可以看到她们在触摸布料,然后把布料披在身上比试花色,或是在揉捻毛线,比对颜色的搭配,再询问价格。密密麻麻的脚,嘈杂喧闹的声音,连同那些缤纷的色彩,一起塑造着这条街的内部。当然,时代风向也在这儿体现——一间“玉珍”美容店和一家“香辣”小龙虾店。有了它们的存在,这条街安然自守的气息反而愈加浓了。旧日,这条街上还有一家寿衣店、一家制笔店和一家钟表店,如今自是不在了。
在时代的洪流中,有些事物永不复返,有些事物留了下来。刘家“永古斋”的雕版和刻字的工具都已不存,制作风筝的传统却像血脉一样一代一代延续了下来,尤其是汉字风筝——福鹞。《红楼梦》第七十回讲到“一个门扇大的喜字风筝”,《南鹞北鸢考工志》也提到“富非所望不忧贫”的七字风筝。曹雪芹的汉字风筝是写在纸上,刘家的汉字风筝运用了刻图章的镂空技艺,工艺更加精美,是传承也是创新。
太阳一寸一寸地高起来,刘力坚手中的线轴慢慢地往里卷,偶尔松一下,福鹞似一只倦鸟,慢慢悠悠地飞回来,颜色从远方的黑色,到黄色,到阳光直射下变成金色,到眼前就是红色的了。这种过程很意味深长,像穿越历史的时空。
这个镂空的巨大的“福”字,笔画胖胖的、圆圆的,不论在什么背景中,都是一种浸入式的,都会让人的情绪满溢着。此时,感觉到了汉字风筝有别于其他象形风筝的美——除了汉字书写之美,还有汉字语境之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二
刘氏风筝的始创者是刘力坚的曾祖父刘益卿。刘氏族谱上写着刘益卿出生于一八八六年,一九〇八年从永嘉碧莲到温州市区,在五马街一间拷绸店当伙计。
温州的五马街似上海的南京路,除了建筑风格相似,也是商号林立,那些从海上来的货物很快就到了五马街的商铺里。
一个二十岁靠双手的乡下人,在城里谋生就像“小细儿”(方言:孩子)爬楼梯,只能手脚并用一级一级地往上爬。伙计是第一级,第二级是站柜台。刘益卿暗中狠下功夫学习打算盘和写字。煤油灯把黑夜刨出一个洞,他就在这个洞里不停地练,算盘珠子把无数个黑夜敲碎,又拼成一个个字。刘益卿终于脱下短衫换上了长衫。
长衫如门面,一穿身份就不同了。操算盘的人也是一家店的主命,算盘珠子的“噼里啪啦”声也是银子滚进滚出的声音,平日里应酬唱和的人也多了起来,日子一久,刘益卿开始入不敷出。毕竟是一个只有长衫面子没有长衫里子的人,城市生活对他藏起的恶意,这个乡下人还没有觉察到。
转眼又是一年春天,天上的风筝也渐渐多了起来。清晨,刘益卿从租住的谢池巷出来往拷绸店走去。谢池巷是南朝诗人谢灵运来永嘉(温州)作太守时的登池上楼休憩清心的场域。谢灵运著名的山水诗《登池上楼》就产于此处。有千年文气积淀,场地也空旷,文人墨客常聚此雅玩。刘益卿在这儿落脚的几年里,看尽了城中富家子弟消磨时光的种种玩物,风筝自然也是其中一种。
“这个月必须断了那些吃喝应酬,儿子永生买字帖的钱也无着落了。”刘益卿脑子里盘桓着这个问题时,不觉脚下打了一个踉跄。与此同时,一只风筝猝然扎下来,啪的一声,一头栽在他的跟前。这是一只“沙燕”。巷子里跑出几个身着绸缎棉袄的富家少年,从他手里要走了这只“燕子”。玩风筝的人已消失在街巷的拐角,刘益卿还愣在原地,仿佛一转身,就放走了某种寻觅已久的东西。
有时候一些事物投映到心上,在某种心情的催化下,会起化学反应。就像此刻,刘益卿的心被这只“沙燕”啄了一下,而后一个念头就破壳而出——“何不扎鹞,赚富家子弟的钱呢?”一次偶然的视线聚焦,给了一个人生活的转机。
虽然相隔了一个世纪,在刘力坚的叙述里依然能够想象一个世纪前的那个春天刘益卿辞职的情状。
刘益卿走出谢池巷,朝五马街口的拷绸店走去,春风撩起长衫的下摆,裹住他的腿脚。这时,他才感觉到还是短打衫方便。而那件曾经让他引以为傲、花了很长时间求来的长衫,没了他一口气的支撑像被抽了骨一样软塌塌地躺在柜台上,看起来如此地单薄。谁都知道,不出几个时辰,就会有人穿上它,又让它神气起来。
三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刘家每日开合的眼皮把风筝放下又提起。刘益卿扎绘的风筝不仅养活了一家人,还在远近渐渐有了名声。扎绘风筝给这三口之家在城里深深扎下根来的力量。正如曹雪芹在《南鹞北鸢考工志》自序中说及于景廉那样:“风筝之为业,真足以养家乎?数年来老于业此已有微名矣。”
刘益卿把儿子永生送到“兴文里”一家叫“怀古斋”的刻章店做学徒,三年后学成出师。刘益卿就在鼓楼街租了一间二层的楼房,挂出了“永古斋”字号。儿子在前台刻章,父亲在后台扎鹞。曹雪芹的《废艺斋集稿》第一册叙述的刻印技艺和第二册的扎风筝技艺,在鼓楼街刘家并存着,也把这一家子的生活重组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
两年后,刘益卿就把鼓楼街这间二层楼房买了下来。刘家在小城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块薄土,过去的二十多年都是为此刻仔仔细细准备着。经过两代人的努力,永嘉碧莲的刘姓,分出的一支到了温州市区鼓楼街。刘氏族谱上用简短的一行字记录了这一支的走向。
小城的风把少女吹成妇人,把五马街拷绸店穿长衫的人吹走一个又一个,把刘益卿吹出了满头的霜迹,但那双手则更灵巧了。在一年“拦街福”(温州春天民间祈福的民俗活动)上,刘益卿扎了一个会自动喷水的风筝龙头摆在家门口让人欣赏。“龙喷水”在小城可是件稀奇事,刘家门口自是被前来参观的人围得水泄不通,刘益卿也被街坊邻居称为“风筝王”。
一个底层手艺人称王称霸,是要招嫉恨的。“永嘉县民教馆”要举办全城风筝比赛,这一场“风筝王”争霸赛,是冲着刘益卿来的。刘益卿想着,做什么样的风筝参加比赛呢?沙燕、大雁、老鹰、金鱼,这些都太平常了。
扎风筝的人也是追风的人,风筝的骨架也是风的骨架,从做第一根篾条开始,就在跟风对话。在刘益卿的耳朵里,竹篾刀划过竹片的“嗤嗤”声,和篾条在火上冒汗的“滋滋”声,都是风的声音。他在这些细碎的声音里捕捉风的方向,掂量风的轻重缓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