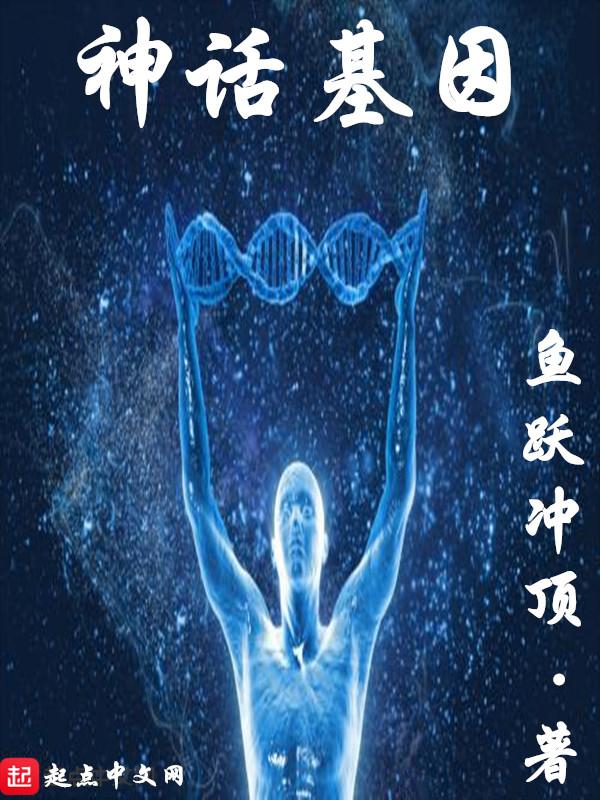奇书网>无名的裘德电影高清免费观看 > 3(第3页)
3(第3页)
“我是喜欢你!但我没有想到还要———还要喜欢得大过那么多……一个人要是有了我那样像是奉迎的感觉,那就不管什么法令,男人和女人住在一起也是通奸。瞧———我把它说出来了……你让不让我走,理查德?”
“你让我伤心,苏珊娜,这样纠缠不休!”
“咱们为什么不能同意使彼此自由呢?咱们订立了契约,咱们也一定能取消它———不是从法律上,当然。但我们能够从道德上,尤其是既然还没有新的利害关系,以孩子的形式,产生了需要互相照料的问题。以后咱们还可以做朋友,见了面谁也不觉得痛苦。啊,理查德,做我的朋友吧,有点怜悯吧!过些年咱们就死了,你把我从拘束中解脱一会儿还有什么人会当回事?我敢说你是认为我古怪,或者太神经过敏,或者荒谬什么的。唉———我生下来为什么要受罪,要是我生下来本没有害过什么人?”
“但是你害了———害了我。而且你发过誓要爱我。”
“不错———正是!我就错在这里。我老是错!宣了誓就像把你捆绑住受罪老要去爱一个人一样,就像宣了誓老是要信一种教义一样,那就像宣了誓老是要喜欢吃一种食物或者一种酒一样傻!”
“那你的意思是,离开我住着,你自己生活?”
“唉,要是你坚决要求那样,就那样。不过我的意思是跟裘德一起生活。”
“做他的妻子?”
“那要随我的选择。”
费乐生身子搐动了。
苏继续说下去:“她,或者他,‘如果让世界,或者他自己的那一部分世界,为他选择生活计划,那他除了类人猿的模仿不再需要别的本领了。’这,是J。S。穆勒的话。我熟读了这话。你为什么不能根据它行事?我愿意照着它办,永远。”
“我管什么J。S。穆勒做什么!”他呻吟道,“我只想过一种安宁的生活!你使我想起了,我要说我猜到了咱们结婚以前我从未想到的———你和裘德,原本就在恋爱,现在还在爱着。”
“你可以继续猜我怎么怎么样,既然你已经猜开了。不过要是像你猜想的那样,我还用得着求你让我离开去跟他一起生活吗?”
学校的铃声突然响起来,把费乐生从目前必须回答这一问题的困境中解救了,这个显然并未打动他,而她作为“令人信服的具有权威性的”论据,本是她在最后时刻失去了勇气,把它拿出来使用的。她开始如此令人困惑不解反复无常了,以至于他将要把这种一个妻子能够提出的最极端要求跟她的另外一些小怪癖扔到一起了。
他们那天早晨像往常一样到校,苏进了教室,他在那里不管什么时候转动眼睛都能通过玻璃隔断看到她的后头。当他接下去讲课和听课的时候,他的额头和眉毛由于集中思考的焦虑不安而搐动着,直到后来他终于从一张胡乱涂写的纸上撕下一块写道:
你的要求完全妨碍了我专心工作。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那是当真的吗?
他把纸条折得极小,交给一个小男孩去送给苏,孩子蹒跚走开进了那个教室,费乐生看到他的妻子转回身拿过便条,她看的时候低着她标致的头,嘴唇轻轻抿着,以防在这些孩子灼亮的眼睛下露出不适当的表情。他看不到她的手,不过她改变了姿势,一会儿那孩子回来了,什么回复也没带回来。可是,几分钟以后,苏班上的一个学生来到了,拿了一张类似于他那张的便条,上面只用铅笔写了这些字:
我真诚地抱歉说那是真的。
费乐生显得比先前更烦乱了,他的眉心又搐动起来了。十分钟后他叫起刚刚送信给她的孩子,送去另一信件:
上帝知道我不想以任何合理的手段阻挠你。我的全部心思是使你舒适快活。但是我不能同意你去跟你的情人生活在一起这样荒谬的意图。你将失去所有人的尊重和敬意;而我也将如此!
隔了一段时间以后同样的角色在那边教室扮演了,回音来了:
我知道你对我的好意。但我不想要被人尊重。使得“人性向最丰富的多样性发展”(引自你的洪堡)对于我的心思远在尊重之上。无疑我的趣味是低下的———按你的观点———无望地低下!如果你不让我去跟他,你能同意我这个要求吗———允许我在你的家里以分居的方式住着?
对此他未予回复。
她又写道:
我知道你的想法。但是你不能可怜可怜我吗?我乞求你可怜可怜,我哀求你发发慈悲!如果我不是差不多被我不能忍受的东西逼迫到了这地步,我不会要求的!没有可怜的女人还会比我更希望夏娃不堕落,以便(如原始的基督徒所相信的)一些无害的草木样式可以栖息在乐园。不过我不废话了。善待我吧———即便我没有善待过你!我将离开,去国外,任何地方,永远不打扰你。
将近一个小时过去了,然后他回了一个答复:
我不愿让你痛苦。你是深深知道我不愿!给我一点时间。我倾向于同意你最后的要求。
她来了一行字:
由衷地感谢你,理查德。我不配得到你的好意。
整整一天费乐生通过玻璃隔断茫然昏花地看着她,他觉得他像不认识她的时候一样孤独。
但是他说话算数,同意她在家里分居。起初,他们在吃饭时见面的时候,她看来好像在新的安排下更镇静自若了,但是他们的状况的使人厌倦对她的性情产生了影响,她天性的每根纤维都像竖琴一样似乎绷紧了。她含糊杂乱地说话以阻止他贴切中肯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