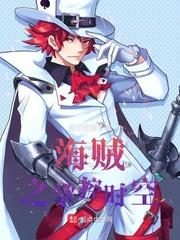奇书网>本草春石斛有限公司 > 不 朽(第1页)
不 朽(第1页)
不 朽
——《本草纲目》五百年
从那叠书稿中随意抽出一卷,粗略翻了几页,王世贞悄悄吸了口凉气,温和中带些矜持的神情慢慢严肃起来。他抬起头,看着坐在自己对面的人。那一身褐色布衣的清癯老者正怡然地品着茶,不知怎的,此刻在王世贞眼中,他原本就得体大方的举止现在更加洒脱,大袖挥动之际似乎还带出了些云烟。
他出了一会神,重又低下头去,端坐正了,仔细捧读起来。也不知过了许久,他终于低叹一声,轻轻放下书卷,对那老人拱了拱手,微笑着问道:“濒湖兄著这部大书,花了多少时间呀?”
老人李时珍——濒湖是他的号,闻言拈须笑道:“大人这话问得我得好好算算了。”沉吟片刻,他接着说:“当初我决心写这《本草纲目》时,不过三十出头吧,一转眼,现在可就是七十三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时日无多了哪。”
“濒湖兄仙风道骨,阎王爷也得卖你几分面子吧。”王世贞插了一句,“如此算来,为这部书,竟然耗了濒湖兄四十多年功夫?我真正是钦佩至极!”
“大人过奖。其实也没那么久,我六十岁那年就已经差不多完成了,最近这些年不过只是核对补充罢了。”
“我粗读几条,便发觉书中引据很多,上至坟典下及传奇,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凡有相关无不备采,濒湖兄涉猎之广,实令我等惭愧。”说此言时,王世贞满脸真诚,绝不是客套。
“山野之人哪敢在大人驾前献丑。我这辈子,也是奇怪,只是喜欢看些杂书,圣人的经典却是不甚精通,该惭愧的是我啊。”李时珍也是言出肺腑。
顿了一顿,他离座走到王世贞面前,深深作了一个揖,神情庄重地说:“时珍自知学术浅薄,难登大雅,故此不揣冒昧,想烦劳大人作一小序,希望此书能借大人妙笔流传后世,多少于世人有些裨益,时珍此生便心愿足矣!”
王世贞连忙起身,扶起老人,说道:“濒湖兄不必多礼!”
“……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复者芟之,阙者缉之,讹者绳之。旧本一千五百一十八种,今增药三百七十四种,分为一十六部,著成五十二卷。虽非集成,亦粗大备,僭名曰《本草纲目》……”
在序中,王世贞用李时珍自己的话,对《本草纲目》的成书过程与规模做了扼要的介绍,当然也不忘记了一笔:“愿乞一言以托不朽。”
在李时珍,还有当时所有人看来,这句话是十分合理的,谁都相信,如果开卷有了王世贞这篇六百多字的序镇着,《本草纲目》便多了几分“不朽”的把握。
因为王世贞是当时的文坛泰斗,独领大名二十年。《明史》载:“(王世贞)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若得如此大腕“片言褒赏”,自然能“声价骤起”,李时珍“乞一言以托不朽”的想法十分正常。
相比王世贞如日中天的名声,医者李时珍自然有自惭形秽的感觉,一定会觉得这辈子不算很成功,尽管他这一生已经活人无数。
李时珍弯下腰去请王世贞写序的那一刹那,他面前的青砖上,会不会幻出当年父亲那因失望而灰暗无光的眼睛呢?
李时珍的父亲李言闻,原本对这个聪明的儿子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指望他光耀李家门楣,好好为祖先出口气。
一开始的迹象表明,这个希望是很有可能实现的。
李时珍十三岁便考中了秀才。
每日清晨,听着儿子还不脱稚嫩的读书声,李言闻便说不出的舒坦。他觉得世代为医的李家或许在他儿子这一代便能转运了,一条通往京城、通往金銮殿、再通往衙门大堂的金光大道已经铺在时珍的书桌上。他不觉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一个四处跑江湖的铃医,每日提着药箱摇着串铃——又叫虎撑的——栉风沐雨挣口饭吃,常常被当成卖嘴的骗子,好不容易在世人鄙夷的眼光中养大了自己;虽然他自己倒也争气,把老人家的手艺发扬了,几十年功夫好歹熬成了一方名医,可其中的辛酸他是实在不敢回首。自从生下时珍,他便下了决心,便是倾家**产也要把这孩子送上正途,可绝不能让他再走祖祖辈辈的老路了,为此他还费了很大力气,托人让李时珍拜到了中过进士的一位老先生门下。十三岁中秀才,老天开眼,这小子争气啊。
信心十足的李言闻就等着乡试、会试,等着时珍一步步沿着他梦想的脚印走下去,走出头。
十六岁,乡试不中。
十九岁,再不中!
二十二岁,还是不中!
李言闻蒙了,这屡战屡败的沮丧后生,当真是那个早慧好学的时珍孩儿吗?怎么越读越不济了呢?
李时珍当然承受着更大的痛苦。第三次乡试铩羽之后,他觉得青春紧迫,有必要对自己的未来做个现实的最终规划了。几个不眠之夜后,他终于向父亲提出了自己的打算。
“你要学医?”李言闻几乎要咆哮了。但看着儿子通红的眼睛和憔悴的脸庞,他又不忍开口责骂。良久良久,他抬头看看天,长长叹了口气,黯然道:“明天,你随我出诊吧!”语气嘶哑,比吞了满口的黄连还要苦涩。
心里猛然空****的李言闻没有多怪儿子,他看得出,时珍已经尽了力。他又记起,时珍自小看到本草方书便两眼放光,精神头比读圣人书还要大,药性歌诀更是不用多教便背得比诗词还顺溜。想到这他又叹了口气,把这一切都归结于祖宗的风水不好,牢牢把李家一脉圈在了医药这个没前途、走不到头的行当之中。
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任何一门技艺,无论你学得多精妙,都是没前途、走不到头的——
都不是正途。
“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成就德行是主要的,居上位;懂得技艺是次要的,居下位——这是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句名言。
儒家学者的气魄很大,动不动就挽起袖子准备治国平天下;他们一生钻研的,也是大济苍生的学问。注意,是“大济”,要大,要大到能涵盖天下,而不是零零碎碎的一技一艺。打个比方,任何一个工匠,泥水工,或是木匠、瓦匠,都不能独力造成一座房子,即使每个匠人在各自领域都是绝世天才;造房子绝少不了一个能统筹全局、调度一切的总工程师。衡量这个工程师水平高低的标准是规划是否合理、目光是否远大、指挥是否得力,而不是他能不能使得一手好刨锯。正如柳宗元所述,那个连自家床坏了都不能修理的梓人照样是个不可或缺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