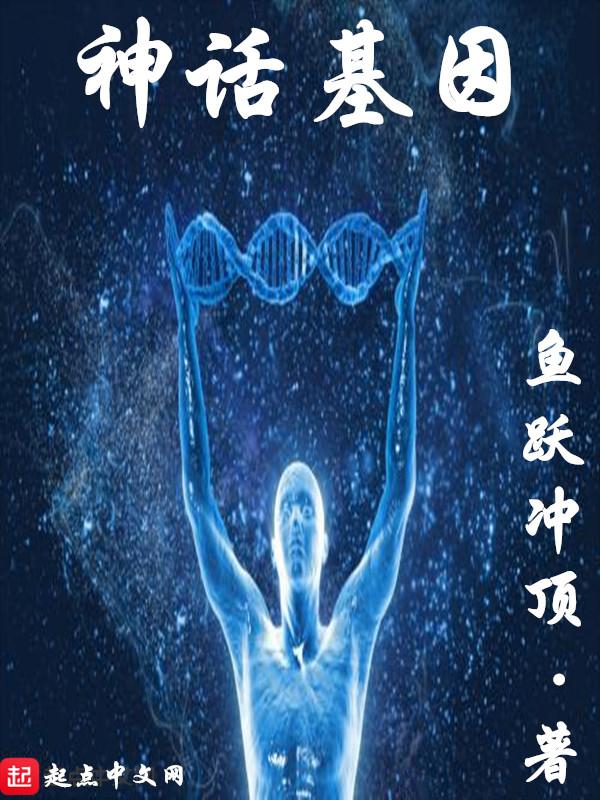奇书网>本草春秋读后感 > 亡天下(第3页)
亡天下(第3页)
牙齿咬得格格响,凡我汉人,谁能忘得了血流成河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我顾炎武更忘不了被砍去一条右臂的老母亲与死难的两个弟弟!
但我们绝不是为了一家一国而反抗,而是为了我们整个大汉民族——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再太平的天下,也是沦陷的天下!
“人人可出,我顾炎武不可出!”
是的,我们已经很清楚大局已定,但我们铁了心继续做遗民,做一只撼山到死的前朝蝼蚁!
傅山慢慢斟上了酒,两碗重重一撞,二人又是一饮而尽。
其他遗民呢?
“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
说这句话的是另一个著名的遗民,曾起兵抗清,“濒于十死”的黄宗羲。
康熙十七年(1678年)开的那次博学鸿词试,同傅山一样,黄宗羲也受到了举荐,当然他也是力辞不就的。次年,朝廷又像当年征聘顾炎武那样请他的弟子修史,黄宗羲没有反对。又次年,有人直接举荐他参与修史,他虽然仍旧托病力辞,但派去了自己的儿子代替,并在给清朝官员的书信中写道:“羲蒙圣天子特旨召入史馆……”他难道忘了自己从前口口声声骂清朝统治者吗?
晚年的黄宗羲,在书信碑铭中,称清朝为“国朝”、清军为“王师”。
尽管他如此言行有些是敷衍,正如他所说“生此天地之间,不能不与之相干涉,有干涉则有往来”,但从遗民的立场来看,黄宗羲终究是晚节有亏。
晚节有亏的遗民数量很多,戴名世曾云:“明之亡也,诸生自引退,誓不出者多矣,久之,变其初志十七八。”当初很多人只是一时激愤做了遗民,其实过不得苦日子,是经不起多少时间考验的。袁枚《子不语》载,明亡之时,有个遗老想殉难,又怕刀绳水火的痛苦,便恣情于女色,终日荒**,想就此爽死,不料好几年也死不了,只是断了筋脉,头弯腰驼匍匐而行,被人呼为“人虾”。
清廷脚跟初稳就大开科举,对有名的遗民更是优待,只要马马虎虎报个到,三笔两笔随便考一下,便有好官帽伺候。一时间,不少以“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为榜样的“隐士”纷纷下山,时人有诗讽曰:
“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首阳山,为当年伯夷叔齐隐居处)
相比这成群结队的“伯夷叔齐”,黄宗羲还是坦坦****的,他始终没有投向清朝,不过是说了一些好话罢了,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实话——难道康熙的文治武功真的不值得称道吗?
遗民不易做。其中甘苦,黄宗羲深有体会:“年运而往,突冗不平之气,已为饥火所销铄。”“落落寰宇,守其异时之面目者,复有几人?”
遗民最可怕的敌人不是饥火,也不是异族,而是岁月的消磨,尤其是太平岁月的消磨。
单纯作为遗民,他不如早死。
史学大家陈垣先生曾经感叹:“遗民易为,遗民而高寿则难为。”
黄宗羲是清初遗民中甚为高寿的,享年八十六岁。
但黄宗羲毕竟是个豪杰,他晚年的变化绝不仅仅只是由于时间的消磨。更确切说,时间不仅能渐渐磨灭“突冗不平之气”,更是逼着他思考自绝于盛世的行为是否真的合理。
从思想家的角度来看,黄宗羲最终对清朝的承认,倒可理解为他正视现实,不一味闭眼逃避,从而虚耗了自己的才能,正所谓既不仕新朝又不废“当世之务”,才是“得中”之举(黄宗羲《谢时符先生墓志铭》)。以修史为例,出山只是因为“国可亡,史不可亡”,并不是替你清廷干活。
如果以完全不合作的标准,深究下去,其实很多苦节的遗民也达不到要求,与应征修史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你不是游幕为生吗?你为之出谋划策的幕主是谁?无论大小,还不都是大清的官员?如此岂不是等于间接的出仕?
你以开馆授童糊口吗?你教的是什么?还不是应清廷科举的制艺?你这不是为大清培养未来的官员吗?——你不教八股举业?好,那你就等着饿死吧,有几家会花闲钱供儿孙学你那些换不了功名的酸玩意?
别提别人的儿孙了,先想想自己的吧。遗民不畏死,更不畏穷,你自己是定能做到的,不开馆不游幕你也可以耕织苦守,可你就不担心几代下来,你家文脉就此断绝在泥田山路上吗?没有回报的苦学,能坚持多久呢?你们不是也已注意到这个危险而尴尬的苗头了吗:“(子弟们)今日不幸处此世界,事业文章都无用处”,“全副精神,忽尔委顿”,“恐其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陈确集》)。
你说你出家为僧道,无牵无挂,那岂不是等同于你所负的责任将随着你的化去而烟消云散,若人人都学你,还能等到复仇之日吗?
不说那么远,只看着眼前。你能受苦,但看着娇儿嫩女年复一年地随你做遗民,衣不覆体瘦骨嶙峋,忍气吞声面有菜色,你自是对得起先朝了,可你对得起他们吗?儿孙何辜,要生生世世随你受苦?
罢了罢了,这遗民还是我自己做了吧!长叹一声,滚下两行英雄泪。
终于,有遗民说出了他们中很多人的心声:“吾辈不能永锢子弟以世袭遗民也(徐狷石)”,遗民不世袭,让他们自己选择道路去吧。
何况后人自有后人的主见,你便是想禁锢也禁锢不了多久,落得想开些。连出名硬气的吕留良,在遗训中也只能吩咐一句:“子孙虽贵显,不许于家中演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