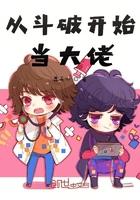奇书网>本草春秋是什么 > 是乃仁术(第3页)
是乃仁术(第3页)
他要借胡庆余堂将自己的名头打得更响亮,打成一块天字第一号的金招牌。
因为他需要更多的信誉,需要天下百姓的支持,他还要甩开手脚干一番大事。
国内虽然也有一些人对他不服气,利用他的靠山左宗棠与李鸿章的矛盾老想整治他,但胡雪岩心目中真正的对手,却是洋人。
他的眼光已经投射到了国外,曾说:“生意做得越大,眼光越要放得远。做生意的眼光,一定要看大局。你看得一省,就只能做一省的生意,看得天下,便能做天下的生意,看到外国,便能做外国的生意。”
胡雪岩把主力集中到了生丝买卖上,与洋人斗起了法。他的手法是以高于伦敦市场的价格大量收购,“遣人遍天下收买,无一漏脱者,约本银两千万两,夷人欲买一斤一两莫得”(《见闻琐录》)。头年,他掌握了形势:“夷人无可奈何,向胡说愿加利一千万买转此丝,胡非谓一千二百万不可。”洋人反复讨论后一致认为:“此次若为胡所挟,则一人操中外利柄,将来交易惟其所命,从何获利?”亏点钱是小事,但此风不可长,坚决不同意,宁愿今年不做中国的生丝生意。胡雪岩毫不在意,盘算着第二年再如此收购一回,洋人必将降服,不低头也得低头。
第二年,新丝上市,胡雪岩自己手头已然紧张,便“邀人集资购买”,不料“无人应者”。这下他再也无力操纵市场,“新丝尽为夷人买去,不复问旧丝矣”。
这一场较量,胡雪岩“两千万两出,一千两百万两归,家资去其半”。
原本这千把万两的损失还不至于彻底击垮胡雪岩的,但兵败如山倒,此时他的对手乘机四处放风,说其赔了血本,钱庄倒闭在即,慌得大小储户统统赶上门来提款,挤兑的人踩破了钱庄的门槛,连门框都被挤歪了。
别说已经有了亏空,便是再大的家当也经不起这般釜底抽薪的狠招;何况对手还落井下石,一边抽紧银根封住胡雪岩拆借的门路一边借助朝廷之势向他大额逼债。如此局面便不可收拾,庞大的胡氏集团,几乎在一夜间崩盘。胡雪岩所有的家产全部被折卖抵债,朝廷也下达了查抄的谕旨。
1885年12月30日,当一道批准“速将已革道员胡光墉(胡雪岩)家属押追着落,扫数完缴”,“将胡光墉原籍财产及各省寄顿财产查封报部,变价备抵”的圣旨传到浙江时,胡雪岩却已在二十四天前病死,一说是吞服鸦片自杀。
出现在抄家官员眼前的,只是一灯如豆、七尺桐棺。“所有家产,前已变抵公私各款,今人亡财尽,无产可封”——连封条都没地方贴,因为停棺的房子也是租来的。
胡庆余堂则早在头一年就被抵了债,落入了恭亲王奕訢的亲家文煜的手里。
这年离胡庆余堂开业,不过只有短短七年。
尽管胡雪岩不用多时就将胡庆余堂经营得名声赫赫,以至于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之说,被誉为“江南药王”,但他毕竟只是个商人。
他不懂医人之术,更不明医国之术。所以虽然他有“做生意赚了钱,要做好事”的仁心,也有相当可观的资本,却迅速一败涂地。
他看不清全局。尽管他说眼光一定要放得远,但他却忽视了自己的身后,看不清同胞同行其实是一盘散沙,各自钩心斗角,绝无法协同作战;也没看清远方,不明白洋人背后有各国雄厚的财力撑着腰,妄想以一人之力挑战全球列强。
病症未清,便鲁莽施药,安能不败?
根本还在于,胡雪岩只看到了外邪入侵——他征战生丝业,便是为了抵抗洋人的经济掠夺——但看不见真正的病根却在国门之内。
国有病,人知否?
整个大清王朝,已是从内里烂起,正气不扶,外邪岂能祛除?
仅仅从商业角度看看祖国萎靡无力带来的后果吧。曾有人评论:“光墉虽多智,在同光年代……海陆运输,利权久失,彼能来我不能往,财货山积,一有朽腐,尽丧其资。”
蒙着眼开方,头痛治头脚痛医脚,你刀来我剑去,只是误事的庸医所为,不仅于事无补,往往还雪上加霜。
时人汪康年云:“江浙诸省,于胡败后,商务大为减色,论者谓不下庚申之劫。”(指1860年江浙太平天国之难)
也怪不得胡雪岩,他原本便不是苍生大医。以全局来看,他只是一味药,一味为己为人强自出头抵御强大外邪的药——虽说商人本性是为了谋利,但胡雪岩此举也有保护蚕农免受洋人压榨之意。
时局危如累卵,如此一味药独立支撑,不过是白白入水火煎熬罢了。
那么面对危局,担当治国重任的苍生大医又有何术能妙手回春呢?
他们正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没精力顾及一个商人的死活。
他们中的很多人倒也是用药如用兵的高手。
几十年前,鸦片危机越来越严重时,有不少人建议朝廷:操纵洋人,可以从禁止中国的茶叶、大黄出口下手。因为据他们了解,洋人如果数月不吃这两样,就会双目失明、肚肠堵塞,甚至丧命,所以只要朝廷断绝供应茶叶、大黄,各国必向大清乞求救命。
即使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在《通谕各国夷商稿》中也庄严劝告:“内地茶叶大黄二项,为尔外夷必需之物,生死所关,尔等岂不自知?”
他们的医术学得甚妙。大黄,因其泻下力猛,药性如大将“斩关夺门”,所以别名“将军”——以将军守国,名正言顺,想来应该是稳如泰山的。
很快他们便惊奇地发现洋人原来不吃大黄也可以活得欢蹦乱跳的。挨够打后,大医们终于醒悟过来,绞尽脑汁开出了一张又一张的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