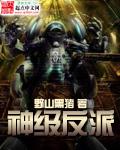奇书网>本草春秋是什么 > 亡天下(第1页)
亡天下(第1页)
亡天下
——遗民不世袭
“不提这些了。”土窑内昏暗的烛光下,傅山显得十分苍老,毕竟他已经是六十五岁的人了。抹了抹眼角,他强笑着对面前的客人说:“还是尝尝我自己再制的汾酒吧。”
顾炎武两眼通红,垂着头,像是没听到傅山的话,犹自喃喃道:“这都二十七年了,二十七年了啊……”直到傅山的儿子傅眉在他们面前摆上几样菜蔬与一个酒坛才回过神来。他抬起头看着傅山——傅山长叹了一口气,又抹了抹眼角。
两人一时无言,只是默默地看着傅眉往他们酒碗中倒酒。灯下,那酒颜色金黄透亮,又微带些青碧,甚是可爱。
酒碗在手,二人相视良久,想说些什么又不知该说什么好;最终还是傅山开了口,他涩声道:“这第一碗酒,让我们为大智和尚干了!”
“无论是不是如传言中那样自沉,能死在惶恐滩头,九泉之下他也该含笑了。”顾炎武举碗在手,又出了神,但很快他便一声轻喝,“干!”
两碗重重一撞,二人一饮而尽。空碗互相一照,却发现对方都是满面泪痕。又是一阵沉默。忽然,顾炎武咦了一声,拿过酒坛边仔细端详边问傅山:“此酒毫无刺口之感,甜绵中又有一股草木清香,余味无穷,绝不是寻常汾酒。我奔命天下这么些年,各地的好酒也算喝了个遍,却从未领略此种滋味,刚才傅兄说这是再制之酒——”
傅山冷峻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些笑意,拿过酒坛又为顾炎武加满了酒,这才拈须笑道:“这是我取上好汾酒,加入竹叶、砂仁、当归、丁香、陈皮、木香等十二味中药浸泡而成的,多少能减去一些酒毒,还添了些益气活血、暖胃舒肝之效;用了个老名号,也称之为竹叶青。”顿了顿,他补充道:“顾兄是知道我傅某嗜酒如命的,可毕竟黄土埋到了下巴,有时实在喝不动了;但不喝酒我更难熬,没办法,只好弄些花名堂,好歹还能多喝几口,倒也不是为了养生——你我难道还怕死吗?”
“是啊,我等如此无能,其实二十七年前就该死的。”顾炎武又垂下了头,像是在认真观察着酒的颜色。
“二十七年了啊,二十七年了啊!三十八岁尽可死,栖栖不死复何言……”这回是傅山开始了念叨。
窑外寒风呼啸,尽管门窗紧闭,但不时有几缕从宽宽窄窄的缝隙间挤入。烛焰吃力地吞吐着,使三人的影子在龟裂的泥壁上忽而蜷缩,忽而伸展,忽而破碎,忽而黯淡。
大明亡国二十七年了。
这是清康熙十年(1671年)。这年,顾炎武严词拒绝了大学士熊赐履荐他参与编修《明史》的聘请,漫游至山西。“南有亭林(顾炎武)、北有青主(傅山)”,遗民的两大领军人物在太原东南七八里处的松庄,傅山的居所,第三次相逢。
两人都有反清复明之志,但每次见面带来的却都是令人悲愤的消息。此次谈及时事二人更加沮丧。尤其是两年前,十五岁的小皇帝康熙居然不动声色一举灭了鳌拜一党,如此手段令他们不寒而栗,觉得光复之事越来越接近泡影。赴晋途中,顾炎武还得来一个噩耗,他们的同仁大智和尚,也就是从前的“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这年事发被捕,押解途中经过江西万安时,在当年文天祥“惶恐滩头说惶恐”的惶恐滩暴卒。
他们又大醉了一场。
这次会面,二人都觉得光复大业已经不可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只得留待后人了。经过反复斟酌,二人决定创办些产业,为来日大举义旗积些钱财。据说山西的票号便是他们开创的,如梁启超《清代学术史》云:“山西票号相传为傅青主、顾亭林所创办。”章太炎《顾亭林先生轶事》也云:“有清一代票号制度皆顾、傅所创也。”
能策划票号生意,想来傅山等人的经济实力应该是非同一般的。然而事实是,傅山的生活甚为清苦。康熙二年,“畿南三才子”之一的申涵光拜访傅山之后,对表亲王显祚说高士傅青主的日子过得很是贫困,全家住在崖坡下的两孔窑洞里,希望他能帮一把,王显祚于是为傅山买了一所宅院,由此可见傅山的困境。创办票号之说,应该只是纸上谈兵,当时不过立了方案规矩,日后才为有财力者沿袭套用,真正大做起来。
但综观当时整个遗民群体,傅山的生活应该还算过得去的,毕竟他精于医术,更妙于书画,两者都堪称国手,为天下第一流的身份,名声显赫,混口饭吃实在简单。其他遗民的生计更是窘迫,他们的境况三百多年之后读来还是令人酸楚。随便从《清史稿》的《遗逸传》中摘几则吧:
“刘永锡寻移居阳城湖滨,与妻及子临、女贞织席以食……食不继,时不举火,有遗之粟者,非其人不受,益困惫。其女已许字,未嫁,乱后恐遭辱,绝粒死。其妻哭之成疾,亦死。其僮仆遇水灾乏食,相继饿死,或散走……卒穷饿至不能起。一夕,大呼‘烈皇帝’者三,遂卒。”
“(徐枋)遁迹山中,布衣草履,终身不入城市……家贫绝粮,耐饥寒,不受人一丝一粟。”
“(李天植)家益困,鬻其园,寄身僧舍,戚友赎而归之,始复与妻居,时年七十矣……老夫妇白头相对,时绝食,则叹曰:‘吾生本赘耳,待尽而已,’有馈食者,非其人,终不受……又十年,蜃园仅存二楹,两耳聋,又苦腹疾,终日仰卧。乍浦有郑婴垣者,孤介绝俗,与天植称金石交,先二年,冻死雪中,至是天植亦饥死。”
穷困是大部分遗民的共同特征。
根据《辞源》的解释,广义的遗民指全部亡国之民,这个范围太大,不分青红皂白一锅煮;一般人心目中的遗民,指的只是改朝换代后不仕新朝的人。
不仕新朝,这其实暗中包涵了遗民的另一个标准:你得先有出仕的资格。在科举时代,出仕的前提就是你必须是读书人;否则,以一个农夫的身份,不管谁坐龙廷,耕的都是那一亩三分地,无所谓新朝旧朝。刘永锡,崇祯乙亥举人,官长洲教谕;徐枋,崇祯壬午举人;李天植,崇祯癸酉举人;傅山尽管无意仕宦,但也出身书香世家,十五岁中秀才,二十岁试高等廪饩,后就读于三立书院,是山西提学袁继咸极青睐的弟子,亦是斯文一脉。
太平时期,埋头八股的读书人往往给人以迂腐颟顸的印象,但天地巨变之时,从前书本上一行行原本不甚痛痒的圣人教诲横竖撇捺间忽然汩汩流出了鲜血,剧痛的文人猛醒过来,几千年积累的民族气节一瞬间在他们体内被激活。面对异族雪亮的刀枪,他们冷冷一笑,从书桌前缓缓站起,骨节作响声中,慢慢直起身,双手分开不知所措的大众,一步步走上前去。
尘埃落定。当一切的反抗都归结于不可挽救的失败后,他们面前只留下了两条路:承认既成事实,低头弯腰,以后半生的灵魂折磨为代价换得眼前的安顿,甚至富贵;或者退出身来,自我放逐于山野。
新朝的大门向他们大开着,胜利者微笑着伸出刚洗净血污的手:这下你等总该看清形势了,来吧,我们可以给你更优厚的报酬!你们不是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吗?天命在我们这边!你看看,你们那些投得早的同胞,现在吃香喝辣,娇妻美妾,好不快活,你等又何必自苦呢?
又是冷冷一笑,拍拍尘土整整衣冠,束紧腰带,一拂大袖扭身就走,不回头,任夕阳里飘着一道瘦长的倨傲身影。从此,我便是这变了色的天地间的一介遗民。
绝了仕进之路,对很多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读书人来说等于是断了唯一的出头之路,甚至是活路,实在是连个田间挣命的农夫都不如。
所以选择做遗民往往就是选择饥困潦倒。
然而穷饿却是遗民最崇高的荣誉,他们的尊严原本就要在饥寒交迫时凸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