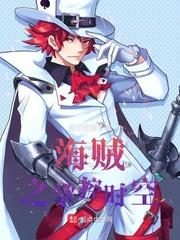奇书网>本草春秋是什么 > 壮气蒿莱(第1页)
壮气蒿莱(第1页)
壮气蒿莱
——从“牵机药”到“五国城”
宋奸相蔡京之子蔡绦有本笔记《铁围山丛谈》,记了北宋一朝不少秘闻轶事。毕竟他老子身居高位多年,频频出入宫禁,历代学者多重视其言,不以等闲视之。其中提到宋徽宗刚即位时曾巡视皇宫,发现有个无名库房,一问方知此库专藏毒药,库内的毒药分为七等,鸩排在第三等,第一等的毒药“鼻嗅之立死”。
即使没有蔡绦的描述,所有人其实都清楚,自从有了皇宫那天起,这个神秘的库房便已经存在。随便翻史书,不必费多大力气,总能找到一些“鸩杀”“饮药死”“毒杀”之类的字眼。这些字透着一股森然的寒气,凝视久了,似乎眼前还能幻化出一个密封的小瓷瓶,以及瓷瓶后令人毛骨悚然的微笑。
下毒杀人毕竟不是光明磊落的事,皇家自然对此讳莫如深,所以那瞬间勾魂的瓷瓶中到底装着什么东西,自古便是一笔糊涂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应该算是宋宫毒库中排名第三的鸩毒,以至于经常用“鸩”来统称所有的毒药。而这“鸩”为何物,从来便讲不明白,或者说令人难以置信。古书中说那是一种不祥的邪鸟,食蛇为生,全身剧毒,沾了它的屎尿连石头都会腐烂如泥,它的巢下数十步之内更是寸草不生,只要把它的羽毛在酒中划过,这酒就可致命。但亲眼见过的人极少,连博学严谨如李时珍都无法对它下定论:《本草纲目》中有关鸩鸟形状的记载互相龃龉,甚至还有些无稽之谈,说鸩鸟发觉木石下有蛇隐藏时,会如人间巫师那般“禹步”作法,“须臾木倒石崩而蛇出也”。
尽管荒诞,但历代还是有人认为世界上确实有过这种简直是来自地狱的生灵,只是人类觉得这种毒鸟太过可怕,所以才捕杀灭绝了它。
可天下终究是有毒药的,一桩桩见得人见不得人的阴谋阳谋都验证了它们的效果。那么所谓的“鸩毒”究竟是什么呢?据专家考证,很多毒药其实不外乎是砒霜、乌头之类,传说中的“鹤顶红”大概便是红信石:含有少量杂质的砒霜矿石;而著名的“牵机药”被认定为马钱子更是极少疑义。
马钱子又名番木鳖,是马钱科乔木马钱的种子,原产印度、越南、缅甸、泰国一带,有通络散结、消肿定痛的作用,可用于痈疽、跌打损伤、风湿痹痛等症,现代还尝试着用来治疗癌症。但有大毒,内服需经严格炮制,而且一般每日不能超过0。3克到0。9克,否则所含士的宁碱中毒,引起全身伸肌与缩肌同时极度收缩,从而剧烈抽搐,出现强直性惊厥,不立即抢救很快就会身体严重佝偻,窒息而死。
这完全符合古籍中关于牵机药的记载:“服之前却数十回,头足相就,如牵机状也。”——牵机之意,现代人不好理解,反正是布机织布时的一种状态。
牵机药在史上如此出名,是因为都说它夺走了一位天才词人的命。
写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南唐后主李煜。
李煜的结局,《宋史》等正史都未明言是被毒死,但《续资治通鉴》的考异说:“李后主之卒,它书多言赐鸩非善终。”说得最详细的则是宋人王铚的《默记》,死于牵机药之说便是来自此书。
按说正史未载李煜被害,后人便该对牵机药之说打个大大的问号,但事实是大多数人宁愿相信一家之言的《默记》,为后主洒一掬同情之泪,也不愿相信《宋史》中平平淡淡的“三年七月,卒,年四十二。废朝三日,赠太师,追封吴王”。
因为很多人认为,《宋史》的不少章节值得怀疑,尤其是太祖太宗年间的事情,更不能全信——
毒杀李煜的疑犯太宗赵光义,早已将那段历史用金漆仔仔细细地刷了一遍。
其实隐饰李煜之死不过是顺手之举,赵光义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证明其继承于兄长的皇位的合法性,而最重要的,就是力脱自己在太祖暴卒中的干系。
太宗对史官修史的干涉力度很大,太宗朝所修的《太祖实录》先后返工三次,虽然已经做了大量的篡改和掩饰,他还是不满意。
但太宗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太祖之死虽然留下了不少抹不去的痕迹,如“烛影斧声”,但毕竟已如太宗所愿,被历史封存,成了千古之谜。唯一的谜底,早已被深深埋入皇陵,无论太宗的双手有没有沾上兄长的血,千年后都已经彻底腐烂,化作了劫灰。
无论真相如何,结果只有一个:宋太祖赵匡胤,死于开宝九年(976年)十月二十日,时年五十岁。
要到两年后,忙碌的死神才降临李煜的小楼。
太祖的早逝,于李煜悲惨的命运等于雪上加霜。只要太祖在世一日,他便不会与任何毒药牵上关系,因为以太祖的胸襟足以容下这么一个亡国的落魄之君。
苏轼的好友王巩写了本《随手杂录》,记了这么一件事。陈桥兵变后赵匡胤回师进宫,见宫嫔抱着周世宗柴荣的幼子,当时赵普等人都在,赵匡胤便问他们该怎么处理,赵普回答:“当然得除去,以免后患。”赵匡胤却说:“即人之位,再杀人之子,我不忍心。”就把这婴儿送给部下抚养,以后再也没问起过。
虽然此事正史未载,但太祖著名的三条誓约也足以印证他的度量:刻在碑上藏之深宫、世代传承的祖宗家法,第一条赫然就是“保全柴氏子孙”。须知太祖的帝位篡自柴家孤儿寡母,而李煜却是堂皇的猎物,于皇朝正统上的敏感意义远不能及。赵匡胤能容柴氏后人,岂能容不下一个整日凄凄惨惨的文人李煜?
反过来说,如果赵匡胤容不下李煜这等亡国之君,那么他为何要在大举南伐时如此郑重吩咐将领曹彬、潘美呢:“城陷之日,不得随便杀戮。即使不得已必须攻打,李煜一门也不可加害!”
而世人都说赵光义杀李煜,不过是缘于他的名作《虞美人》中“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等句触怒了龙颜;或者还得加上这位好色天子对李煜美艳的小周后的垂涎——野史记得绘声绘色,说赵光义常召小周后入宫,而每次回来小周后都会对李煜又哭又骂。
不管什么原因,毒杀一个手无缚鸡之力、已经对自己构不成丝毫威胁的彻底失败者,都不是好汉的行径:如果李煜真的有罪,真该处死,为何不能明正典刑昭告天下?
只可惜,在史书上处处透露出做贼心虚的赵光义,原本就不是条好汉。
太宗一母同胞的兄长赵匡胤才是一条好汉。
这位天子的身上,有着一种历代帝王难得的草莽英雄气,而这种性格又迥异于同样来自民间的刘邦——刘邦身上多的是市井流氓气,赵匡胤则更像是一个传奇小说中的侠客。
史载赵光义自小“性嗜学”,像个斯文人,但他哥却是另一脾气,幼时没正经读过书,好舞枪弄棒,而且武功很高,几乎每个跑码头的都会耍的那套“太祖长拳”,据说便是创自他手。《宋史》中也记载了他的好身手,说他“学骑射,辄出人上”,随便学学就远远超过一般人。有次他试骑一匹没有笼头的烈马,那马发了劣性子狂奔,经过城门时,逸上斜道,赵匡胤的额头重重撞在门框梁上被甩下马来;旁人都以为这次老赵可完蛋了,天灵盖定然被撞个稀巴烂,可赵匡胤爬起来,立即发力奔跑,追及烈马腾身再上,竟然毫发无伤。看来,老赵起码练过金钟罩铁布衫和八步赶蝉之类的轻功。
赵匡胤从军前曾经浪迹江湖,那几年生涯在民间留下了很多传说,什么千里送京娘、华山摆棋摊云云,野史提及太祖身上的江湖气也是津津有味。比如说他称帝之初,不少昔日同僚有些骄横难制,于是一日赵匡胤将他们召来,每人授予佩剑强弓,他自己则不带卫士,与他们一起上马驰出皇宫来到一处深林饮酒。几杯下肚,赵匡胤冷不丁发话:“此处僻静,你们之中谁想当皇帝,可以杀了我,然后去登基。”众人都被他的气概镇住了,全部拜伏在地,战栗不止。还有一次,御驾出巡,突然飞来一支冷箭,射中龙旗;禁卫军大惊失色,赵匡胤却若无其事地说:“多谢他教我箭法。”——不准搜捕刺客。
野史也许夸张了些,然而正史的很多记载同样鲜活地凸现了这位赵官家的草莽豪情。《宋史》“质任自然,不事矫饰”只是笼统的虚写,生动的事例比比皆是。如说他好交朋友,动辄结拜,仗义疏财,酒肉大家吃,有所谓“义社十兄弟”;登基后在皇宫中待不住,老喜欢微服出行;爱吃赵普老婆做的烤肉,一直称呼她为“嫂嫂”,做了皇帝也不改口,每年都要来赵普家吃喝几次,有回居然在大雪之夜摇摇摆摆带着赵光义上门,倒把来开门的赵普吓了一跳;还有次宴会,赵匡胤倒了一杯酒给李煜的难友——南汉后主刘鋹,把刘鋹唬得魂飞魄散,当年他自己好用毒药毒臣下,这回看到皇上赐酒,以为大限到了,捧着杯子涕泪直流恳请开恩,赵匡胤见状呵呵一笑,拿过刘鋹的酒一饮而尽,另外给他倒了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