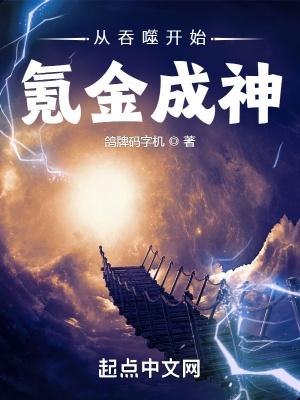奇书网>古代中国文明类型 > 第三节 宋词(第2页)
第三节 宋词(第2页)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悼亡词意境凄美,情感浓烈而真切。苏轼对亡妻的思念,字字泣血,读来**气回肠,心中哀伤与艳羡交替。这是一位多情的文人,一个不忘至亲爱人的血性男儿。苏轼的词,在抒发个人意气的同时,带领我们走过他蜿蜒曲折的人生轨迹,跟随着他的悲喜哀愁领略时代潮流的汹涌变迁。
作为北宋文坛的领军人物之一,苏轼在散文、诗歌、词章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的艺术风格为后人争相效仿,而其作品中所流露出来的宠辱不惊、淡泊从容的人生态度,俯仰寰宇、包容天地的广阔胸襟,更是为后来的文人树立了典范,在历代影响深远。其后,11世纪中叶的北宋词坛,出现了两大创作群体,群星璀璨,光耀千古。其一便是以苏轼为核心,由黄庭坚、秦观、晁补之、李之仪、赵令畤、陈师道、毛滂等人组成的苏门词人以及晏几道、贺铸等相关词人群。其二则是以周邦彦为主帅,曾供职于大晟乐府的曹组、万俟咏、田为、徐伸、江汉等人构成的大晟词人群。前者注重抒情言志,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囿于音律规范,可读性强;后者则重视词的协律可歌,抒情节制,力避豪迈,追求词艺。两大群体开创了词章发展的两条道路,奠定了南宋词章发展的方向。
苏门词人群中,黄庭坚的词作追求雅俗并重,致力于自我刚直倔强个性和乐观人生态度的表达,内容更贴近日常生活;秦观追随苏轼脚步,一生亦饱受宦海波谲云诡之苦,空有报国之志而难以施展,脆弱的心性下精神饱受打击,早早离世。然而,他的词作在宋朝词坛上仍旧独树一帜。敏感纤细的性格,使得他虽为男子,却真正写出了男女情爱至纯无暇的境界,予人至高的情感享受。“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秦观《鹊桥仙》)在他笔下,爱情变得无限美好,令人向往。而其“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鹊桥仙》)的慨叹,升华了爱情的高度,引导人们见识更加豁达、从容,意蕴悠长的爱情。
柳永、苏轼等人的努力,使慢词大行其道。然而,同时代的晏几道却反其道而行之,仍旧遵循父亲晏殊的“花间”传统,以小令书写**气回肠的男女情爱,对象明确,情感真挚。“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晏几道《临江仙》)在他的词作中,爱情成为一种纯精神性的追求,更成为一张特色鲜明的名片。
大晟词人群的代表人物周邦彦,一生支持变法新党,故而也在新旧党争的交替中浮浮沉沉。他的词作长于铺叙,顺叙、倒叙、插叙错综结合,时空结构回环往复,交错叠印。他在怀古咏史中抒发人生起落无常的感慨,宣泄漂泊人生的倦怠与无奈,情景交融,交错往复,跳脱无踪迹。且善于用典,能将前任诗句融入词中而浑然天成,有如己出。如《西河·金陵怀古》中“夜深月过女墙来,伤心东望淮水。酒旗戏鼓甚处市。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入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皆由化用唐朝刘禹锡《石头城》、《乌衣巷》等诗歌而来,似曾相识,却又自成一体,意蕴更丰。此外,他所创作的词调不仅数量众多,且用字高雅,较之柳永等人更符合南宋文人的趣味,因而在南宋受到广泛尊崇与效法。
两宋之际,在靖康之变的冲击下,李清照、朱敦儒、张元干、叶梦得、李纲以及陈与义等一批“南渡词人”登上词坛。由于时代剧变,他们的创作也往往被鲜明地割裂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生活安逸,所作多为闺中情爱,且好吟风弄月,创作光芒往往为周邦彦、贺铸等人所掩盖。靖康之变后,山河破碎,国家危亡,民族耻辱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之心与社会自觉,开始追随苏轼等人的词风,发出救亡图存的呐喊。具体到现实,他们的目光从闺房、书斋中走出,走进芸芸众生,有意识地关注普通民众在战火纷飞中的苦难,心中的家国责任感进一步唤醒。然而,对天下兴亡抱有强烈抱负心的他们,在现实面前却往往深受挫折,进而为其词作增添了难以消除的沉郁苦闷之气。在北宋词的基础上,南渡词进一步扩展了词体抒情言志的功能,强化了其时代感与现实感。
这一时期,女词人李清照以其清雅婉约之姿,在宋朝词坛上书写了难以磨灭的佳话。她的一生深受时代洪流的影响,早期的幸福甜蜜随着金军南下而烟消云散,后期的颠沛流离亦拜金人所赐。故而她的词作中,既有“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一剪梅》)的美好爱情与离愁别绪;又有南逃丧夫后“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李清照《声声慢》)的孤独凄凉、悲痛哀婉。女子情态下,还藏着一颗坚毅勇敢的心,以至在品评古人时发出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夏日绝句》)的豪迈心声。李清照的词用字虽简却精妙清亮,风韵天然,语言清新素雅,巧夺天工。这使她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创造力最强、艺术成就最高的女性作家之一。
与李清照同时经历了南渡之苦的朱敦儒,继承并发展了苏轼自我抒情的词风,有鲜明的自传性特点。他的青少年时代,“生长西都逢化日,行歌不记流年。花间相过酒家眠,乘风游二室,弄雪过三川”(朱敦儒《临江仙》)。放浪形骸的生活下,是一颗追求独立自由的心。朝廷征召时,他断然拒绝,并写下了“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朱敦儒《鹧鸪天·西都作》)的词章以明志。
靖康之变,洛阳城破。朱敦儒仓皇逃亡东南,辗转岭南避难。南奔途中,灾难不断,他的词风亦由飘逸洒脱变得凄苦忧愤。“放雁向南飞,风雨群初失。饥渴辛勤两翅垂,独下寒汀立。”(朱敦儒《卜算子》)被战火所迫,远离家乡之人,好似风雨中迷失的南飞之雁,前途未卜,生死难依。国破家亡,“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朱敦儒《相见欢》)。其间的忧愤与伤感,溢于言表。
面对国家与民族的灾难,南渡词人们逐渐放弃曾经或闲适或放浪的生活,开始积极关心国家命运,甚至投身仕途,投笔从戎,以期报效国家。在他们的词作中,不仅有对战火肆虐的真实描写,有对普通民众苦难的切实陈述,也有誓死抗击金人的一腔热血,以及对统治者不作为、一心苟和的愤慨。如曾协助李纲指挥汴梁保卫战的张元干,目睹了汴梁城下哀鸿遍野的惨烈景象,体会过山河破碎的悲伤后,愤而写下“长庚光怒,群盗纵横,逆胡猖獗”(张元干《石州慢·己酉秋吴兴舟中作》)的词句,更发出了“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张元干《石州慢·己酉秋吴兴舟中作》)的呼声。然而,面对最高统治者不顾大局、一心南逃的现实,词人满腔无奈,只道“两宫何处,塞垣只隔长江,唾壶空击悲歌缺。万里想龙沙,泣孤臣吴越”(张元干《石州慢·己酉秋吴兴舟中作》)。又如早年“睡起流莺语”(叶梦得《贺新郎》)的叶梦得,在熊熊战火中,亦唱起了“坐看骄兵南渡,沸浪骇奔鲸。转盼东流水,一顾功成”(叶梦得《八声甘州·寿阳楼八公山作》)。他们焦急于国家的灾难,渴望大展身手,保家卫国。其中的豪情壮志,令人胸中激越。而站在国家剧变第一线,率领大军以血肉之躯抵抗金兵南侵的李纲、岳飞等人,也将其奋不顾身、誓死保卫疆土、收复河山的精神彰显于词作中,成为这个时代抗金救国的最强呼声。
靖康之变中主持东京保卫战的李纲,在其《苏武令》中表达了坚定的救国救民信念:“调鼎为霖,登坛作将,燕然即须平扫。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强烈的节奏感,恰似词人勃勃跳动的心脏,是扫平寇贼,迎回徽、钦二帝的一颗赤子之心。纵使被罢职,李纲仍旧以慷慨激昂之势盛赞历史上征战沙场的圣君勇将,期待“六军万姓呼舞,箭发狄酋难保。虏情詟,誓书来,从此年年修好”(李纲《喜迁莺·真宗幸澶渊》)的实现。
当李纲等人请命呐喊时,血战沙场的岳飞则在戎马倥偬中留下了响彻天际的雄壮呼声。“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车长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身为军人,保卫山河本是天职所在。然靖康一役,敌寇入侵,汴梁梦碎,君王被掳,生灵涂炭。这一切,于军人而言,是莫大的耻辱。激**于胸中的愤怒,“还我河山”的迫切愿望,酝酿出了词人胸中直上九霄的朗朗气魄,令人气血翻涌。
历经绍兴和议,宋金对峙局面逐渐形成。安定下来的局面,为词的创作重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12世纪下半叶,南宋词坛上再次出现大家辈出、名作纷呈的局面。以辛弃疾、陆游、张孝祥、陈亮、刘过和姜夔等为代表的“中兴”词人将词的创作推向高峰。
“中兴”词人,首推辛弃疾。作为战后出生于金人统治区的汉人,辛弃疾对金人的残暴统治,对收复故土的强烈渴望与李纲、岳飞等人一脉相承。他一生希求征战沙场,驱逐金人,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辛弃疾《破阵子》)。然而,这种昂扬向上的进取精神却与偏安东南的南宋朝廷背道而驰。历史的错位注定了辛弃疾的悲剧命运,加之南宋对南归的“归正人”的猜忌与歧视,使得他壮志难酬,只得在地方小吏上辗转迁徙,抑郁而终。
现实的不如意,促使辛弃疾将胸中剑化为手中笔,用词来表现自我的精神世界。与虎啸生风、豪气纵横的英雄气概相得益彰,辛弃疾的词“有心雄泰华,无意巧玲珑”(辛弃疾《临江仙》),情怀胸中激烈,意象雄奇飞动,境界雄伟壮阔,语言雄健刚劲,使得辛弃疾词成为宋词史上的一座丰碑。
宋朝词坛中,苏轼和辛弃疾都曾凭吊过赤壁。然而,苏轼在感叹赤壁的雄壮开阔,赞美赤壁之战中周瑜的运筹帷幄之后,仍不免发出“人生如梦”(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感慨,流露出典型的文人心态,不免有英雄气短之感。然而,辛弃疾凭吊赤壁,却是“半夜一声长啸,悲天地,为予窄”(辛弃疾《霜天晓角·赤壁》)。面对赤壁的“惊涛拍岸”,辛弃疾表现出了直上云霄的昂扬斗志,是天地唯我一人的雄阔意境。这种英雄本色,贯穿于他的词作中。纵使英雄失意,落魄江湖,仍不忘壮志报国。平生所愿,唯有“气吞万里如虎”(辛弃疾《永遇乐·京口碑古亭怀古》),“横空直把,曹吞刘攫”(辛弃疾《贺新郎·韩仲止判院山中见访席上用前韵》)。
从少年时代的横戈马上,到中年的壮志难酬,再到暮年的隐居田园,错误的时代令英雄的人生每况愈下。尽管辛弃疾在大多数时候都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甚至留下了“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的优美乡村画卷。然而,一系列不如意终究将他身上的英雄气概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辛弃疾《鹧鸪天·鹅湖归病起作》)的落寞与悲哀。这是一个被时代亏欠,被怯懦、自私的庸人集体拖垮的人。身处时代洪流中,我们总在不知不觉间便充当了恶的帮凶,抑或被滚滚潮水淹没,成为无可名状的悲情传说。辛弃疾的词,值得我们反复品味,铭刻心头。
与辛弃疾同时的姜夔,终身布衣,游历过淮楚、荆湘、合肥、湖州和杭州等地,以其清高耿介的个性安贫自守,为传统婉约词输入了清冷雅俊的气质。他所描写的爱情,较之于北宋有了不同的色彩。“别后书辞,别时针线。离魂暗逐郎行远。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姜夔《踏莎行·自沔东来丁未元日至金陵江上感梦而作》)他不仅着重表现离别后的相思之苦,还以冷色调将情爱高雅化,使其拥有了超尘脱俗的韵味。
与此同时,他的咏史怀古词亦别有一番沉静悠远之风。他在白描之外,加入侧面描写,勾勒广袤渺远的意境,令人生出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如其《声声慢》:“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这一番描写,犹如以字为画。一步一景,清晰可见、可闻、可感。又“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以古人喻于己,更深一步地传达出对山河破碎的忧伤。后一句“二十四桥明月夜,波心**,冷月无声”,以一桥、一月、一清流,勾勒出一幅静中有动的画面,清俊空灵,韵味无穷。
姜夔之后,南宋词坛仍旧涌现出不少优秀的词人。但其创作思路与艺术风格,大抵已不超出自北宋以来开辟的道路。待到南宋灭亡,词坛亦是一片哀声。唯有坚持抗元的文天祥,以视死如归的气魄唱出了13世纪最后的高歌:“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人生翕炊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文天祥《沁园春·题潮阳张许二公庙》)这是两宋词坛最后的辉煌。此后,随着一个大时代的终结,词终究走向没落,再难崛起东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