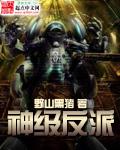奇书网>世事苍茫如云烟 > 保持对学术工作的热情答文艺报约陈定家问(第1页)
保持对学术工作的热情答文艺报约陈定家问(第1页)
保持对学术工作的热情——答《文艺报》约陈定家问
陈定家:赵老师,您好!很高兴有机会采访您。当我接受采访任务时,心里突然蹦出了“标杆”两个字。听说北大中文系的老师把您作为优秀研究生的标杆,见到出类拔萃的女生,就夸她或将成为“另一个赵园”!我本人也多次见证过以您为标杆的情景。十几年前,我向所里一位先生请教问题,那位先生总是有意无意地以“赵园说”做评判标准。此后,我在好几位同事那里遇到过类似的情形。您看,这些令人敬佩的求学者和治学者,都以您为标杆,这算得上一种学者的成功吧?可是有人说您走上学术之路纯属偶然,治学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您能否先说说这方面的情况?
赵园:您过奖了。“标杆”不敢当。我也听到过您提到的那种说法,对那一种比方不可当真。我并不希望别人像我。事实上,我欣赏的年轻学人,包括女性,比如张丽华、袁一丹,各擅胜场,并不像我,倒是让我觉得后生可畏。
我的“走上学术之路”,无非利用了1978年研究生招考提供的机遇。当时我在郑州的一所中学教书,报考的动机,只是为了逃离那个单位。我研究生的同班同学,大多是中学教师,我猜想情况和我类似,未见得当时就有怎样的志向。偶然性还在于,北大中文系在统计各考场分数时,我所在的考场漏计了一项分数。倘若这点疏失未被发现,我应当早已作为中学教师退休,在“颐养天年”。我不能因此说自己有怎样的幸运。其实事后看来,得失很难计量。
走上“治学之路”后,应当说是比较顺畅的。压力不大,没有深厚的已有积累的压力,也没有来自国外汉学的压力。有些条件现在仍然有,即如没有来自国外汉学的压力。压力不大,“余地”却比较大。我是“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学术荒废已久,大家都刚刚起步或恢复研究工作,而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十七年间屡遭重创,发展不充分,因此无论新手还是老将,都像是在拓荒。而这批“新人”即使基础薄弱,却各自在“文革”中积累了社会生活经验;学识匮乏,却不缺少对人事的理解力与识别力。这后一方面是我所属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点“本钱”,尽管有限,却很重要。我最近还在一个场合,谈到毛泽东所说文科应当以社会为工厂,作为教育理念是有合理性的,虽然具体的路径未见得适当。
此外我们还得益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良好的学科环境。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后文革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崛起,以五四新文学运动作为重要资源,与那个解放运动密切呼应。对于我所属的这一代专业工作者,确实是难得的机遇。无论基于个人经历还是遭逢的时世,都使我们有足够的动力去“拼”。
近些年来学术生态已经大变。便捷的网络下载,不但改变着学术工作的方式,而且重新塑造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以致我读到某些炫耀博学的宏文,会条件反射地想,那些材料是怎么来的?网络时代的“博学”或正成为“虚胖”,那种文字少的是生命感,一个生动个人的生气的灌注。这种无生命的学术作品正到处泛滥,如古人说的那样,祸枣灾梨,令人慨叹。
陈定家:《艰难的选择》是您的第一本学术论著,您在这本书中试图通过分析现代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描绘出现代知识者的心理图景。有人将这本书说成是您治学生涯的里程碑,但您本人对这本书所应用的叙述方式好像并不满意,它是否有点受制于线性叙述逻辑的束缚,以致论述过程中的“丰富性”未能得到充分呈现?这本书对您此后的研究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
赵园:“知识分子考察”是读研中就已经选择的研究方向,与我们这代人的经历有关——那一代现代文学研究者,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相近的方向,以便经由学术,思考“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道路与命运”。我曾引用过鲁迅“连自己也烧在里面”的话,很能描述我们当时的状态。这种学术工作,也是在探寻自己的精神血缘。知识分子与革命,或革命中的知识分子,是二十世纪的一大主题,对我的吸引力至今仍在。学术文体不能容纳的更个人化的内容,我写在散文随笔中,即如那一组《乡土》(收入《独语》一集)。
对我的第一部学术作品的不满,不止在叙述方式,还在框架、具体论述以至表述。那些缺陷,多少也由于资源的匮乏。我着手写作那本书的时候,还没有大量的理论输入;我所凭借的,是原有的一点积累。但那种“连自己也烧在里面”的**,是那一时期特有的。那种写作状态与研究态度,是只能一次的经历,不可重复,值得怀念。
最初的选择贯穿了我的学术工作的始终,由中国现代史上的知识分子到其前身(以古代中国的“士”为近代知识分子的“前身”,要作种种限定,这里姑妄言之)。我常常对年轻学人说,最初的选择有可能持久地影响你学术研究的取向与格局,也就以我和我的朋友们为例。最初的选择确实有某种决定性。而我的学术工作始终在最初选择的方向上,无论“二十世纪”还是“明清之际”。
陈定家:您的《北京:城与人》与《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是继《艰难的选择》之后完成的两部重要著作。学界对这两本书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依我个人的浅见,后者似乎比前者更为厚重、更为深刻。但从媒介反应和读者接受的情况看,前者受欢迎的程度似乎远在后者之上。您能说说出现这种反差的原因何在吗?
赵园:两本书的写作,投入大有不同。写《北京:城与人》,缘起只是几篇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京味小说”。在我的学术作品中,那本书写得最轻松,甚至没有做必要的文献准备。但对于学术价值,不适用“投入产出”的计量方式。这本书的“受欢迎”,多少由于机缘——出版时恰逢“北京文化热”。后来“北京”、“城市”热度不减,那本书就有了“常销”的可能。而对于农村的关注度却在下降。这种情况仅从新闻报道就可以感到。农时、农事、灾情等等,曾经是我所属的一代人日常关心的方面。我至今还保有对气候影响于农事的敏感,与“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世代不同。
写《城与人》有偶然性,写《地之子》,则像是还愿。我尽管不是农家子弟,由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历,对乡村似乎有“天然的”亲近感。7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曾在河南农村插队两年,那段经历也令我难忘。回头读两本书,长处都在作家作品的分析,而“大判断”往往经不起推敲,也证明了我的强项在此而不在彼。
《城与人》之后,我至今仍然有对“城市”的兴趣,旅行中往往持“考察”态度,对近几十年的“城市改造”随时怀了忧虑。而乡村则是另一个关注的方面,尤其对于“空心化”带来的乡村文化生态的不可逆的变化,对于农村老人的养老困局。
陈定家:在大多数人心目中,您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堪执牛耳的实力派学者。《艰难的选择》等著作为您开辟了坚实宽广的学术道路,按常理说,接下来应该是您推出相关研究成果的高峰期,风头正健,人生也步入了黄金岁月,但这个时候,您却出人意外地放弃了现代文学研究这块优势阵地,移师当时“没有本钱”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这无疑是一次学术冒险。这么多年过去了,可否说说,您对这次学术转型的心态与看法是否有所变化?
赵园:我的转向明清之际,转向史学与文学之间,是在提倡“跨学科”、“越界”之前,完全是一种个人选择,既不像有些人猜测的那样,因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国内形势,也与学术界的“潮流”无关——当时的我,由于缺乏外语能力,很封闭,对国外学术潮流几乎一无所知,也缺乏了解的渠道。至于被认为“暗合”了某种取向甚至理论,则更像是巧合。我的动机,无非是在已有的研究陷入停滞后,寻求挑战,试探自己的可能性,希望再次激发学术热情。那确如你所说,是一次“学术冒险”。我是像沟口雄三先生所说的那样,“空着双手”进入明清之际的那段历史的。这么说也不十分准确,因为我的手中有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积累。这对我很重要。这一点,要在这以后的学术工作中,才被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
这次转折对于我至关重要。我至今仍然认为自己当年的选择很明智——这不止是由“成就”的角度,更是由自我丰富、提升的方面衡量。进入新领域后,我有了机会接触学术经典,接触学术大师的作品,经历了重新学习做学术的过程;也有了机会在更大的范围内作学术交流。尤为难忘的,是与台湾同行的交流。这种机会,是我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不能得到的。
陈定家:有人说您是历史学家中文学叙事派,是文学研究队伍里历史学家。您能否结合自己的研究,谈谈您理解的史学与文学的关系?
赵园:学科壁垒是人为设置的,一个大活人何苦要画地为牢?记得一些年前,在一个场合回答提问,我说非驴非马,是个骡子有什么不好?这句话似乎也是别人说过的,我不过拿来自我辩解或解嘲罢了。时下鼓励“越界”,我的选择的正当性已无需解释,却仍然有必要鼓励年轻学人作这类尝试。
古代中国的学术,文史本不太分。亦文亦史,前辈学者就承接了这种传统。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是文学还是史学?倘若用了现在通行的尺度,能不能通过学术刊物的审稿程序?可不可以用来评职称?
我自己不大考虑专业归属,想的是如何调动自己全部储备(包括能力),力求使“题无剩义”,而非符合某个学科既经形成的评价尺度。“历史学家中文学叙事派”或“文学研究队伍里历史学家”不是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与专业背景有关。事实上在做“明清之际”的二十多年间,我主要是在向优秀的史学著作学习,获益极多。但文学研究的专业背景对我的意义绝不是负面的。对这一点,越到后来体会越深,也越有自信。
陈定家:我注意到,您写过一些学术自述,也接受过各种访谈,您在那里谈到了自己从事学术工作的甘苦。但我仍然希望知道,您如何看自己的学术工作的得失,包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与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
赵园:回头看,我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考察中,较为经得住时间的,是作家作品研究。这一点,刚才已经提到了。即如论萧红的,论骆宾基的,论凌叔华的几篇。所以经得住时间,是因为写作家论必须面对作品,而有可能不过分依赖流行的理论框架。那一时期也确实有活跃的审美感受力——我发现这是最容易失去的一种能力,与年龄与经历都相关。一旦失去,就难以再次获得。读自己的旧作,我常常会暗自惊讶,同时庆幸:幸而写在了当时;过了那个时候,就难以写出,硬写,也决不会精彩。
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的几部著作中,第一部少一点遗憾。《艰难的选择》与《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分别是两段学术经历中的初作。那当然是很不同的两本书,但在“投入”、“切身”、“痛痒相关”上相近。写《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较之写《艰难的选择》,更有初次踏入陌生领域、与对象不期而遇的兴奋,偶尔会“文思泉涌”,因知之不多,反而较少顾忌,有可能写得酣畅淋漓,使内心深处的**得以释放。那种状态是不大可能长久维持的。尽管《续编》诸篇更规范,论述更周延,却少了那一种元气,虽则“气盛”了难免于泥沙俱下。这既与状态又与年龄有关——状态往往也系于年龄。
但我以为《续编》另有价值。以“戾气”为题的确赖有直觉,写《君主》、《井田、封建》更出于设计,基于已经形成的对这类题目的重要性的认知。至于最终结果如何,与是“直觉”还是“设计”无关。“正编”或许更可读,但我对《续编》不无自信,相信其中的论题对相关研究有贡献。学术作品不妨力求可读,但可读性毕竟不是评价学术的标准。有人以表述“西化”、不“深入浅出”贬抑一个年轻学人的作品,我觉得很奇怪。我们的使用的概念系统本来就赖有输入,不过“西化”的程度不同、来源不同罢了。而缺乏难度,缺乏深度,缺乏重量感的东西已经够多,何不挑战一下自己的理解力,试着读一点确有分量的论著?
我的文字的好读难读,与论题更与写作状态有关。写《易堂寻踪》也像写《北京:城与人》,有偶然性,属于计划外项目,也因此写得轻松。用散文的方式组织学术,也让我更有可能体验写作中的快感。那本小书所写的一组人物,在他们的时代并非都声名显赫,却多少令人想到了鲁迅的论刘半农,清浅得可喜。这本小书的写作中时有感动,有沉醉。那在我,是一段美好的写作经历。尝试着变换写作方式,以不同的方式处理不同的材料,即使在同一部书中也力求如此。在我看来,这也是自我训练的一部分。
材料运用中的“精审”,是一种难于抵达的境界,但写到《想象与叙述》,取材已能节制,剪裁也较为工致,文字则少了那种格格不吐的艰涩,以至有评论者认为这一本的文字在其他几种之上。但由学术作为一种经历来看,得失仍然难言。写到这时候,已趋于冷静,甚至波澜不兴,没有了最初进入“明清之际”时的兴奋。仅仅由此我也意识到,是与这一种研究告别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