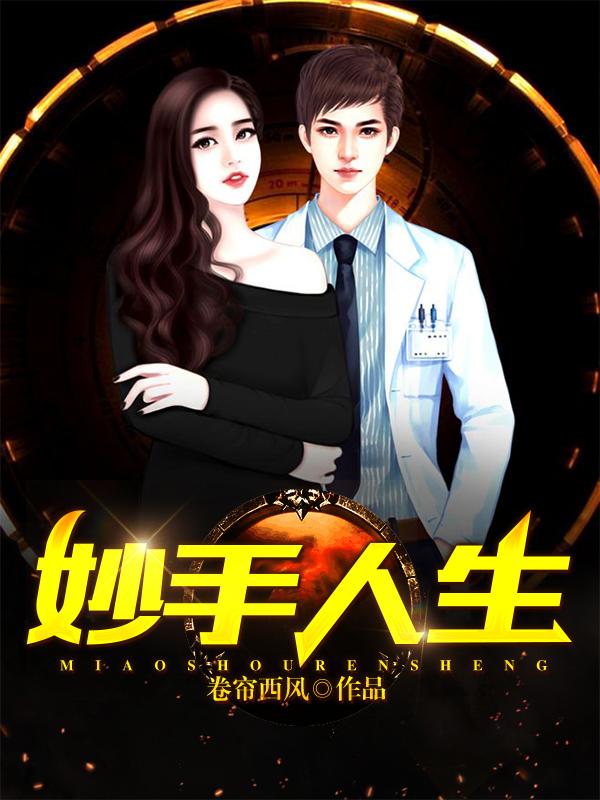奇书网>王阳明良知究竟是什么 > 三小结(第1页)
三小结(第1页)
三、小结
明代的政治文化在正德一朝变化相当大,其中“诛八虎”计划的失败是一转捩点,从此之后,宦官刘瑾等掌握国家大政,其中种种倒行逆施的作为,在在都使得国家的秩序濒临崩解状态。此时的士大夫们敢勇于挑战宦官权势的,不能说没有,但以当时内阁大学士等人的做法,又何尝不让中下阶层的官员们为之气馁。刘瑾倒台之后,官员们上疏直谏的文字中,振作“士气”成为普遍的共识,但由于政治权力依然掌握于宦官之手,“士气”依然萎靡,朝政仍不见起色,国家情势依然危急。此时的阳明在历经龙场的放逐生活后,怀着经世之志回到北京,原想于“后刘瑾的时代”中,一展经世济民的抱负,但其“政治受难者”的光环,却使其遭受无形的政治打压。一连串有关其父亲贿赂等情事的“曝光”,不但引起众人的指指点点,当然也影响到阳明的心情,在那表面上强调“政治清白”的政治情势下,真正“政治清白”的人,却遭到“不白之冤”,充分显示当时的道德价值的沦丧与倒置。
处在如此不堪的朝局之中,阳明怀着悲愤的心情,思考着当时的情势是如何造成的,为什么满口仁义道德的人,却做出言行不一的作为?为什么政治与学术地位高的人,没有办法把持其道德的信念,坚持善恶、是非、义利等传统的价值?为什么当有人起而对抗这种歪曲正义是非的行为时,却遭到无情的对待,无人再挺身而出来声援呢?士大夫的“气节”哪里去了?“君子”何在?往后国家社会的秩序又将如何维持呢?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情况是否即将到来呢?这一切问题的症结点又为何呢?现在又该如何才能挽救国家社会于危急之时呢?阳明秉持其“一心运时务”的思想理论,认为当务之急是恢复道德的秩序,也就是要让“君子道长,小人道消”。而起点就从每个人的“心”中做起,使每个人都成为“君子”,而这就是为何阳明要汲汲于提倡“心学”的原因。阳明首先重新思索学术发展的问题,认为当今学界错认学术的发展路径,忽略了孔门真正之传是在颜子一脉,而非强调博学广识的学术传统,所以阳明通过对“圣人之学”的重新衡定,并于《大学》一书中,寻求到其理论的根据。所谓“格物”,是去格心中之物,也就是将“心”中不正的部分去除掉,即能将“人心”变回“道心”。唯有如此,才能靠着这无私欲的“心”分辨善恶是非。其次,通过与朋友的交往,极力宣扬此学,希望他们可以了解到此学“变化气质”的功效,成为“君子”。
当阳明极力宣扬此新“圣人之学”,来自友朋的批评,不但直接,也点出阳明思想上的问题。这些批评有的从学术正统来论,有的从学术源流来论,再加上当时现实环境望治心切的需要,促使阳明去深化其此“圣人之学”的内涵。而其内涵中最重要的转变,就是将原本局限于个人修养工夫方面的探讨方向,提升至天下国家的层次上,提出“三代之学是心学”的宗旨。这意味着说现今如要重复“三代之治”,就必须从“心学”着手。在阳明提出此宗旨时,也是“朱陆异同”之辩争论非常激烈的时候,在此氛围之中,阳明高举“心学”的宗旨非常容易被化约为“陆学”与“禅学”的代表。不论阳明从北京到南京任官,这样的攻讦一直都有。阳明为了证明“陆学非禅学”说法以及强调“朱学亦有未定之说”,因而编撰《朱子晚年定论》一书。且为了不重演其座师程敏政《道一编》之作所引起“朱陆异同”的陈年争论,阳明单独取朱子之言,以证明其所采取的“主敬存养”的修养工夫,亦是朱子晚年所认同的。此论一出,虽不免引起更多人对此书内容编排等问题的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影响力也逐渐地在学术圈中发酵,导致坚持“朱学”思想不会错的信念开始动摇了。
要到阳明领兵南赣之时,正式刊刻古本《大学》及《朱子晚年定论》,其观点才逐渐为人所知,影响力也才发挥出来。就笔者阅读当时人的著作的初步印象,古本《大学》的内容及思想在当时并不如《朱子晚年定论》一样,得到太多的回响,除了湛甘泉与罗钦顺外。阳明的《大学》观或许还须等到《传习录》首卷刊刻流通后[108],才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
[1](明)孙绪:《马东田漫稿序》:“瑾诛后,婴祸者类擢不次,以旌直风。”见《沙溪集》(文渊阁四库全书·集1264)(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一,页493d。
[2](明)罗洪先:《明故中奉大夫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歉斋张公墓志铭》,见《罗洪先集》(阳明后学文献丛书)(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卷二十二,页877—878。
[3]如王鏊在刘瑾伏诛后,写信给韩文,信中说道:“事变仓卒,众皆愕眙,世之君子,各务自全,莫肯相援,甚者推咎于人以自解。某诚不佞,愤不自制,忘身直前,而力寡谋浅,不能少裨万分之一,心窃愧之。盖起事之初,志同许国,则祸患之至,义无独殊,而当事之人,莫究本末,荣辱顿殊,此某所以惓惓而不能舍,虽公之心未尝有望于仆,仆之心终不能无愧于公。”见《与韩尚书》,见《震泽集》(文渊阁四库全书·1256)(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三十六,页520b。
[4](明)郑岳:《故荣禄大夫太子太保刑部尚书见素林公行状》,见《山斋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1263)(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十四,页87a—87b。
[5]《明实录·武宗实录》,卷七十四,页1634—1635。
[6]顾佐的性格是刚正不阿,如《玉光剑气集》记云:“都御史顾佐历尹两京,刚正不挠,贵戚敛手。”见(明)张怡《玉光剑气集》,《臣谟》,卷二,页54。
[7](明)顾清《故刑部尚书致仕东湖屠公勋行状》:“丁卯,升刑部尚书,时逆瑾用事,乞奏请必先关白。公执不从,曰:‘如此,是二君也。’瑾用是衔,而公亦力求去。”见(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刑部一·尚书》,卷四十四,页1846c。
[8](明)谢丕《荣禄大夫刑部尚书谥庄僖韩公好(邦)问墓志铭》:“正德丙寅,升南京大理寺卿。戊辰,升刑部左侍郎。时逆阉刘瑾恶不通欵,升刑部尚书致仕。欲假他事中伤,而卒不能有所加。”见(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刑部一·尚书》,卷四十四,页1847d。
[9](明)焦竑《玉堂丛语》:“王华才识宏达,操持坚定。方贼瑾用事,士大夫争走其门,华独不往。华子守仁论瑾,瑾怒,逐守仁。顾素敬慕华,不辄迁怒,间以语人,欲讽使就见,华不往。及转南京,瑾又使人言华不久当召用,冀得往谢,华竟不往。其平生大节如此。”《方正》,卷五,页160。
[11]《明实录·武宗实录》:“(正德元年九月)南京十三道御史李熙等以灾异条陈十事:……五曰谨天戒以黜不职,吏部侍郎张元祯夤求入阁,礼部侍郎王华讳名首赂。”卷十七,页516—517。又记云:“癸巳,礼部左侍郎王华以御史李熙等劾其讳名首金,乞为究竟其事,洗涤冤愤,然后罢归田里。有旨,华事情已白,其勿辩,可尽心所职。”页521。
[12]如阳明在《乞恩表扬先德疏(1522)》云:“窃念臣父始得暗投之金,若使其时秘而不宣,人谁知者。而必以自首,其于心迹,可谓清矣。乞便道省母,于既行祭告之后,其于遣祀之诚,自无妨矣。当时论者不察其详,而辄以为言。臣父盖尝具本六乞退休,请究其事。当时朝廷特为暴白,屡赐温旨,慰论勉留,其事固已明白久矣!乃不意身没之后,而尚以此为罪也,臣切痛之。”见《王阳明全集》,《续编三》,卷二十八,页1018。
[13](明)杨一清:《海日先生墓志铭》,见《王阳明全集》,《世德纪》,卷三十八,页1389。
[14](明)王守仁:《寄诸用明(1511)》,见《王阳明全集》,《文录一》,卷四,页147—148。
[15]阳明晚年回忆道:“先生(杨一清)之在吏部,守仁常为之属,受知受教,盖不止于片言一接者。”见《书同门科举题名录后(1524)》,见《王阳明全集》,《续编三》,卷二十八,页1023。
[16](明)王守仁:《上父亲大人书》,见(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25,无页数,民国10年(1921)江都王氏鉴古书社影印本,傅斯年图书馆藏。此信为阳明佚文,考证详后《附录》。
[17](明)王守仁:《上大人书一(1511)》,见《王阳明全集》,《补录》,卷三十二,页1209。
[18]如(明)陈洪谟:《继世纪闻》记云:“刘瑾既诛……刘瑾流毒尚在,天下盗贼蜂起,而朝政乖宜,赏罚未当。山东、河南、江西、四川诸处,盗贼并起,而天下不胜烦扰矣。”(北京,中华书局,1997),卷三,页89—90。
[19]例如阳明自己在庐陵时有诗云:“万死投荒不拟回,生还且复荷栽培。逢时已负三年学,治剧兼非百里才。身可益民宁论屈,志存经国未全灰。正愁不是中流砥,千尺狂澜岂易摧!”见(明)王守仁:《游瑞华二首·其二》,见《王阳明全集》,《外集二》,卷二十,页720;又友人王云凤在《闻伯安自贬所召至京》诗中说道:“一别天涯经几载,多忧应是不胜癯。朝阳曾睹岐山凤,明月遥归合浦珠。报国心劳难措手,在堂亲老莫捐躯。年来学到今何得,可寄微言满纸无。”以周公及孟尝来期许阳明,见(明)王云凤:《博趣斋藁》(续修四库全书·集13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近体》,卷十一,页178b。
[20](明)董玘:《与王伯安》,见《中峰文选》,《杂著》,卷三,页14a,明刊本(傅斯年图书馆藏)。
[21](明)王守仁:《赠别黄宗贤》,见《王阳明全集》,《外集二》,卷二十,页724—725。
[22](明)王守仁:《赠翰林院编修湛公墓表(1512)》,见《王阳明全集》,《外集七》,卷二十五,页939。
[23](明)王守仁:《别张常甫序(1511)》,见《王阳明全集》,《文录四》,卷七,页230。
[24]县志记云:“邦奇之学,以程朱为宗,与王守仁友善,而语每不合。”见(清)钱维乔修、钱大昕纂:《鄞县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人物》,卷十五,页319c—320a。
[25](明)王守仁:《别湛甘泉序(1512)》,见《王阳明全集》,《文录四》,卷七,页230—231。
[26](明)王守仁:《别黄宗贤归天台序(1512)》,见《王阳明全集》,《文录四》,卷七,页233。
[27]关于此卷版本及内容的讨论,见陈荣捷:《传习录略史》,见《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学生书局,1983),页7—16,及钱明:《〈传习录〉补考》,见中国孔子基金会等编:《儒学与浙江文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页101—110。
[28]例如(明)吴与弼云:“世之志于学者,孳孳早暮,不可谓不勤也,其所求言语文字之工,功名利达之效而已。志虽盖勤,学虽益博,竟何补于身心哉?是则非圣贤志学之旨矣!圣贤教人必先格物致知以明其心,诚意正心以修其身,修身以及家而国而天下不难矣!故君子之心,必兢兢于日用常行之间,何者为天理而当存,何者为人欲而当去。”见《厉志斋记》,《康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1251)(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十,页555a—555b。
[29](明)程敏政:《道一编目录后记》,见《篁墩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1252)(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十六,页284a—284b。
[30]此序作于“正德己巳夏五月既望(1509)”,见(明)张吉:《陆学订疑序》,见《古城集》(文渊阁四库全书·1257)(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二,页606c。
[31](明)钱德洪等编《年谱·正德四年》:“始席元山书提督学政,问朱陆同异之辨。先生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页1229。
[32](明)钱德洪等编:《年谱·正德六年》,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页1233。
[33](明)王守仁:《答王虎谷(1511)》,见《王阳明全集》,《文录一》,卷四,页148—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