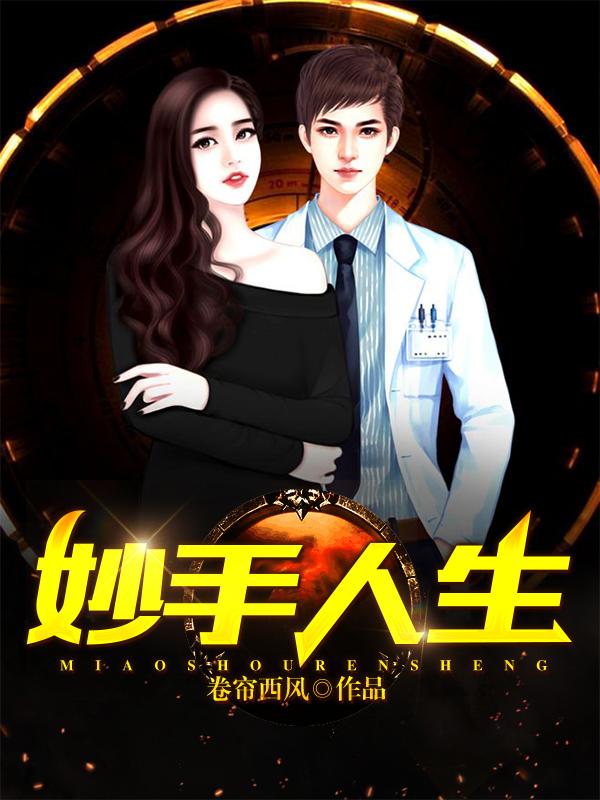奇书网>王阳明良知究竟是什么 > 四圣人之道 心即理(第1页)
四圣人之道 心即理(第1页)
四、圣人之道:心即理
阳明在龙场时期,其所思所想自然围绕着“丁卯之祸”的前因后果,尤其是针对当时官员们的种种反应与作为,深入剖析。因为这些人的作为(尤其与阳明亲近之人),冲击着阳明的内心,促使他重新思考,究竟是过去遵循的道德观念不合时宜呢,还是说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道德价值无法彰显出来?如果是道德观念不合时宜,那么什么样的道德观念才是合时宜的?假如道德观念并未有任何不合时宜,又为何这个社会无法彰显道德的价值呢?此外,身为当时国家中流砥柱的士大夫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坚持甚至是放弃了平常口说笔论的道德观念,而汨没于私欲之中,与宦官同流合污呢?其原因何在呢?这一切的问题都促使阳明对于他所信仰的价值观念体系,重新做一次检查,来寻求问题的根源,并进而提出他的看法。而这思考的最终目的,自然是要恢复一个道德完善的社会。
(一)对李东阳作为的反思
由于在“诛八虎”事件中,是以铲除宦官为目的,因此不论是赞成或是反对,即便是默不作声,皆标志着官员们自身对此事件的立场。不同的立场,也无形中形成一个分隔点,区分了这些平常相与谈学论道、诗文酬唱、互动频繁的士人圈子,形成一个“君子与小人”、“是与非”、“正义与邪恶”阵营之两方。就以大学士李东阳为例,由于其与刘瑾等交通的作为,不但引起士人间的纷纷议论,尤其对其门生故吏而言,其内心所受的煎熬,更是不言而喻。但是,终究有门生对老师下达最后通牒,罗玘(字景鸣,称圭峰,1447—1519)在写给其师的信中说道:
今则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无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终日。”此言非欤?彼朝夕献谄以为当依依者,皆为其身谋也。不知乃公身集百诟,百岁之后,史册书之,万世传之,不知此辈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谁复言之。伏望痛割旧志,勇而从之,不然,请削生门墙之籍,然后公言于众,大加诛伐,以彰叛恩者之罪,生亦甘焉!生蓄诚积直有日矣![108]
虽说此信只是一封老师与学生间的书信,但是却可以说是当时道德观念**然无存的最佳陈述。此信开头即说天下之人都知道“忠”这个价值观念已经不存在了,其原因是李氏是忠于宦官,而非忠于国君。也因此,士大夫们对于所谓经国大业也没有实践的空间。这显示出当时舆论对于朝局的发展是相当失望的,而应为此局势负责的人就是李东阳。而身为他的门生,罗玘在忍耐相当长的时间后,终于提出要不请老师回头,要不就请老师削去其门生之籍。罗玘眼见其师在宦官把持的朝廷里,仍然安居于大学士之位,不仅完全没有毅然辞官的动作,更没有要与宦官对抗的举动,毫无羞耻心。正所谓“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对罗玘来说,情何以堪。事实上,李东阳自己也知道外界是如何评价他的,他在写给另一门生乔宇[109](字希大,号白岩,1457—1524)的信中,即为其自身在“丁卯之祸”后,未能如同刘健与谢迁一般乞休致仕,辩解说:
走处身无状,不能勇决必退,以逃贪冒之讥。夙昔初心,中间时势,皆希大所深信而洞烛者,无容喋喋……自逆贼擅权,老奸附和,四三年来,修《会典》者,退降升职,修《实录》者,挤黜大半,当是时,旁观坐视,不能救正,咎有所归。[110]
不论是“诛八虎”事件后,未能与刘健、谢迁般离开朝廷;或是在宦官当权时,也未能对其擅权行为而有所“救正”,都使得李氏遭到外界的非难。而李氏在此信中,虽想得到乔宇的谅解与认同,但显然并未如愿。所以,李氏在另一封信中说道:
近两得书,寒温外别无一语,岂有所惩,故为是默默者邪?计希大于仆不宜尔,或前书过于自辩,致希大不自安,盖于希大有不容不尽者,若今道路谤责之言,洋洋盈耳![111]
从所谓“寒温外别无一语”,可以想见李乔师生间的关系,已经到了相敬如“冰”的情况,已非过去往来密切、相互酬唱的关系。而当时社会上充斥对李氏谴责的舆论,更证明身为李氏的门生,在“丁卯之祸”后,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因此才会不惜说出“请削生门墙之籍”的话来。这同时也显示过去一同诗文酬唱的士大夫们,也必定因此事件,彼此间的关系起了微妙的变化,也就是说,不仅是被贬谪的一方人生有了重大的变化,另一方也是一样,承受着与宦官同流的恶名将永远留在史册上的压力,就如同如罗玘所言一般。
不过,当时仍有些士大夫们并未持与罗、乔两人一样的态度,反而因平时与李氏的交情与关系,而宽恕李氏之所为。阳明好友崔铣就曾说道:
往西涯公(李东阳)处于刘瑾、张永之际,不可言臣节矣!士惠其私,犹曲贷而与之,几无是非之心,景鸣(罗玘)责引大义,愿削门人之籍。[112]
所谓“不可言臣节矣”,就是如同罗玘所言“忠赤竭矣”,也就是说李东阳道德观念的沦丧。而仍有士大夫因为私交而原谅李氏,对于崔氏而言,简直是毫无“是非之心”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崔氏此语亦显示出两个当时重要的现象,一是崔氏本身也是李东阳的学生,而从学生口中说出老师没有道德观念的评价,可见李氏门下士仍然有不少人不满其师的作为;另一则是即使当时是士大夫“几无是非之心”的景况,仍然有人是秉持道德的观念,不为流俗所倾倒,隐然存有一“拨乱反正”的伏流在。
阳明对李东阳的态度,亦是从亲密走向疏远。早年李氏与王华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这从其为王华母亲写祝寿诗的动作中可以看出[113]。另外,《年谱》亦记载当阳明会试落第之时,李东阳亲自来安慰鼓励的事情[114];而当阳明坠马受伤,李氏同样也来慰问[115]。这些事情表明了在“丁卯之祸”以前,李王两家来往颇多,但之后则是趋于疏远。例如在李东阳的文集中只有一封回给王华的信[116],信中除针对王华于南京吏部尚书致仕的事,给予祝贺外,并无语及阳明被贬谪之事。自此以后,从李东阳文集及王阳明的文集中,丝毫未见有任何往来的迹象。这种不相往来的情形,间接表明了两家人关系的决裂,其个中原因当然与李东阳在“诛八虎”事件中的作为,脱不了干系。而对于阳明而言,过去感情交好,在政治上、文坛上有一定地位的座师,如今沦落与宦官们同流合污,其间巨大的情感落差,必定冲击其过去所信奉的价值观念。且在刘瑾等人掌权时期中,多少官员们,靠着行贿而得美官、超迁等,世风日下,更加深阳明对现实的不满[117]与反省。这个反省的过程,是阳明价值观念转变的过程,更是其中心思想的起点。
(二)“一心运时务”的思想理论
当阳明选择了赴龙场任官后,相较于过去北京时的生活,改变是相当大的,不管是从生理层面,或是心理层面来看。生理层面指的是面对牢狱之灾、廷杖、贬谪、泛海历险到后来居住于贵州地区种种生活上的困难与不便,这些经历皆非当初上疏前所能料想到的。这些外在生理的改变也渐渐影响到其内在心理的层面,因而调适身心以因应现实环境,成为他初到龙场驿时最重要的事情。例如因为无粮可吃故向当地人学习农事,或是盖房子来居住、上山砍柴等,完全过着与当地土人一样的生活。阳明也常常感叹自己的处境,例如以鹦鹉自况,说到“能言实阶祸,吞声亦何求!”[118]过年时候,触景伤情,回忆过往在北京的时光,有诗云:“炎荒万里频回首,羌笛三更谩自哀。尚忆先朝多乐事,孝皇曾为两宫开。”[119]这些抒发当时感受的诗文,在在都反映出阳明初到龙场时的苦闷心情。但是,随着生活逐渐适应,阳明也颇能自得其乐,优游其间,例如有诗云:“绝域烟花怜我远,今宵风月好谁谈?交游若问居夷事,为说山泉颇自堪。”[120]不过,即使阳明在生活上已经没有适应的问题,其内心却仍然有其困扰在。之前曾提到,从阳明在狱中所作的诗,可以知道他对当时的横逆之来,是采取退让的态度,而其往后的做法也是照着《明夷》的卦意而为。到了龙场,仍然采取这样的处世态度,例如他在给刘寓生(字奇进,石首人)的诗中,以《蹇》卦来勉励,他说“蹇以反身,困以遂志。今日患难,正阁下受用处也”。[121]这个卦意也曾是阳明在狱中时所认同的。可是,这样的处世态度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现今处于“明夷”之时,那未来的人生,又是什么呢?对于这个新的“出处”问题的思考,一直盘旋在其心中,所以他在诗中提到:“也知世事终无补,亦复心存出处间。”[122]阳明自认现今无法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但是往后又该如何呢?对此问题,他朝向着两个方向来思考,一是辞官归隐,所以此时期的诗文中处处可见其思乡及归隐之情;二则有用世之意。例如他以桃花自况,诗云:
雪里桃花强自春,萧疏终觉损精神。却惭幽竹节逾劲,始信寒梅骨自真。遭际本非甘冷淡,飘零须信委风尘。从来此事还希阔,莫怪临轩赏更新。[123]
所谓“遭际本非甘冷淡,飘零须信委风尘”,隐约地说明自己现今的处境并非是其原本的个性,只不过委身于风尘之中。透露出阳明对于未来仍抱有一丝的希望,只不过说这个希望还不足以让他毅然而然舍弃归隐的想法。
阳明对于未来人生方向看法的转变,是与其针对现实环境所做的思考相关的。鉴于当时士大夫们的“小人”行为,社会是一“小人得志”的社会,因此阳明此时的思考重心是紧扣着如何成为“君子”的概念,也就是说在现今之时,如何让“君子”得以行其志。例如说他在《何陋轩记》中说道: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为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嗟夫!诸夏之盛,其典章礼乐,历圣修而传之,夷不能有也,则谓之陋固宜。于后,蔑道德而专法令,搜抉钩絷之术穷,而狡匿谲诈无所不至,浑朴尽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虽粗砺顽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谓欲居也欤?[124]
阳明自己盖了一个房子,援引孔子所言“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之语,意味着在这个简陋的房子里,住了一位“君子”,正是其夫子自况。而此文末段所言,莫不是针对当时“蔑道德”的情况而发的。阳明除了在此文中,以“君子”自居,在其他文章中,也充斥着他对于“君子”内涵的探究。例如:他讨论何谓“君子”,有《君子亭记》;何谓“君子的体用”,有《玩易窝记》;何谓“君子之行”,有《远俗亭记》;何谓“君子之政”,有《重修月潭寺建公馆记》等。这样一而再地讨论“君子”意涵的动作,充分表达出其想要做君子的意图。但是,要如何做,才能成为“君子”呢?阳明认为一个人之所以不能成为“君子”的关键,在于“一己之私”,他曾经回忆说道:
寻谪贵阳,独居幽寂穷苦之乡,困心衡虑,乃从事于性情之学。方自苦其胜心之难克,而客气之易动;又见夫世之学者,率多娼嫉险隘,不能去其有我之私,以共明天下之学,成天下之务,皆起于胜心客气之为患也。[125]
他认为当时的学者的问题,就是不能去其“有我之私”,所以才不能明天下之学等,一切问题的根源是“胜心客气之为患”。所以,去除此“胜心客气”,即是“君子”。用传统学术语汇来说,即是去除“私欲”,而阳明采用的方法即是“静坐”。《年谱》记云:
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