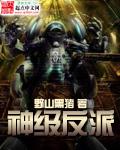奇书网>北京公共卫生管理 > 第二节 女性身体的再造(第1页)
第二节 女性身体的再造(第1页)
第二节女性身体的再造
在卫生话语的审视之下,近代女性的身体不仅存在各种不应有的束缚,还处于各种不卫生的状态之中。要实现强国强种的目的,必须消灭女性身体不卫生的状态,同时还要造就健康的女性国民以生产强壮的后代。在舆论的推波助澜下,社会和政府开展了具体的工作,卫生知识为再造女性的身体以合于国家和民族的需要提供了关键养料。
一、改造妓女的身体
在19世纪后半叶的西方世界,性病已经在社会上呈高发之势,当时一些医学传教士较早关注这个问题,并加以研究。1890年,嘉约翰(J。G。Kerr)在《博医会报》上撰文,提到性病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他以制定法律控制性病为解决问题的方法,指出19世纪初,欧洲就已制定一系列强制措施,对妓女开业作出严格限定,60年代英国议会陆续制定和通过了传染病条例,要求患病妇女开具医学证明。[64]嘉约翰还翻译出版了《花柳指迷》一书,可以认为是研究性病的第一本中文著作。
在近代中国城市中,女性卖**现象也普遍存在。1905年清政府成立巡警部后,京师及各省官方开始收取“妓捐”,在官厅登记注册挂牌者为“官娼”,其余为应取缔的“私娼”,民初形成了公娼制度。官方将娼妓合法化的做法使得妓女更形泛滥,娼妓问题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
民初北京的娼妓业空前繁荣。1917年在警厅登记的妓院有406家,妓女有3887人,加上最保守估计有7000人之多的暗娼,北京城的妓女数量达到上万人,相当于每81人中便有一个妓女,或每21个妇女中便有一人当妓女,其人数与城市人口总数的比例仅次于上海,居世界第二位。[65]1924年,据燕京大学教授步济时的统计,登记妓女的人数上升至3962人,民初以来的十年间增长了32%,增长速度竟比人口增加的还要快。[66]1929年相关的调查显示有妓院332家,妓女人数2752人。[67]至1935年仍有2558人。[68]北京在首都南迁后百业凋零,娼妓业亦逐渐趋于衰落,但妓女人数并未大见减少,而且还“由官的娼妓转至私的密卖”,花柳病感染的人群“由政客转至小贩,由先生转至学生,由大人转至走卒”。[69]
随着卫生知识的普及,人们逐渐认识到花柳病即性病是一种传染病,而妓女是最主要的媒介,因而被认为是传播性病的罪魁祸首。据1928年9月至1929年11月的统计数据,平均每5。5个妓女中就有一个患病的,所患疾病90%以上为性病,而无论何种等级的妓女患病几率基本是等同的。[70]妓女的身体是不卫生的,而嫖客则免除了这样的谴责,于是有的嫖客感染了性病,还抱着迷信的心理寻找没病的妓女来“过病”[71],这导致了性病的进一步蔓延,妓女的身体时刻面临性病传染的威胁。
除了性病之外,妓女的身体还受到许多不卫生因素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妓女的生存环境上,尤其是下等妓女的居住条件极差。在北京,三等妓女虽能每人一屋,但其中凌乱和污秽的情形不堪入目,四等妓女更是住所破败、黑暗、污臭。其次妓女的饮食极不规律,因为陪客事忙而饿肚子是常有的事,三、四等妓女连米饭也吃不上,日常主食仅有粗粮,更时有遭遇领班虐待不给饭食的情况。妓女身体遭受的最大摧残主要来自**易,嫖客不会顾及妓女的身体不适,妓女有时一天留宿多人,在经期、孕期中还必须留客,甚至有导致流产或致病者,还有的年龄很小即被强迫留客,其身体在发育期间就受到摧残,必然会影响身体的健康状态。[72]
在社会上,逛妓院是中国社会的普遍恶习。社会舆论虽然贱视妓女,但对嫖娼者较为宽容,“甚至代表舆论的报纸也以为鼓吹风雅为妓女大登广告,无知小民更不觉到花柳病的危险,以嫖妓为唯一的娱乐”[73],由此造成的严重的后果就是性病的泛滥。20世纪初十年后期,到北京各大医院就诊的人中有相当比例的性病患者,此外仍有很多人对性病的严重性根本认识不足。[74]
性病患者涉及各个职业,学生的比例很高。1915年据某医生的报告,“大约100学生中有90人受染花柳病毒”,情况之严重促使当年北京学界发起了反对嫖赌恶习的行动,青年学生团体“北京社会实进会”也屡次召开讨论会,拟定采取一些切实行动。[75]但反对嫖娼恶习未能形成大规模的运动,学生群体患病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据北京大学医学院皮肤花柳病科1926年至1930年五年间的统计,求诊患者中学生远多于其他职业,占至三分之一。即便考虑到北京的学校林立使得城市中聚集了相当数量的学生,以及该医院的学校背景,仍然使人们对这样的比例感得触目惊心:“莘莘学子,苟尚流连狭邪,不自振拔,则亡国灭种,祸不旋踵。”[76]
难以遏止的社会恶习造成娼妓业的泛滥,使得性病成为蔓延社会各界的传染病,而性病治疗因此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商机。20年代在警察厅专门药的登记册中,治花柳病者竟占十分之四,而这些药中大多掺杂以毒攻毒的猛药,重则致命,轻则亦会传染妻子,以致无后。[77]以治疗花柳皮肤病为主的诊所纷纷开设,在报纸上大作广告,俯拾皆是。[78]有的江湖医生劝说有遗精情况的男人到妓院去治疗,公共厕所里也贴满了各种治疗花柳病的广告。[79]社会上关于性病的各种言论甚至谬论流传,影响了人们对性病的正确认识,进而影响到感染性病者的及时治疗,更间接推动了娼妓业的发达。
社会现实显示了娼妓问题和性病传播的严重性。舆论对此虽早有议论,但直到五四时期才开始得到热烈讨论,医学与卫生学为这场讨论提供了科学的依据。1919年,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废娼问题》一文,揭开了这场讨论的序幕。他提出五大必须废娼的理由,其中之一即为尊重公共卫生,因为娼妓造成的花柳病传染,“不但流毒同时的社会,而且流毒到后人身上”,对于人种存亡影响很大,若娼妓一时难以废止,则暂时的解决办法是将其放在国家的监视下,实行检查身体的制度和设置相当的卫生设施。[80]
1923年,《妇女杂志》将当年第三期订为《娼妓问题号》,集中发表了对娼妓问题的一些讨论,涉及娼妓制度的根源、娼妓的社会危害等,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其中《娼妓之卫生取缔》一文通过翻译国外对于娼妓卫生问题的前沿讨论,主张国家应负起社会卫生的责任,对妓女的身体实行卫生的监视。[81]1927年,《妇女杂志》再次发表这类讨论,留美博士胡定安提出“性病是国民病之一种”,而妇女是媒介主体,建议国家通过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全面防治性病,以达到“监视”和“保护”妇女卫生的目的。[82]
在这场讨论中,卫生的引入使得对妓女的谴责不再停留在道德层面,而上升至科学和国家的高度。舆论不断论证妓女不卫生的身体,“监视”一词被屡次提及,其话语的逻辑就是:妓女的身体是不卫生的身体,应该将其置于国家权力的严密控制之下。这样的逻辑在2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由于妓女传播的性病危害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因此舆论将解决娼妓问题的希望寄托于政府,娼妓管理的良善与否,甚至能否实行废娼,成为舆论评价政府政绩的指标之一。这为市政机构的娼妓管理带来了压力,但也为其增强行政控制能力提供了社会支持。
1906年,外城巡警总厅订立了《管理娼妓规则》,以此前外城卫生局将妓女登记上捐的工作为基础,将登记入乐户的妓女分为四等,提交照片和相关信息以申请执照,并规定身患传染病和花柳病者,以及怀孕五个月者不得接客。规则中还可见外城警厅有设立娼妓检验所的计划,要求俟其设立后就进行妓女身体检查,患病者必于治愈复验后才准接客。同时批准实行的还有《管理乐户规则》,其中要求娼妓患传染病及花柳病时须速送医院诊治,且报明该管区。[83]但对妓女实行身体检验的机构在清末未能设立,切实的妓女检验工作也未有施行。
民国以后,京师警察厅鉴于“保全人民健康,实为卫生警察第一要政,而检验娼妓,尤为保卫一般健康,预防传染病之最妙良策”[84]。根据卫生处的职掌事务,断诊娼妓健康是日常的工作之一。虽然警察厅对设立娼妓检验机构“早有提议”,但“因事繁琐,于风化、习惯均不相宜”[85],致使检验机构在民初迟迟难以建立,具体的检验工作也没有成为常态。
市政机构存有对妓女进行身体检查的意愿,但仅在性病蔓延恶化的情况下采取了临时性的措施,未能形成一项连续和稳定的政策。如1917年,京师警察厅曾拟派医生前往妓院检查,每一二星期一次,查出患病者立即停止营业,抗拒检验者重惩。[86]而至1920年,鉴于上一年的医疗报告中花柳病竟占至三分之一,警察厅拟议每年春季实行对花柳病的调查、检验和疗治一周。[87]如此短的时间内集中进行娼妓检查,其试探和象征的意味大于实际的效果。警察厅甚至“拟定药方,印为传单,分送八埠各娼寮,令其按法配制,如遇妓女染受梅毒,即按法服药”[88]。但直至第二年春季似乎都未有动作,到6月时因梅毒病症较往年倍增,警察厅最终决定从6月20日开始,要求各埠妓女前往外城医院候检。[89]此次检验与否及效果未知,但当年10月内政部无法坐视花柳病的蔓延,促使警厅决定近日内再次对妓女施行一律检验。[90]
只有在专门的检验机构设立后,对妓女的身体检查才能渐趋于常规化和制度化。1918年,警察厅曾提出仿照日本开设诊治妓女的医院,院址拟设于香厂,拨妓捐为建设用款,但最终仍因资金无着而作罢。[91]1923年,警察厅卫生处再次提出筹办妓女检验所,每星期检验妓女一次。[92]检验机构最终于1927年初成立,位于外城官医院,名为检验娼妓事务所。[93]
1928年北平特别市卫生局成立后,结束了市政机构监管妓女身体的碎片化状态。检验娼妓被列入公共卫生第一期的应办事项中,要求厉行检查,并设立专门的检验和治疗机构。[94]妓女检治事务所也很快设立,从其基本章则中可见,该所对登记领有执照的妓女进行定期的身体检查,按照妓女的等级制定收费标准和检验间隔,一等妓女只须每月一次,而四等妓女则须每周一次;检验项目包括内诊、全身检查、细菌和血液检查,凡检查出患病且具有传染性者停止留客,并要求立即医治,不遵者重惩;该所还承担花柳病防治宣传工作,采用每日讲演、图画标语、幻灯电影、展览陈列和分送印刷品的方式对来所的妓女进行宣传教育。[95]事务所成立当年就检查出为数甚多的患病妓女,由于事务所难以承担全部的治疗工作,故由卫生局函请各公私立医院对持有该所诊疗单前往各处治疗的妓女给予优待,减收治疗费,并注意医治以期速愈。[96]
在1930年卫生局裁撤后,妓女检治事务所就只以检验为主,直至1934年卫生局重新恢复后,将其独立出来隶属于市立医院之下,才恢复了治疗事务。[97]此时的检查频率不再根据妓女等级,而是统一为每月一次,凡检查出患病者一律要求停止营业,速行医治,检治所提供免费的治疗服务。[98]所有妓女都被强制要求进行身体检查,屡不检查者,由公安局各区署协助严加催促,并对有病留客妓女认真取缔。[99]检治所并对妓女一律施行种痘,以预防天花。[100]
市政机构要求经过身体检查确认患病的娼妓必须接受治疗。根据京师警察厅的规定,在未治愈之前绝对不准再留客,必须在相当时间内将所患疾病诊治痊愈,经检验所再次检验确实无病后,始准再照常营业。[101]对于违章留客的妓女,京师警察厅给以严厉处罚。[102]对于隐匿不报的乐户和娼妓,一经查觉,必定照章处罚。[103]虽然制度严格,但在实际操作中,警察厅并未能对所有娼妓一律平等检查。1927年检验所成立后,警察厅即普遍开展了对娼妓的身体检查,但随后一等乐户清吟小班代表呈请免验一等娼妓,警察厅认为“所有二等以下娼妓患花柳病症者较多外,一等娼妓患病者,数目尚较少”,于是对于各小班妓女,特另订免验办法,令每人每月出具保证书一次,附缴保证金10元,再由各该班执事人出具切结保证。[104]这种通融方式也为患病妓女寻找变通办法留下了空间,如乐户老板可以通过行贿送礼给检治所等方式使其免发禁止留客的通知[105],社会上也出现了宣称可以“请托免检或检验有病各妓而能以疏通留客”的情况[106]。
鉴于市政机构不彻底的态度和作为,对妓女的身体实行卫生检查能否切实地控制性病的传播,当时的舆论基本持否定态度,但亦承认卫生检查是在彻底废除娼妓之前不得不采取的一个暂时性的措施。对于北平妓女检治事务所的工作,就有人根据调查担忧地指出,其只对于病重的妓女采取干涉,而其他妓女均能得到检验所的盖印,这简直就是为花柳病传染提供了一层保障。[107]
30年代初,卫生专家俞凤宾在对近代中国五十年的卫生状况进行总结的文章中也谈到了娼妓问题。他提出了社会上扰乱治安及犯法作恶者大半为低能的人,而低能的人往往由花柳病之家产出的逻辑,以此证明花柳病为害之巨,并从专业技术的角度对娼妓检验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估:
……至按期检查,表面上较不检验为妥,而实际反可增加传染之机会。何以言之,查验花柳病,非短期之视察,即可判定,盖血清反应之试验,非数小时不能竟,用显微镜试验,查得病菌或螺旋虫,固可断定其有病,若未得之,尚难确定其有无,况检验员之肯用上列二法者,吾人未之闻焉,仅用外表检查法,仅可欺骗童稚及愚鲁者,何足以弭害……检查员非上等有道德之医士所愿任,盖于最短期内判某妓有花柳病,无论其学识如何丰富,必不能骤下断语,假使某妓在检查员眼光中认为无病,而许其卖**,苟该妓领执照后于五日内可染毒病,则后之冶游者,往往因有执照之可恃,而大受其毒害。[108]
娼妓职业造成的不卫生身体,对妓女产生了多重的约束。妓女的身体受到嫖客的**,时刻面临性病的威胁,还受到妓院领班的虐待,处于不健康的状态。同时妓女又由于这样不卫生的身体,成为舆论批判和国家监视的对象,被强制要求进行严格和定期的身体检查。在检查过程中身体遭受强制的状态使许多妓女将其视作畏途,1937年《大公报》上就曾报道,有的妓女“害怕检验人员的钳子,死也不肯检,甚至有愿意退捐而不愿受人钳制的”。[109]
即使妓女脱离妓院,也难以获得普通人的身份和生活,多数人只能进入济良所。1906年,协巡营在处理玉莲清吟小班掌班张傻子虐待妓女案件之后,为使“受虐待之诸妓女能有活路”[110],决定设立济良所。济良所的房屋为张傻子的玉莲班及张傻子的住房充公而来,并有北京的绅士捐借柏兴胡同路南原有水会公所。[111]在外城巡警总厅和绅士的努力下,济良所得以设立。
但济良所的用意虽好,却办理不良,只能成为又一个继续束缚和摧残妓女身体的地方。从1919年社会学者甘博的调查中,可知济良所中使用了大量的警察,并从管理者的性格和所中姑娘羞愤的表情上可以推知,所女受到的待遇不够人道。[112]1921年,《晨报》上详细披露了济良所对入所妓女的非人道对待:
已入所者庾毙时闻,而受领家虐待之娼妓闻济良所三字,几视为地狱,如此复何济之可言,良之可说。昨闻由该所嫁出之某女言,妓女入所后,多年只有随身衣服,所中并不为添制,以致破烂不堪,无衣替换,并且无论冬热均须十四人一床,冬日犹可忍受,夏日则蚊虫成群,人人体无完肤,加以无衣替换潮气熏蒸,恶臭难闻。平素饮食,又粗糙异常(多吃窝窝头),颇难下咽。因此所女时常发生疾病,辗转求死。主管者见之又并不为之医治,即偶尔延医一观,则药饮乱投,一榻呻吟,无人看视,其状殊为哀惨,不堪目睹。[113]
虽然妓女多不情愿,但进行身体检查能使妓女获得一定程度的卫生服务以及与性病有关的一些卫生知识,客观上增进了妓女对自身卫生的关注,并使一部分患病者得到了治疗,暂时缓解了娼妓职业对妓女身体带来的持续威胁。但妓女的身体要最终实现卫生的状态,不能仅止于依靠身体检查和治疗,还应使其脱离娼妓的行业,并且获得自主独立的生活,才能得到健康生存的基本保障,而这需要整个社会环境的彻底改善,在近代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完成的任务。
通过对妓女身体进行改造的讨论和行动可以看到,舆论与官方皆以卫生为出发点,希望遏止性病加剧蔓延的情况,但两者亦存在诸多差异。舆论对妓女身体状态的关注和忧虑,根本着眼点在于国家和种族的存续和健康。国家要摆脱落后状态,种族要解除灭亡危机,就必须完全改造女性群体中这部分不卫生的身体,彻底消灭娼妓这种生产和传播不卫生身体的职业,即“‘所谓解决娼妓问题’就是灭绝娼妓,不复使她们存在于世”[114]。而政府除了卫生的顾虑,还要考虑财政收入与妓女安置等问题,因此对废娼行动并不积极,仅愿意采取检查妓女身体的治标之策。这种方法不仅难以彻底改造妓女不卫生的身体,还进一步加剧了妓女身体的不自主状态。
二、再造“国民之母”
女性身体最重要的特质是孕育后代,因此近代女性作为国民的首要表现就在于女性是“国民之母”。“盖女子者,国民之母也。一国之中,其女子之体魄强者,则男子之体魄亦必强。”“将来造成新国民,养成优民族,皆此辈女子之责矣。”[115]在“富国强种”的渴望之下,对健康母亲的要求也十分迫切:“现在的世界,第一要有健全的国民,然而健全的母亲,实为根本。”[116]近代民族国家话语要求女性作为母亲的身体应该置于国家与社会的保护和监视之下,以近代卫生的标准进行再造,从而确保女性孕育健康强壮的后代。为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提供产科卫生的保障,向孕产妇灌输卫生的知识,并提倡节育以确保优质的生育。
在传统中国,女性身体受到的最大威胁来自生育,“古来的医家,即以妊娠,分娩,及授乳三者,为女子的特殊疾患,认为妇人身体之苦痛,官能之障碍,都是因此而起”[117]。到近代这种状况并未得到较大改观,30年代初,中国孕妇的死亡率仍然高居世界各文明国家之冠,这被认为是不注意助产事业的后果。[118]在北京,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几占人口死亡率的三分之一,倡导卫生的知识分子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责任在于旧式产婆。[119]因此,保障产妇卫生,应改进助产事业,要一面取缔旧的产婆和接生方法,一面训练新的助产士和提倡新法接生。
产婆,北京称之为“姥姥”,又名“收生婆”,也称“稳婆”,多为不识文字的妇人,常以接生赢利而不顾产妇身体,因此造成的孕妇婴儿死亡时有所闻。[120]从近代医学卫生知识的角度来看待产婆,其弊有三:
一、不明产科生理与病理之别,无术辨别于前,自不能救急于后,似此情形,果有难产,欲求产妇之不死,何可得哉。二、不知消毒灭菌之法,致产妇发生产褥热,或婴儿发生破伤风而死者不少。三、不明饮食卫生之法,使产母在孕期产期产后期,调养失宜,而起自家中毒,或骨质软化诸症,在婴儿则乳养事宜,致肠胃及呼吸器发生疾病,因而丧命者,不知凡几。[121]
民初,京师警察厅鉴于产婆误人的现象频发,于1913年制定了《京师警察厅暂行取缔产婆规则》。该规则采取登记的办法约束产婆,经考核获发许可证者方准执业。当时有意愿从事接生者即可领照[122],总数在四百人上下[123]。经批准注册的产婆方能在门前悬挂木牌标明,一般多写着“某氏收洗”、“快马轻车”、“吉祥姥姥”等字样。[124]市政机构在实际工作中更多的只是查禁无照者,对领照者若无事故则未有干涉,属于消极的管理。社会上还曾有公共卫生调查团将产婆善恶列入调查事项,但这类组织的作用主要为了“调查报告以助官厅所不及”[125],也无法形成有效的干预。
近代卫生知识对产婆的态度是完全否定的,但从社会现实来看,大部分产妇仍然依赖产婆进行接生。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习俗的惯性,产婆“大多数皆系土著或承袭先代工作,于本市居民脑中,印象甚久,根深蒂固”[126],而且产婆对新法接生进行恶意诋毁,她们往往“造出种种无稽之谈,住户之妇女亦皆深信不疑,故对于新式产婆多扰缩不前”[127];另一方面亦是由于新法接生的不普及,专门的产科医疗人员太少,且生产费用较高,“虽有产科医之设立,也不过是为贵族人而立”[128]。鉴于这种情况,政府调整了对待产婆的策略,采取教育的方式使其掌握基本的卫生知识,尽可能减少接生过程中的不卫生现象,并希望产婆在无法解决接生困难时主动向西医求援,以期最大限度地降低生育过程中的死亡率。
1927年12月,内务部制定了《管理旧式产婆暂行规则》,再次强调了警察机构对产婆的管理责任,规定警察厅应分期或分区举办或委托公私立医药机关办理临时产科讲习所,经警察厅核准的旧式产婆应于规定期限在产科讲习所练习1至2个月,学习内容主要有妊妇保护法、产褥妇保护法、初生儿脐带固扎法、初生儿养育法以及清洁消毒大意,学习期满且成绩优良者,由警察厅发与修业证书,并呈请内务部发给其简易助产执照,成绩拙劣者将被撤销核准的产婆执照。[129]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也公布了《管理接生婆规则》,限定接生婆的开业资格,规定地方官署应设立临时助产讲习所,向接生婆讲授接生上必要之知识。[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