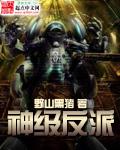奇书网>北京城与人读书报告 > 六 方言文化(第1页)
六 方言文化(第1页)
六方言文化
北京人与北京话
北京人对其“说的文化”的那份自豪,那种文化优越意识,一如对其“吃的文化”。这一点也像法国人,法国人对法国菜与法国话的自豪与优越感。不过据说由于美国的文化渗透,法国人的语言自豪正在日益丧失。北京城虽有“英语角”,这一种危险却还远不是现实的。
说与吃同样依赖于口腔运动。“民以食为天”,人是符号动物,可知吃与说是最基本的文化。这倒让人惊讶于如上的文化自豪与优越意识的稀有。人们的文化憧憬过分地被庞大而耀眼的东西吸引了。北京人与巴黎人,却保有了上述最基本的文化感情。与饮食文化一样,方言艺术也要闲适悠然才能造成。“说”这种行为曾经是包括王公贵族和里巷小民在内的北京人的重要消闲方式,以至聊天(“海聊”、“神聊”、“神吹海哨”、“侃大山”等等)与提笼架鸟一样,竟也成为北京人的典型姿态,易于识辨的特殊标记。这一方面,北京之外,惟有以其方言而自豪的四川人著名的“摆龙门阵”差堪比拟。近闻有人批评四川人的语言陶醉出于“盆地意识”,尚未见有对北京人的类似批评。
北京人如珍视其文物古迹、珍视其胡同四合院一样,珍视北京话。关于北京的怀乡病,竟往往也由于北京方言的魅力。林海音那一组“城南旧事”使用方言处,即可看出这样的心理背景。北京记忆也非赖有北京话、北京方言才有可能真正复活。听觉记忆在这里也如味觉记忆一样顽强。
《京华烟云》极写北京人语言之美,写女主人公木兰“听把北京话的声韵节奏提高到美妙极点的大鼓书”,并从日常说话,“不知不觉学会了北京话平静自然舒服悦耳的腔调儿”。〔45〕这语言之美在林语堂看来,是北京文化价值攸关的重要部分。
文化优越意识简直可以看做北京人作为京城人的一方徽记。更妙的是,京味小说在由这一方面呈现北京人时,也感染了、分有了北京人的语言陶醉。《“四海居”轶话》(邓友梅)写人物说着“一口嘣响溜脆的北京话”,“一口京片子甜亮脆生”。这“嘣响溜脆”、“甜亮脆生”较之其他,更是人物作为北京人的身份证、资格证书。〔46〕《索七的后人》(邓友梅)中的人物则说“北京当然是好地方。甭别的,北京人说话都比别处顺耳。宁听北京人吵架,不听关外人说话”。未免偏执,却也正是北京人的声口。《四世同堂》写韵梅:“小顺儿的妈的北平话,遇到理直气壮振振有词的时候,是词汇丰富,而语调轻脆,象清夜的小梆子似的。”很难想出比“清夜的小梆子”更醒神且含着爱意的形容了。《正红旗下》写那个完美到近乎理想的漂亮人物福海,也不忘强调他的“说的艺术”,说的艺术几成为“漂亮人物”的必具条件。“至于北京话呀,他说的是那么漂亮,以至使人认为他是这种高贵语言的创造者。即使这与历史不大相合,至少他也应该分享‘京腔’创作者的一份儿荣誉。”(着重号是笔者加的)这类文字有时令人疑心作者在借端表达他本人的文化优越感。
上述语言陶醉中,有更朴素更基本的文化认同,其心理又非惟北京人所有。於梨华《傅家的儿女们》写留美华人傅如曼在异国使用中文,“立刻觉得浑身舒服起来”。她想不通“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别一个国家住上这么些年?怎么忍受得了说上二三十年的英文,不是自己的语言?”民族感情是赖有一些琐细经验维系的。它在这“琐细”上才显出切实可靠,是人的感情。这或也是使但丁使用杜斯加尼方言写作《神曲》的感情(但丁在去世前不久写了《俗语论》)?同类感情则使得离开了苏联本土的诗人布罗茨基宣称自己“是属于俄国语言的诗人”。语言是语言共同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反映着其所由产生的特定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语言对于文化感情的维系,或许比之任何其他因素都更能持久与强韧。
北京方言是北京文化、北京人文化性格的构成材料。《京华烟云》借人物感触写到“北京的男女老幼说话的腔调儿上,都显而易见的平静安闲,就足以证明此种人文与生活的舒适愉快。因为说话的腔调儿,就是全民精神上的声音”。虽有国粹派气味,但由北京人说话的“腔调儿”推知其情态心境,却是极细心的。说着一口脆滑响亮的北京话的北京人,其北京话既传达着呈现着也在某种程度上规定着其生活与性格。“甜亮脆生”与“平静安闲”中,有闲逸心境,有谦恭态度,有潇洒风度,有北京人的人际关系处置,有北京人的骄傲与自尊。北京话中极为丰富的委婉语词,更标志着一种成熟的文化,敏于自我意识、富于理性的文化。你甚至会想到,说着这样一口脆滑的京片子的,是不会举手对人施暴的。你自然也不大敢指望他投袂而起。因为他是这样的温雅聪明,世故得令人不觉其世故,精明到了天真淳厚。北京话完成着北京文化,同时又像是这文化这人文面貌的漂亮装潢、醒目标签。它本来也的确是这文化中最易于感知的那一部分。
成熟的有教养的北京人并不喋喋不休(北京人或许比别处人更忌“贫”),节制与审美态度在这里同样是“成熟”与“教养”的标志。汪曾祺的《云致秋行状》中主人公的聊天,其趣味纯正处最近正宗。“他的聊天没有什么目的。聊天还有什么目的?——有。有人爱聊,是在显示他的多知多懂。剧团有一位就是这样,他聊完了一段,往往要来这么几句:‘这种事你们哪知道啊!爷们,学着点吧!’致秋的爱聊,只是反映出他对生活,对人,充满了近于童心的兴趣。”好处就在这无目的、非功利上,由此使聊天近乎艺术行为,当事者也有近于艺术创造的心境。这艺术创造不待说是中国式的,因而语言陶醉中自有理性的节制,不至于忘形尔汝。“致秋聊天,极少臧否人物。”“他的嘴不损。”善言辞,却不逞舌辩,图一时快意。“闲谈莫论人非”,是世故,也是修养。在主人公,自然也因宅心仁厚。“他的语言很生动,但不装腔作势,故弄玄虚。有些话说得很逗,但不是‘膈肢’人,不‘贫’。”有这些个,才能说“他爱聊天,也会聊”,品味比别人(比如剧团的那位)高着一层。能欣赏这诸般好处的,品味也自不低。“说”至此才成其为“艺术”。〔47〕在聊天这老北京人的常课上,云致秋其人可称全德。除去道德自律不论,其语言趣味,就最得北京人方言艺术的精神。
“说”一旦艺术化,信息传输的功能就不再“惟一”。北京人有时使人感到俨然为说而说,为说得漂亮而说——对意义并无甚损益的“漂亮”;为了更好地诉诸听觉,诉诸细腻的语言感觉。“说”由是成为娱乐手段(当然在一定场合)。在这种场合,“说”的心态,也正是享受生活的心态。这势必有助于提高语言的美学功能。
京味小说不止一处写到北京人的以“说”找乐(如京俗所谓“逗闷子”),自娱娱人。这也是对于物质匮乏的精神文化的补偿。以“逗”为乐,得到类似于喝豆汁、杏仁茶的满足感,生理与心理的安适。较之豆汁,更是随处可得的满足——写到这里,才补足了上文所谈的北京人的生活艺术。谈北京人的生活艺术而不及于其以“说”找乐、语言陶醉,是必不能充分的。说的艺术,其条件,其心理内容,其美感效应,应当比之别的更有利于说明北京人“审美的人生态度”。〔48〕
“说”作为艺术行为最值得注意之点,在“说”的方式(怎么说)被提到了“目的”的位置上。这里有某种市民的“形式主义”。因而北京话并不总以简洁、经济为美,其“味”倒是常常要由冗余成分、剩余信息造成的。废话不废,是在美学意义上,在美感效应上,在语言行为作为艺术活动的条件、情境上,倘若不避庸俗社会学之嫌,这或者也是宗法制下的生活所培养的美感趣味?说者追求“味儿”,听者于得信息外,也得其言语中的“味儿”,从而语境、语感等等一并受到注重。附件挤入了主体,外在条件实质化了。有时更是语言技巧重于语义,不惜为了说得聪明、俏皮而牺牲点效用——亦合于北京人天性中的慷慨大度。这儿有一种特殊的语言功能观。“说”的成为艺术,自然赖有那些不但赋有语言才能,而且特具审美能力,说而求其味,听而知其味,善能玩味语言、鉴赏语言之美的人们。当然,为说而说,是不免极端的说法。更多的情况下,传达信息的目的与传达语言趣味的目的兼重,既实用又非纯粹实用:竟也恰合于北京文化的特点!
京味小说使人感到,它们的作者在有关语言功能的理解上,与所写人物是相通的。汪曾祺曾这样谈到文学语言:“中国现代小说的语言和中国画,特别是唐宋以后的文人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中国文人画是写意的。现代中国小说也是写意的多。文人画讲究‘笔墨情趣’,就是说‘笔墨’本身是目的。物象是次要的。”〔49〕
在文学语言问题重新重要起来之先,京味小说作者以其创作所表达的有关见解或也可以认为是一种“超前”?京味小说语言不大追求信息量,它以味胜,背后是对于以语言本身作为审美对象的接受期待。有时也不免于“玩儿”文字,“玩儿”话语。你由小说文字间,确也读出了北京人式的语言陶醉,以说得漂亮,以能自在地驱遣文字为乐事的享受态度。陶醉于所运用的语言的质料之美,复又陶醉于自己加工创造的语言能力,陶醉于结果更陶醉于过程——“写”的自娱性质。这种语言意识和创作状态有助于造成作品特有的轻松感,“幽默”也赖有同一心态而产生。因上述种种,作品文字给予你的审美愉悦补偿了其他,如内容的瘦损、形象的单薄平面。凡此在目下也许已不值得特为指出,但在老舍创作盛期的三四十年代,在当代京味小说创作勃兴的1982、1983年,都应当是值得注意的文学语言现象,虽然始终并未以此引起足够的注意。
在如张辛欣、陈建功这样的青年作者,北京方言活跃的再生力,所拥有的表现力,确也成为了他们创作风格的倚托。由所负载的信息与负载信息的方式,透露出文化意识的自身矛盾,是青年作者那里通常可以见到的情况。而在汪曾祺、邓友梅,“认同”是在形式与内容、语言及其负载的“文化”的同一中充分呈现的。你又在这里具体地触到了城与人。正是“城”不见形迹地参与了“说”,鼓励着上述语言趣味,以其方言文化助成着作者们的语言陶醉。城在经年累月的文化创造中,创造了关于自己的描述方式。以独特语言描述北京人的文化存在者,那语言本身又属于北京人的文化存在方式。
最优越处通常也即最脆弱处,语言优势正易于成为语言陷阱。说而又不免于“为说而说”,以有冗余信息而成其为“艺术”,本身即含有一种危险,即“贫”、“油”。故“京油子”、“耍贫嘴”一类批评并非无因。信息载体的语言不以负载信息为惟一目的时,有可能审美化,稍稍逾限即沦于“贫”——纯粹的废话。“贫”也是一种语言污染,且最易于败坏北京话的美感。文化品质高的语言从来都是较为敏感娇弱的语言,“节制”在北京方言艺术几乎有了“生死攸关”的意义。“适度”与“过”,京味小说自身即含有标准。在我看来,如《那五》、《安乐居》等,就是因节制而保持了美感的例子。范本并不只在古典作品里。
语言优势是一种文化优势。北京人的语言优势多少也是赖有“京华”的绝对优势地位造成的。金克木曾谈到《红楼梦》、《儿女英雄传》“证明了满族统治者所推行的北京语的‘官话’的文学语言已经不可动摇地要在全国胜过各种方言”。〔50〕近代史上的上海虽然如暴发户般地珠光宝气,以致把京都衬得更其破落,北京却依然有上海挟其经济实力终不能胜过的优越地位。政治文化的大题目姑置不论,单是上海话就决不可能取得有如北京话的“官话”地位和其普及性。这种普及在当代尤其近几年有更强大的势头。其中不可免的有北京的“文化扩张”。〔51〕多少也因此,在方言文化广泛开掘的当下,北京方言文学享有非一般“乡土文学”可比的尊荣。这也鼓励着北京方言文学艺术的创造热情并准备了良好的接受条件。当然普及也赖有这种语言的自身条件,赖有它的魅力,它特具的功能。因这文化熏染,久居北京的他乡作家,往往于不觉间,把京味糅进了别一种“生活”里,所使用的语词、句法,以至“说”的神情态度,透入“说”中的语言意识,都隐约有北京的文化渗透。
这就是京味小说作者进行创作的语言环境,其得天独厚处也如北京人。在北京人和居住于北京的人们中,他们又是对北京方言文化做出最积极贡献的一部分。他们以北京方言口语为坯料,烧制出最具美感的语言。他们是致力于提纯、加工,提高方言品质的创造性的语言工作者。更重要的是,他们以其作品培养了对于这种方言的审美兴趣与审美能力。他们作品的成功固然赖有方言魅力,方言魅力又赖有他们的创作而造成。
艺术创造中,以生为新易,以熟为新难。京味小说作者选择的,是后面这较难的路。正因俗常、熟,使用中更排斥纯粹摹仿。这种方言固然助成创造,同时也以其敏感,苛刻地检验着使用者的审美能力、语言能力,在他们之间无情地做出区分。创作者创造性的语言运用,是使俗常转成新鲜的条件。老舍曾发愿烧出白话的“原味儿”来,又说自己所使用的“既是大白话,又不大象日常习用的大白话”。〔52〕在白话规范化,文学语言渐有套路、渐成滥调的二三十年代,老舍的北京方言运用,使得语言清新鲜活。这也是一种“陌生化”。俗常、熟识的事物因艺术化使人感到陌生,对其持审美态度。在与“文革”文学的样板语言、新时期文学一时通行的共用语言的比较中,京味小说的方言运用也同样因鲜味而令人感到陌生。
苏珊·朗格曾经说到过彭斯诗作“方言的运用表现出一种与诗中所写、所想息息相关的思维方式。彭斯不可能用标准英语说到田鼠,甚至注意田鼠时也不能想到它的标准英语的名称,……”〔53〕类似情况在我们这里,大约限于民间创作,比如道地农民诗人创作的那种情形;由于长时期的言、文分离,知识分子采择方言作为语言材料,意在营造情境、氛围,他们自己,通常是用另一套语言思维的。老舍甚至不像当代京味小说作者那样全用方言(除非在人物自述的场合,如《我这一辈子》)。多数情况下,他将所用语言材料因不同情境而区分开来,把人物与他本人关于人物的思考以语言形式区分开来,却又力求将不同形式的语言衔接得天衣无缝。至于全用方言力求纯粹的当代作者,也不同于用方言思维的胡同居民。但话说回来,方言确又有助于他们将思维透入北京文化的里层,以至像老舍,一旦放弃这种语言形式,几乎等于放弃了老舍式的主题。在这里语言正是一种文化系统,包含着价值态度、审美意识等等。它决不仅仅是工具:中性的,冷漠的,对其负载物漠不关心的,无机的。在这一点上不妨说,新文学史上还很少有另一位作者,特定语言材料之于他犹如对于老舍这样,决定着思维的路向和对于生活的参与方式。在这种意义上是否又可以认为,方言不仅被用以表达,也用以思维?只不过其间关系并不同于道地“农民诗人”罢了。
方言文化,是京味小说中北京文化的重要部分。新文学自“五四”到30年代,都在强调平民化、大众化,提倡采撷民众唇舌间的语言,却并无“方言文学”的明确倡导。〔54〕文学、文学语言的创造自有其规律,并不必待提倡。老舍之外,沙汀对四川方言的提纯运用就很可称道。使用口语(30年代张天翼的创作在这方面很有成绩)被理解为文艺“大众化”的具体表现。方言的运用在“大众化”的总意图下,缺少负载地域文化的自觉(尽管方言本身即“地域文化”),也难得被自觉作为构造语言个性的材料。虽有助于脱出“五四”以来文学的“新文艺腔”,又有造成另一种“共用语言”的可能——一种方言对于其他方言区虽为个性,在此方言区内又属共性。这多少是一种语言材料的浪费的使用。
在当时,老舍的努力易于被承认的,在丰富现代白话的表现力方面。较之30年代流行的“新文艺腔”,老舍使用的,是更依赖语境、特定语言场的语言。其依语境而有的省略、倒装等等,以脱出严格文体规范的灵活性,引进了生动的生活力量。这种非规范的极灵活的语言运用,往往把情节与环境同时说出,造成了丰富的空间印象,使人惊讶于口语的形象塑造力。
声音意象与说的艺术
传统中国人重农轻商,鄙薄商业行为,他们的北京记忆里,市声,北京街头商贩的叫卖却偏能经久,而且所记住的往往并非叫卖的内容,倒是其腔调。近有电视片《燕市货声》,即是复制这已失去着的老北京记忆的:对于老北京的声音记忆。叫卖是市井艺术,构成了北京人日常声音环境的一部分。叫卖中的声调运用,对于北京方言的注重声音形象,不妨看作有几分夸张、戏剧意味的象征。
上文所引京味小说关于人物说话的形容,“嘣响溜脆”、“甜亮脆生”,以及“清夜的小梆子似的”,强调的都是声音形象。鲁迅曾以“响亮的京腔”与“绵软的苏白”对举,“绵软”是质感,“响亮”则是声音形象,概括都精确。京腔的确给人以光滑感(不柔腻)、明亮感(不沉郁)。它如上所说,响亮,明亮,“脆生”,不缠绵粘腻,不柔靡,其中亦含有北京的文化气质。京味小说给人的明亮感也部分地赖有其语言:少晦黯不明的情致,少幽深曲折的境界。由另一面看,过于明亮难免少了含蓄。但有那份不可比拟的生动,足可作为补偿了。
上引鲁迅所说是“京腔”。北京方言是极端依赖于“腔调”的语言。林语堂《京华烟云》谈北京话,首先是“腔调”。老舍写那个体面的旗人后生福海的善辞令,北京话说得“漂亮”,也不止在措词得体,而且在腔调动听:“是的,他的前辈们不但把一些满文词儿收纳在汉语之中,而且创造了一种轻脆快当的腔调;到了他这一辈,这腔调有时候过于轻脆快当,以至有时候使外乡人听不大清楚。”(《正红旗下》)——又是一种北京人的“形式主义”。
强调声音形象,强调可听性,腔调的音乐性,强调细腻的听觉效应,略见极端而又有谐趣的例子即上文刚刚说到的叫卖。清人笔记中的有关记述颇能令人发噱:“京师荷担卖物者,每曼声婉转动人听闻,有发语数十字而不知其卖何物者。”(阙名《燕京杂记》第120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呼卖物者,高唱入云,旁观唤买,殊不听闻,惟以掌虚覆其耳无不闻者。”(同上)以俗见这真乃本末倒置,陶醉于声音艺术而略失“卖物”的宗旨了。
因“良可听也”,风味十足,故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有“叫卖大合唱”,传统相声有《卖布头》等。《四世同堂》写中秋前后北平的果贩“精心的把摊子摆好,而后用清脆的嗓音唱出有腔调的‘果赞’:‘唉——一毛钱儿来耶,你就一堆我的小白梨儿,皮儿又嫩,水儿又甜,没有一个虫眼儿,我的小嫩白梨儿耶!’歌声在香气中颤动,给苹果葡萄的静丽配上音乐,使人们的脚步放慢,听着看着嗅着北平之秋的美丽。”这种艺术并未全然失传,而且由当代作家接续着搜集到了:“……最动人的,并不是这些国营商店也许有、但摆得不那么显眼的货,而是叫卖声。最新、最时髦的发声方式,是这个城市的年轻人划拳时不知怎么就改了风味的,从酒桌旁边、胡同墙根底下来的腔儿。这发音吐字,讲究底气足,却又不张嘴,气憋在软腭和喉头之间,于是,字与字之间象是加了符号,长短不一,表面上有点儿懒洋洋的,实际上更透出一股子经蹬又经拽、经洗又经晒的韧性来。满街就听这一种吐字发声带着运气的叫卖了:‘嘿!瞧一瞧呐看一看,宝贝牌儿皮鞋,小宝贝牌儿小皮鞋,一对夫妻一个孩儿,小宝贝牌儿小皮鞋嘞!’……”(《封片连》)
老式叫卖讲求韵味,音乐性,以曲折婉转动人听闻,新式叫卖更炫耀“说”的技巧。背后的文化虽不尽同,注重声音效果则一,为此不惜把简单的行为复杂化了。说得唱得花哨,诸多点缀、装饰,未必全为实用;或许也在自娱:竞争中仍有一份闲逸神情。这里又有功利中的非功利。商业活动自然可以使用广义的“艺术”,如“商业艺术”、“经营艺术”,但在上述情况下,“艺术”像是更在其本来意义上。
对声音因素的偏重相对削弱了达意功能,却又强调了汉语本有的会意性——不全借助词义分析,也借助于声音感觉去领悟意义。北京方言尤其新方言有时近于单纯的声音符号。你可由声音会意,却难由语词读出明确语义。这种语言要求相应的语言场,如同舞台艺术一样依赖于现场反应、交流,因而有其限制,却也就有利于保存话语的主动性。焉知语义的非确定性不也会使话语扩张意蕴呢。
这是一种渊源古老的声音文化,听觉文化,其中存储有人类文明发展中失落了的一些东西。30年代瞿秋白批评“五四”以后创作中通用的“新式白话”,说“各国人都说读报,中国人却说看报。中国文言的文字,无论文体怎样变化,都是只能用眼睛,而不能用耳朵的”。至于“新式白话”,“仍旧是只能够用眼睛看,而不能够用耳朵听的。他怎么能够成为‘文学的国语’呢?”(着重号系原文所有)〔55〕对语言的听觉效应、声音形象的忽视,是文明民族的共同性现象。我们承受的是语言文化演进的一般结果。〔56〕
人类幼年时期曾经有过极其发达的有声语言,其声音的功用足以使高度文明的现代人惊奇与惭愧。“魏斯脱曼(D。Westemaun)说,埃维人(Ewe)各部族的语言非常富有借助直接的声音说明所获得的印象的手段。这种丰富性来源于土人们的这样一种几乎是不可克制的倾向,即摹仿他们所闻所见的一切,总之,摹仿他们所感知的一切,借助一个或一些声音来描写这一切,首先是描写动作。但是,对于声音、气味、味觉和触觉印象,也有这样的声音图画的摹仿或声音再现。某些声音图画与色彩、丰满、程度、悲伤、安宁等等的表现结合着。毫无疑问,真正的词(名词、动词、形容词)当中的许多词都是来源于这些声音图画的。实在说来,它们不是形声词;它们多半是描写性的声音手势。”〔57〕这是付出了极大代价才获得的人类能力,其得而复失也应是文明总体进步中局部退化(或曰“失落”)的例子。
书面语势力的扩张使得即使在“说”的场合,人们也不再分心留意语音、腔调。那种渊源极古老的文化却以残余形态留在了俗众的口头语言里。北京话不是惟一的注重声音形象的方言,却也称得上其声音形象最为文学艺术所珍视的方言。在这一方面,即使不是最有魅力的,也是最得天独厚的。
对于话语的声音形象的敏感也要有余裕才能造成。最理想的仍然是京味小说作者所格外垂青的老北京人闲聊的场合。“在闲聊中,言语仅限于它的交流感情的功能,失去了它的语义效能的参照功能:人们为说话而说话,象交换东西(财物、女人)那样交换词句而不交换思想。”〔58〕《离婚》写李太太与丁二爷间的闲聊:
“天可真冷!”她说。
“够瞧的!滴水成冰!年底下,正冷的时候!”他加了些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