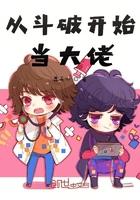奇书网>青山净化取得车间用空气净化专利 > 509收账(第1页)
509收账(第1页)
银杏苑里安安静静。
陈迹坐在石桌旁默默思索,手指在桌面一下一下敲击着,谁也不敢打断他的思绪。
小满有些不解,明明天宝阁和鼓腹楼才是最赚钱的营生,怎么公子偏偏对一个宝相书局来了兴致。
。。。
海风渐歇,船泊于岛岸。返程的航路并未因苏挽晴的归来而变得轻省,反而在归途中屡遇异象。每当夜深人静,船底便传来低沉的嗡鸣,像是地脉深处有谁在吟唱未完的誓词。陈砚命人在甲板布下忆灯阵,以共忆之光护持整艘船体,可那声音依旧穿透木板,渗入梦中。
念安开始做同一个梦。
她站在一片无边的灰原上,四野空茫,唯有中央立着一尊残破的石像??面容模糊,却穿着与苏挽晴相同的素白衣裙。石像脚下刻着三个字:“未名者”。每当她试图靠近,地面便裂开缝隙,涌出黑色雾气,化作无数张口无声呐喊的人脸。他们不悲不怒,只是凝望着她,眼中盛满一种近乎哀求的期待。
“你们想说什么?”她问。
风起,卷来一句断续的回音:“……记得我们。”
醒来时,窗外正掠过一道极光般的银线,横贯天际,转瞬即逝。小茉守在舱外,手里攥着贝壳项链,轻声哼着那首童谣。
“你也看见了?”念安披衣起身。
小茉点头:“每晚都见。它从海底来,往青山去。阿婆说,那是‘散魂引’,是那些没能被记住的名字,在寻找归途。”
念安心头一震。她忽然明白,《万灵录》虽已重光,忆灯遍野,可这世间仍有太多记忆未曾归位。清忆司三百年的遮蔽,不只是抹去几个名字、几段历史,而是让整整一代代人的存在被彻底蒸发。他们不曾被悼念,不曾被传述,甚至连死亡都没有碑文。
他们是真正的“未名者”。
归京之后,朝廷欲为苏挽晴举行国礼,封其为“共忆先师”,却被她婉拒。她在存真堂前立下一愿:“若真要敬我,不如替我找回那三十六个名字。”
众人不解。
她指向庙宇中碎裂的七块木牌:“你们以为那是我的封印?不,那是他们的墓碑。当年我以自身为锁镇信冢,亦将七位同道的记忆封入木牌,以防清忆司夺其魂魄、篡其意志。如今木牌碎裂,不是封印松动,而是他们在呼唤??该回家了。”
于是,“寻名计划”正式启动。
由念安牵头,联合各地忆师、史官、民间说书人,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追忆行动:凡能记起一个名字者,皆可在忆环广场点亮一盏白灯;若能讲述其生平片段,则加注青焰;若有实物遗物为证,如旧信、玉佩、兵牌等,则立碑于新筑的“归名园”中。
起初响应者寥寥。毕竟岁月太久,许多家庭连祖辈姓名都已遗忘。但随着苏挽晴亲授“共忆引法”??一种通过集体冥想唤醒潜藏记忆的仪式,越来越多沉睡的片段开始浮现。
一位老妇在梦中听见父亲哼唱战前小调,醒来后泪流满面,写下“沈文昭”三字;
一名铁匠翻出祖传刀鞘内层夹纸,发现一行血书:“吾名周允,死不负国”;
甚至有孩童在沙地上无意识画出人脸,经考据竟是百年前失踪的太学院女博士林照云……
三个月间,三千二百一十七个名字重现人间。
当第两千零二十四盏白灯亮起那夜,奇迹再度降临。所有灯火突然升腾,在空中交织成一座流动的星图,其形状竟与乌陵地宫最底层的“心渊祭坛”完全吻合。而在这星图中心,缓缓浮现出七个光点,正是那七块碎裂木牌所对应的方位。
苏挽晴闭目感应良久,睁开眼时,泪水滑落。
“他们还在。”她说,“灵魂未散,只待召引。”
于是,第二次南行启程。
此次队伍更为庞大,除原班人马外,还加入了七位自愿承担“承忆之躯”的青年忆师??他们将在仪式中短暂容纳亡者记忆,完成最后的对话与告别。小茉坚持随行,尽管年仅九岁,但她坚称:“我能听见他们的歌。”
再次抵达海岛时,无名庙宇已发生变化。原本静默的三十六块木牌中,有七块开始自行震动,表面裂纹中蓝光流转,仿佛内部藏着跳动的心脏。陈砚以古法测脉,发现这些木牌竟与海底宫殿的地脉频率同步,每一下波动,都对应着某种意识的呼吸。
按照《南溟志》记载,开启“归魂仪典”需满足三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