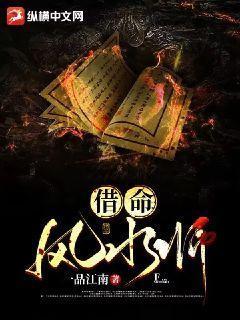奇书网>中西方古典史学比较 > 第一节 古代中国与西方历史理论概论06(第1页)
第一节 古代中国与西方历史理论概论06(第1页)
第一节古代中国与西方历史理论概论06
这种反宗教的立场也必定受到新兴起的基督教及其神学家的强烈反对。只是到了文艺复兴以后,他的原子论和伦理学才重新得到了重视。
3。柏拉图主义
新柏拉图主义是与晚期希腊哲学的三大学派(即斯多噶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怀疑论学派)相并行的另一条重要的思想脉络,其产生的时间比较晚,因此受到了上面三种学派不同程度的影响,新柏拉图主义的出现既是对晚期希腊—罗马哲学的一个全面的总结,同时也标志着古代哲学的终结,它从一产生就与基督教神学紧密结合,成为连接古代和中世纪哲学思想的一座桥梁。
新柏拉图主义的前驱是罗马时代的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斐洛(约公元前25—公元50年)。他的哲学思想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希腊的古典文明衰亡之后,希腊化时代的文化中心转移到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历史上第一次东西方文化在这里全面地碰撞和交融。这里的犹太人从很早开始就热衷于研究希腊哲学,并试图把它移植到犹太教的母体中去。斐洛正是这一全新尝试最成功的也是最重要的代表。作为一个犹太哲学家,他对希腊的语言、诗歌和哲学有着高度的热情和精深的修养,能够使用典雅的希腊文进行写作。他研读过古典时代大多数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并深受其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柏拉图。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提到了柏拉图的全部著作,也正是通过柏拉图,斐洛使希腊哲学和犹太宗教有机地结合起来,正如黑格尔言:“他特别擅长柏拉图的哲学,此外他更以引证犹太圣书并加以思辨的说明出名。他把犹太教的历史当作基础,加以注解。但是历史上的传说和叙述,在他眼里都失去了直接的现实意义,他甚至从字句里找出一种神秘的、寓言式的意义加到历史上去,在摩西身上他找到了柏拉图。”[214]关于斐洛和柏拉图之间的这种紧密的关系,古代的拉丁教父哲罗姆早就注意到了并且说得更为明确,他说:“或者是柏拉图斐洛化,或者是斐洛柏拉图化了。”[215]此外,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以及斯多噶学派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斐洛发生过直接的影响。
斐洛的一生用希腊文写了大量的著作,基本内容几乎都是《圣经·旧约》的《摩西五经》进行注释和解析,在这个过程中他所使用的“喻意解经法”最集中地体现了他在沟通犹太教神学和希腊哲学,宗教启示和哲学理性当中所作出的尝试和努力。应该说,用哲学的思维对神话或宗教进行解释并不是从斐洛开始的,在他以前,包括斯多噶派在内的希腊哲学就曾经这样做过,而且这种做法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受过教育的犹太人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斐洛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把这种方法推而广之,毫无拘束和更为系统地运用希腊的哲学理念解释犹太先知们的话语,把上帝看作是世间永恒不变的一种力量,其作用等同于渗透在万事万物中的、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作用的“逻各斯”,人也是上帝按照“逻各斯”或理性的样子造出来的,因此,在这个中心点上,斐洛找到了希腊哲学和犹太宗教的一致性,正是凭借这种方法,他用希腊哲学的理论来解释《圣经》,从而建立起他的宗教神学体系。归纳起来,斐洛的哲学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论证神的本性。在他看来,神是绝对没有任何属性的存在,因此不能用肯定的判断说他是什么,而只能用否定的宾语说他不是什么。但他还是试图对神进行论证。他认为神是“太一”或“一元”,是独一无二的、单纯的、自足的、永恒的存在,是万事万物的终极根据。
第二,神创造了世界。在这里,他把《旧约·创世纪》中的说法和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提出的创世说融通起来,提出是独一无二的神创造了独一无二的世界,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把世界的物质性基质的形成归因于上帝,上帝只是在凭借“逻各斯”的力量赋予这个世界以秩序的意义上创造了世界,与犹太宗教相比,这一思想显然更接近柏拉图的思想。
第三,人与神的关系。既然神是一种绝对没有任何属性的存在,那么人是如何认识他并与之发生关系呢,这是神学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难题。斐洛认为,人只能通过神秘的体验去关照神,靠近神,这是一种心灵的体验。他举例说,不能说圣徒看到了上帝,只能说上帝被圣徒看到了。因此,对神的认识不是凭借理性,而是凭借直觉和启示达到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柏拉图在“洞穴比喻”中的心灵关照本体的影子。的确,柏拉图的理念论对斐洛影响至深。如果说柏拉图的理念论有了与神接近的潜质的话,那么斐洛则把二者的距离大大拉近了,毫无含糊地把理念解释为神的思想,第一次提出理念就是神,从而把客观的理念改造为主观的神,以适应犹太教的需要。这一新的发展后来被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教父哲学继承下来。与此同时,希腊哲学,尤其是斯多噶学派中对“逻各斯”的解释也对斐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提出,“逻各斯”是上帝创造世界之前就已存在于心灵中的模型,是内在于神的,是神与人的中介,是赋予自然的规律,是人及其社会必须遵守的。这种思想同样也对基督教哲学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斐洛的学说无论在哲学思想史还是在宗教神学史上无疑都具有划时代的作用和影响。首先,他的关于“神—理念—逻各斯”的学说为新柏拉图主义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使他成为新柏拉图主义的先驱;其次,斐洛把犹太人的圣书变为希腊语读者可以接受的著作,把《旧约》中神秘的教义翻译成希腊哲学的语言,这些贡献与他的神学思想一起对基督教及其神学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总之,希腊和犹太这样两股伟大的思潮在斐洛那里得到了汇合。
比斐洛晚出的罗马帝国时代的哲学家普罗提诺(204—270年)是新柏拉图学派的奠基者。作为从希腊—罗马哲学向基督教神学过渡的重要环节,普罗提诺及其创立的新柏拉图学派在西方哲学思想发展史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据说普罗提诺出生在埃及,青年时曾经到亚历山大里亚学习哲学达11年之久,后来一度跟随罗马皇帝出征波斯,40岁以后定居罗马,直至去世。普罗提诺生活的时代正值罗马帝国正逐步陷入危机,贫富的分化,政局的动**,周边部族的入侵,奴隶的起义,剧烈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使得各种宗教迷信活动和神秘主义盛行起来,同时,希腊的理性主义思想则日渐黯淡。因此,如何使希腊哲学和异教崇拜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哲学,以对抗基督教,适应帝国的需要,成为普罗提诺哲学思想的背景和出发点。当时的亚历山大里亚是帝国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东西方各种古老的和新近出现的哲学和宗教流派和思想在这里相遇、交汇、交流和传播,这种氛围正好符合普罗提诺杂糅各家创立新说的目标,其中,至少有三种思潮为新柏拉图学派的创立产生了直接和重要的影响,它们是以斐洛为代表的犹太—亚历山大里亚哲学、新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早期基督教神学,此外,他十分重视学习和研究希腊哲学,希腊哲学对普罗提诺及其学派的影响是全面和深远的,其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斯多噶学派的影响尤为巨大。他继承了柏拉图—斯多噶学派的哲学理路,反对伊壁鸠鲁学派的唯物主义倾向,顺从罗马统治者的需求,创造出自己的神秘主义哲学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此前的古代哲学在普罗提诺及其开创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思想那里得到了全面的交融与汇合。
普罗提诺庞杂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即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其中,理论部分以对“三一原理”的阐发为核心内容。他的“三一原理”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其最初的思想渊源来自于巴门尼德和柏拉图对希腊哲学传统问题的认识。巴门尼德首先把真正意义上的存在同感觉区分开来,柏拉图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三类东西和三种领域的学说,普罗提诺把这一学说又经过改造成为自己的“三一原理”,即“太一”、“心智”和“灵魂”,三者的关系是由高到低,逐步下降的。
普罗提诺有时也把“太一”直接称为“神”或“善”,是一切理性认识的最终目的,是一切可感世界的终极本原,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因而等同于至善和神。实际上,他在这里所谓的“太一”也就相当于柏拉图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的作为质料因的第一推动者。他认为,从“太一”中最先流出来的是“心智”,是“太一”的第一个孩子,是第二原理。但由于“太一”是永恒的和不动的,所以这种“流出”并不是依靠运动和变化,而毋宁说“心智”是“太一”自身的一个部分,就像太阳和它的光芒那样,是一种“发出”。与“太一”不同的是,“心智”是多样性的开始,它也是永恒的,包括一切精神的存在,其原型是真正的理念中的善。与感觉和感觉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同,“心智”和心智活动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同一的,但它本身也是被产生出来的,因而不是最单纯的,只能位居“太一”之下。最后,“灵魂”是由心智派生出来的。“灵魂”处于无形的心智世界和有形的可感世界的中间,又分为高级和低级两个层次。“灵魂”内容更加多样,形式极为丰富,是杂多的统一体。正是由于“灵魂”位于心智世界和可感世界之间,所以它具有可知和可感的两重性。在灵魂和肉体的关系上,他认为物质是由灵魂创造出来的,物质没有独立的实在性,灵魂是不朽的和可以转世的。理性是灵魂特有的活动。
可见,“太一”、“心智”和“灵魂”实际上是一体的,“太一”是终极的原理,“心智”按照其本性处于永恒的活动中,“心智”又赋予“灵魂”以思想的力量,“灵魂”围绕着“心智”活动。这样,三者就构成了一个由高到低、由里到外的同心圆的结构,由形相世界一层层地向可感世界流溢、发散。
如果说普罗提诺的理论部分是用从上向下,从里到外的顺序进行阐发的话,那么在实践部分则完全相反,是一个超越、上升和使自己的灵魂不断得到净化的过程。这是通过一系列道德实践活动来完成的,最终的目标就是达到与神同一。上升之路有两条:第一是伦理道德,第二是辩证法。
普罗提诺认为美德有两种,一种是公民的美德,正是这种美德把公民们联系起来,使他们过一种合乎准则的生活,第二种是净化的美德,这种美德可以帮助灵魂摒弃外界的污染,向神圣的心智上升,因此,灵魂要极力摆脱肉体的束缚和干扰,只要求满足基本的自然需要即可。此外还有一种美德对前两者起到统摄作用,那就是对神的爱,这是灵魂逐渐上升回到太一的阶梯。这就需要人抛弃尘世的现实生活,追求灵魂的纯洁,最终达到与神的结合。这样一种灵魂解脱说必然走向宗教神秘主义。除了这些道德实践活动,辩证法也是使灵魂回到太一的重要途径。他认为,辩证法是哲学中最具有教育意义的部分,是灵魂直接把握真理的唯一途径,因而不论是对理论还是实践活动都具有指导意义,其最高的目标就是认识真正的存在,即“太一”(神),这样,辩证法与神学在普罗提诺那里也统一起来,成为其神学目的论的工具。
总之,如果说在普罗提诺以前已经出现了新柏拉图主义的一些理论萌芽的话,那么是普罗提诺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学派。从新柏拉图学派创立,到公元529年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宣布关闭雅典所有的学派而告终结,前后大约持续了三个世纪左右。该学派从唯心主义的立场概括了自希腊哲学产生以来八百年的思辨过程,它既是古代哲学的终结篇,也标志着古典思想已经被融合进基督教神学,并被后者继承,从而在此后的一千年中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发挥作用。
[1]关于武王伐纣的确切年代,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议,此处采用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所订年表中给出的定年。
[2]王充:《论衡·正说篇》。
[3]许慎:《说文解字》书部:“书,著也。”段玉裁注引《叙目》曰:“著于竹帛谓之书。”详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页下。
[4]先秦儒家以颂《诗》、《书》,习礼、乐闻名。《论语》、《孟子》、《荀子》中引用《诗》、《书》之处甚多。《史记·孔子世家》即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墨家承认《诗》、《书》的权威性,《墨子》一书多引《诗》、《书》。
[5]《荀子》称“书”为“经”。秦始皇能禁《诗》、《书》,应是因为其时《诗》、《书》的篇目已较确定。
[6]周原甲骨卜辞的发现,似可说明这一点。
[7]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将殷人的宗教总结为“祖先—元神”——“先祖=上帝”。详见该著第1卷第3章《殷代的宗教思想》,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7—70页。
[8]《尚书·大诰》。
[9]从张守节《正义》说,见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34页。
[10]《尚书·多士》。
[11]《尚书·康诰》。
[12]《左传》僖公五年记虞大夫宫之奇引《周书》。
[13]参见斯维至:《说德》,《人文杂志》1982年第2期。
[14]《尚书·无逸》。
[15]《尚书·酒诰》。
[16]《尚书·多方》篇曰:“有夏诞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昏,不克终日劝于帝之迪,乃尔攸闻。厥图帝之命,不克开于民之丽,乃大降罚,崇乱有夏。因甲于内乱,不克灵承于旅;罔丕惟进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钦,劓割夏邑。于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纯,乃惟以尔多方之义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为,大不克开。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
[17]《尚书·康诰》。
[18]《尚书·酒诰》。
[19]《尚书》、《诗经》中,多次提到“天”之“监”,如《诗·大雅·文王》篇“天监在下”,《诗·周颂·敬之》“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
[20]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