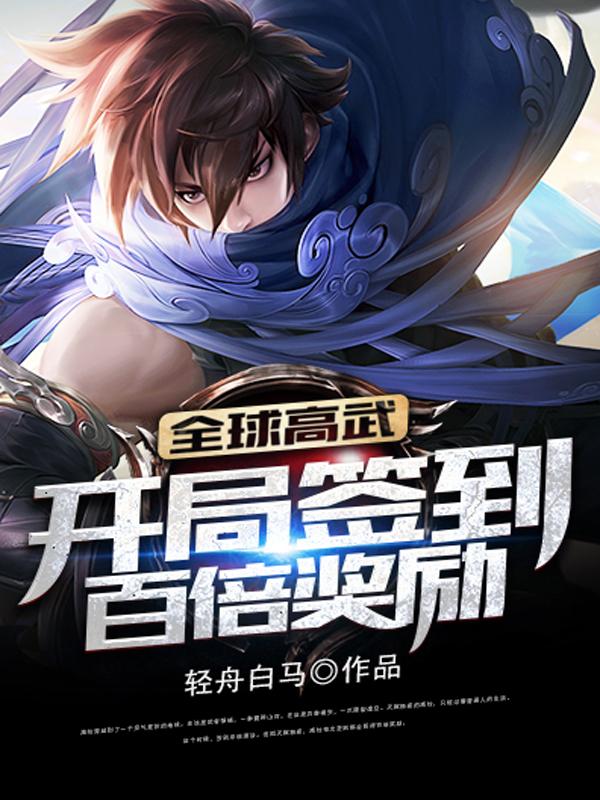奇书网>中西史学差异 > 第二节 专论03(第4页)
第二节 专论03(第4页)
关于庄子的道,请看下面两段话: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狶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235]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正获之问于监市履狶也,每下愈况,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236]
两段虽都用譬喻,但其中的道所指不同,则是显而易见的。按前面那段话,道指万物的本原,而不是万物本身,因此与物是不同的,得到这样的道,或可以长生,或可以成仙,或可以为政。可是按后面那段话,道却指万物本身,而不是万物的本原,得到这样的道,未必能够成为超人。可以说,前者有本原性的意义;而后者则有普遍性的意义。至少在万物有没有本原、道与物是否相同这两点上,《庄子》关于道的论述是有矛盾的,这在《庄子》中还有许多例证,[237]看来并非偶然。
《韩非子》中有很多关于道的论述,以下几段颇有代表性:
夫道者弘大而无形,德者核理而普至。至于群生,斟酌用之,万物皆盛,而不与其宁。道者下周于事,因稽而命,与时生死,参名异事,通一同情,故曰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衡不同于轻重,绳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湿,君不同于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239]
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无常操,是以死生气禀焉,万智斟酌焉,万事废兴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时得之以御其变气,轩辕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与天地统,圣人得之以成文章。道与尧舜俱智,与接舆俱狂,与桀纣俱灭,与汤武俱昌。以为近乎,游于四极;以为远乎,常在吾侧;以为暗乎,其光昭昭;以为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内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随时,与理相应,万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万事得之以败,得之以成。道譬诸若水,溺者多饮之即死,渴者适饮之即生;譬之若剑戟,愚人以行忿则祸生,圣人以诛暴则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败,得之以成。[240]
大体说来,前两段中的道指始,与物不同,有本原性的特征;而后面一段中的道,由于有理的中介,而与物同一,有普遍性的特征。概括起来,老子的道主要是本原性的;庄子的道既有本原性的特征,又有普遍性特征;韩非子的道既有本原性的特征,又有普遍性特征。为什么这三个思想体系的道论有如此的不同?这种不同与它们各自的历史理性有什么关系?以下试做分析。
这里所谓的本原,取其中文词义。从造字本义上说,本乃指事,指树木之根;原乃会意,谓岩下泉水,乃江河源头。从经验上说,树根不同于树干,泉源不同于江河,是理所当然的。如果道是以本原这个方式存在的,那么,只有事物的本原才是合乎道的,事物本身就不是合乎道的;把这个道理应用在历史上,就可以说,只有历史的原初状态是合乎道的,而后来的发展形态却是不合乎道的;“小国寡民”和“至德之世”是合乎道的,而后来的历史发展却是不合乎道的。这是老庄历史观的重要内容。
不论中文“普遍”二字,还是英文universal(源于拉丁文),都指全部,指无所不在,本文所谓普遍性,即是这个意思。根据这种理解,如果说道是普遍存在的,或者说,道不脱离事物,就在事物之中,那么,天下就没有不合乎道的物了;把这个道理应用到历史上,就可以说,道贯穿历史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全部历史都是合乎道的;因此,“安之若命”、“世异则事异,世异则备变”的历史观就有了着落。这是庄子历史观的另一方面内容,更是法家历史观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庄子历史观隐藏着深刻的矛盾;[241]而老子、特别是法家的历史观,却显得明确而单纯些。
不过,这里面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第一,韩非的历史观是建立在道的普遍性基础上的,他关于道的本原论是否还起作用呢?前面说过,法家历史观中承袭了道家历史倒退论的某些因素,在他们的历史观中,原初阶段与后来的历史进步是有一定差异的,但是,法家关于道的本原论主要是为以力为德的政治观和君臣不同道的统治术服务的,这在《主道》(“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扬权》(“道不同于万物”,“明君贵独道之容”)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道的本原性并非只为历史观服务的。
第二,与以上问题有关,道的本原论和普遍论是有矛盾之处的,为什么还会在同一思想体系中并存?这个问题我已思考过若干年[244],至今没有在理论上找到更稳妥的解释。我的看法是,这是由思想家现实目的的多元化决定的。本原性的道,可为不同于普通大众的生存或行为方式提供理论支持,有一定神秘性,除了倒退论的历史观,养生、成仙、驭臣所遵循的道术,都可从中得到启迪,这在《老子》、《庄子》、《韩非子》书中不难找到证据。而普遍性的道,只能为纯粹历史理性和现实的生存或行为方式提供理论支持,就历史观而言,不管态度如何,《庄子》、《韩非子》都承认历史进步,这与它们都承认道的普遍性是吻合的。庄子为什么一方面要回到“至德之世”,另一方面又表示要“安之若命”?我以为,前者表示他对历史进步的否定和批判,后者表示他对历史进步的无奈和顺从,这是他的实际处境和心态的写照,没有什么神秘的。社会转变时期,总有许多持此种矛盾心态的人。至于韩非的道论,为什么会在高倡普遍性的同时,又对神秘的本原性有所保留?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为了顺应时代需要,推进法治改革,自然要把握历史进步的客观规律;为了加强集权,在“上下一日百战”的激烈斗争中,更有效地驾驭臣下,同样需要冷静地分析客观形势,掌握切实可行的统治方法。这是他强调理性思考,重视普遍性的现实动机。可是作为君主的统治术,是不能公开的,它的实施,必然是神出鬼没、与众不同的,这样不同寻常的道术,当然也需要找到一个不同寻常的生命依托,这就是韩非之所以对本原性有所保留的现实根源。可是,韩非自以为神秘的本原,在我们眼里,依然逃不脱普遍性的“天网”,没有什么神秘的。
六、五德终始说与历史正统观
(一)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五德终始说宣扬五种自然力量依某种规则循环运转,这种对自然的关注,与希腊早期自然哲学有一定的相近之处。如果可以把这种观点纳入自然理性的范畴,那么,这种自然理性具有怎样的特点呢?
深入一步,又会发现,五德终始说之重视自然力量,是为了说明历史变动的规律,它不但与中国古代历史理性有着许多一致之处,而且就在历史理性发生的潮流中诞生。作为一种历史观,它又具有怎样的特点?在理性主义历史观兴起的潮流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再深入一步,还会发现,五德终始说具有为某种现实的政治统治提供合法依据的更为直接的功能,也就是说,它实质上是关于统治的合法性的学说,是一种正统观,运用这种观点看待历史,那就是历史正统观。这是五德终始说的根本所在。要想真正了解五德终始说,必须把握住这个根本;要想回答前面几个问题,同样必须把握住这个根本。
本文首先对正统概念的内涵进行考证,然后抓住正统观这个根本,对五德终始说作历史的考察,对上面几个问题试作回答,不妥之处,尚祈指正。
(二)“正统”概念的定义
历史正统观是五德终始说的根本。可是,就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却存在着分歧,归纳起来,大概有三种看法。一派以宋代欧阳修为代表,认为:正统之论“始于《春秋》之作”[245]。当代研究历史正统观最有成就的饶宗颐教授赞成此说。[246]按照这个时间,五德终始说应该属于古代正统论的内容。一派以清儒顾炎武为代表,认为:“正统之论,始于习凿齿,不过帝汉而伪魏吴二国耳。”[247]一派系今人孙家洲先生的观点,认为正统思想形成于汉代。[248]按照后两种观点,五德终始说就不在正统论的范畴。
为什么会有分歧?我以为对概念的内涵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应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了使研究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必须对“正统”概念作出准确定义。
何谓“正统”?从宋代开始,学者们作了许多的讨论,但大多是从当时的政治需要出发来界定的,至于训诂上的研究,迄今尚未见到。
关于“正”。《说文解字》二篇下正部:“正,是也。”“是,直也。从日正。”[249]十二篇下乚部:“直,正见也。”段注:“《左传》曰:‘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引申之义也。见之审则必能矫其枉,故曰正曲为直。”[250]可见,汉人认为“正”就是正直,与“曲”即不正相反对。古今意义相当。《易传》:“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王弼注:“正位不可以假人。”孔颖达疏:“‘正位者’,释‘王居无咎’之义,以九五是王之正位,若非王居之,则有咎矣。”[251]《礼记·文王世子》:“正君臣之位。”[252]可见,“正”字很早就与君主和王朝统治有关,表示最高权力的合法性。
《汉书》注引李奇、张楫:“统,绪也。”[254]《文选·甘泉赋》“拓迹开统”注引李奇曰:“统,绪也。”[255]《说文解字》“绪,丝耑也。”段注:“耑者,艸木初生之题也,因为凡首之称,抽丝者得绪而可引。引申之,凡事皆有绪可缵。”[256]《方言》:“纪,绪也……或曰端”[257]。
《文选·笙赋》“统大魁以为笙”。李善注:“總,统也。”[258]《荀子·议兵》:“功名之總也”[259],《韩诗外传》四“總”作“统”[260]。《汉书·兒宽传》“统楫群元”注引臣瓒曰:“统犹總览也。”[261]《说文解字》“總,聚束也。”段注:“谓聚而缚之也。總有散意,糸以束之,礼经之總,束发也;禹贡之總,禾束也。引申之为凡兼综之称。”[262]
根据以上资料,可知,“统”可训“纪”,“纪”通“绪”,为丝之端,即头绪,是“统”为本、为元、为始、为端;此外,“纪”为丝之别,指众丝之头绪,统通纪,但不强调别,因而含有综括众丝之头绪,即聚束、揔揽和兼综之义。所谓“统天”即本于天,所谓“大一统”,即重视(大)统(众纪)的集中(一)。公羊学家认为,《春秋》书“王正月”,就是为了在每岁开始之时,突出诸侯历法始于王、总于王的意思。“统”的这种解释强调空间上的延展或兼综。
不过,“统”既然为始,为端,当然也可用为时间上的“起源”和“始于”的意思,用作动词,就有追溯源头、反本寻根之义。[263]凡物皆有“统”,此物之“统”乃承接他物而来,是“统”又隐含着“接续”或“承接”之义。《汉书·贾山传》注引如淳曰:“统,继也。”[264]《说文》段注:“虞翻注《易》曰:‘继,统也。’”[265]是“统”可训“继”。按“继”,左边是一个“糸”字,右边是古文“继”字,左右翻转,就是断绝的“绝”字(其实,在古代,这两种写法都兼含继绝二义,训诂学家有称之为“反训”的),《说文》:“(绝之古文)象不连体,绝二丝。”《说文》:“继,续也。”“续,连也”。可见,“继”字内部兼有断、连两义,是个会意字,可作“连接断裂”解释[266]。“统”的这种解释更强调时间中的延续,有克服断裂而后继续的意思,当然,也有空间的接续之义。
又班固《典引》云:(高祖、光武之龙兴)“盖以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蓄炎上之烈精。”[268]根据李善注,可知,这里所谓的正统是说汉承周后,为火德,像唐尧克让一样,归运谓尧归运于汉。这里的正统即是指承继,而承继必在时间延续中进行,这个解释强调时间上的承接,符合“统”字的第二种含义。
这两种解释在汉代及以后的学术发展中有没有形成传统呢?回答仍然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