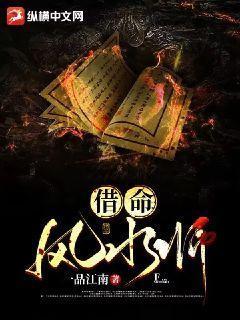奇书网>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综述 > 第一节 古代中国与西方历史理论概论04(第1页)
第一节 古代中国与西方历史理论概论04(第1页)
第一节古代中国与西方历史理论概论04
从时间上看,毕达哥拉斯学派最早产生在公元前6世纪的意大利,其创始人是萨摩斯岛的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71—约前497年),从时间上看,正处于米利都学派和赫拉克利特之间。虽然受到过米利都学派的影响,但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些与爱奥尼亚传统不同的特色。与米利都学派不同,毕达哥拉斯盟会首先是一个宗教团体,信奉灵魂不朽、轮回转世的学说,恪守一套严格而古怪的教规。在哲学上,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将抽象的“数”作为万物的本原,认为世界万物的存在都可以由一定的数量关系而得到根本性的解释。这样一种不可感知、没有形体、不能运动的“数”比米利都学派提出的水、气等元素更具有本质的特征。如果说米利都学派所说的本原本身是运动变化的,只不过它们都来源于并回归于某种不变的元素,那么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的作为世界本原的“数”从本身来讲就是不变的,成为一种可以与一般的具体事物相分离并且高于一般事物的独立的存在,这一从有形向无形、从物质向精神(思维)、由运动变化中的不变到静止的不变的转化代表了不同于爱奥尼亚哲学传统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启发了后来的爱利亚学派和柏拉图哲学,从而向希腊哲学中不变的“本体”概念又迈进了一大步。黑格尔对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希腊哲学史上的这种承上启下的作用作出了精辟的阐述:
我们在将宇宙解释为数的尝试里,发现了到形而上学的第一步。毕达哥拉斯在哲学史上,人人都知道,站在伊奥尼亚哲学家和爱利亚学派哲学家之间。前者,有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仍然停留在认事物的本质为物质的学说里,而后者,特别是巴曼尼得斯,则已进展到以“存在”为“形式”的纯思阶段,所以正是毕达哥拉斯哲学的原则,在感官事物与超感官事物之间,仿佛构成一座桥梁。[195]
继米利都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之后,仍然属于爱奥尼亚哲学传统但也吸收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约前475年)使希腊哲学,尤其是辩证法思想得到了巨大的推进。赫拉克利特以文风晦涩而著称,喜欢使用模糊的隐喻方式表达他的思想。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之所以难于理解,除了文字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深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当时一般哲学家的水平,超出了当时的文字所能够表达的思想的限度。
从总的情况来看,赫拉克利特还是继承了米利都学派开创的爱奥尼亚哲学传统。从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大多数哲学家都把赫拉克利特与米利都学派相提并论,他所提出的火是万物的本原的学说是早期自然哲学寻求万物的物质本原的继续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赫拉克利特还是与早期的自然哲学家存在很大的差异,有着自己独特的创造和发展。有学者认为,他所提出的永恒变化中的世界常驻不变的“逻各斯”、对立面的结合与分离促成了发展等思想还是受到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深刻影响。[196]
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万物的本原,这个观点见其著名的残篇:
这个世界的一切存在物都是同一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按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197]
在这段话中,他所强调的万物的运动变化和对神创造世界的否定无疑集中地体现了米利都学派的唯物论传统,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为什么选择火作为万物的本原,是因为与水、土等元素相比,火更加活跃,更富于运动和变化,更为重要的是,火并不是一种实体,它必须借助于一种实体才能存在。也就是说,水、土是物质,而火却是物质的运动状态。对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就已经有了明晰的说明,他指出,火是最接近没有形体的东西,而且,火不但自身是运动的,而且又是能使别的事物运动,火不但是运动,而且又是运动的原因。[198]所以火的这一特性使之区别于和高于水、土等物质性的实体,因而更加深刻和抽象。
赫拉克利特认为,既然火是万物的本原,那么火和万物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但是,在火、土、水和气之间到底如何转换,却存在不同的说法和不能自圆其说的困难。这就要说到上面这段话的第二层重要的含义,那就是虽然世界(火)的本质特征是永恒的运动,但其燃烧和熄灭也必须按照一定的尺度(必然的逻各斯)进行,后者则是不变的,以一定的数量关系表现为宇宙的秩序(os),这一点不能不说是受到了早期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深刻影响。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赫拉克利特的另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所以它分散又团聚,接近又分离。[199]
毫无疑问,赫拉克利特在这里首先表述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那就是万物的不断变化。由此推演到人的生命,那就是我们又生又死,既存在又不存在。本来,在赫拉克利特的这一命题中既没有否认运动中的相对静止,更没有贬低运动中的世界(即感观世界)的意思。因为“同一个人”和“同一条河流”正是体现了运动中的相对静止,但是,在赫拉克利特第一次对动与静(即变与不变)作出了深刻的哲学解释之后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引申,透过这个问题的不同认识,希腊哲学中的不变的“存在”或“本体”概念逐渐凸现出来。
对于赫拉克利特的命题,克拉底鲁首先做出了极端的推演,认为人即使踏进同一条河流也是不可能的,正因为世界万物的运动是如此的瞬息万变,不可把握,所以“人根本不能说什么,而只能简单地动动他的手指”,因为在你说它的时候,它已经不是原来的它了。这种夸大运动的绝对性的说法只能导致不可知论,也是一种形式的形而上学。与克拉底鲁相反,爱利亚学派则根本否认运动变化,这样才有“飞矢不动”之说。这两种推演虽然方向相反,但性质相同,都违背了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思想,倒向形而上学。但是这些争论对后来的哲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克拉底鲁用巴门尼德的思想对赫拉克利特的学说进行了引申,认为通过一切可以感觉到的事物是不能产生真正的知识的,而柏拉图正是通过克拉底鲁了解到赫拉克利特的学说,并接受了克拉底鲁的思想,认为现实的具体世界是变动不居的,对它只能有感觉,不能有知识,知识只能来自于另外一个世界,即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
赫拉克利特的命题的第二层含义就是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是按照一定的尺度和规律进行的,这就是“逻各斯”,具体的讲,逻各斯表现为事物内部两种相反力量的对立统一。对立的双方以对方的存在为条件,这种对立中的统一性就是“和谐”,也就是中国哲学中所讲的“和而不同”,即有差别的统一。在这一点上,赫拉克利特显然受到了早期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但二者在倾向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应该说,赫拉克利特继承并发展了毕达哥拉斯的对立思想,从而创立了完备的对立统一学说。例如,与毕达哥拉斯更重视对立面的和谐不同,赫拉克利特更强调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如果说毕达哥拉斯看待万物的落脚点是静止的话,那么赫拉克利特则坚信永恒的运动变化是万物产生的根源,这正体现了意大利哲学与爱奥尼亚哲学的不同特点。
最后,赫拉克利特还被认为是第一个提出认识论问题的哲学家,他最早提出了感觉是否可靠的问题。虽然深刻地看到了万物运动变化背后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逻各斯,但赫拉克利特还并没有把感觉(经验)和理性分开,所以不可能得出理性高于经验的认识。将这两者完全分开,进而得出重视理性、蔑视经验的说法,最早是从巴门尼德才开始的,柏拉图接纳过来并进行了更为系统的阐发,最终使这种理论成为希腊哲学的主流。
3。原子论者
赫拉克利特之后,希腊哲学发展的两支——爱奥尼亚哲学和意大利哲学——又出现了新的发展。
先说意大利哲学。继毕达哥拉斯之后,在南部意大利的爱利亚城邦形成了一个新的哲学学派,即著名的“爱利亚学派”,其代表人物包括塞诺芬尼、巴门尼德、芝诺和麦里梭,其中,巴门尼德又是爱利亚学派最重要的哲学家。从总的倾向上看,爱利亚学派对爱奥尼亚哲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提出了一个永恒不变的“存在”概念,将早期希腊的自然哲学引向本体论,对古希腊哲学的走向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下面我们就结合“存在”概念的形成过程看一看爱利亚学派的主要哲学观点。
塞诺芬尼(约公元前580—约前485年)首先提出了万物是“一”的说法,亚里士多德注意到,他所提出的这个“一”是与泰勒斯自然哲学家等人提出的作为万物质料的“一”是不同的,因为后者是运动的,万物从中产生,最后复归于它,但塞诺芬尼提出的“一”却是不变的,所以无所谓生灭。而且,出于对早期希腊神话中拟人化的多神论的反对,塞诺芬尼提出“神是一”的观点,这个神不再具有人的形体和思想,是无生无灭的,不动的和唯一的,这个神不仅成为巴门尼德的不变的“存在”的来源,也是后来柏拉图提出的“创造者”、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力”乃至基督教时代的宗教哲学的理论起点。
虽然塞诺芬尼是第一个说出“一”的,但他没有做出清楚的说明。后来,他的学生巴门尼德(约公元前540—?)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这个“一”就是“存在”。在早期希腊哲学发展中,巴门尼德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与此前的所有哲学家(包括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和赫拉克利特等)不同,巴门尼德不再将哲学思考的主题停留在万物的本原是什么和万物如何生灭的问题上,因为他认为人们从变动不居的世界是得不到永恒不变的真理的,就像赫拉克利特讲的,它们既存在又不存在,只能得到凡人的意见,因此,哲学研究的任务应该是寻求更高一级的真理,那就是唯一的、真实的和不变的“存在”。
请看巴门尼德的残篇中关于“存在”问题的两个著名的命题:
存在物是存在的,是不可能不存在的……存在物是不存在的,非存在必然存在。[200]
虽然关于这两个命题在翻译和文意上还存在很多争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巴门尼德所谓的存在物是不生不灭的、唯一的、不动的和完整的(即不可再分的),这与爱奥尼亚哲学将世界看作是运动变化的截然不同,毕达哥拉斯学派虽然看到了数的不变性,但没有还是否认世界是运动变化的。巴门尼德提出的这个真实的“存在”则第一次将运动和静止、变与不变完全对立起来。一方面,巴门尼德的“存在”说陷入了形而上学,且并不完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他在古希腊早期哲学发展中所起到的不可或缺的转型作用,因为正是这一次运动和静止的完全割裂使人们认识到通过感觉和观察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得到的知识是不真实的,只有用理性的思想去把握变动背后的不变的存在才能够得到真理,也就是说只有“存在”才是能够用思想来认识和表述的,“非存在”则不能,只能用感观感知。
在希腊文中,表示“存在”的eimi本来就是一个联系动词,即汉语中的“是”,后来演变成为巴门尼德的“存在”,这表明,思想的唯一对象就是存在,与此相反,感觉的对象则只能是非存在。只有存在是可以表述的,可以形成“真理”(aletheia),非存在是不能进行表述的,只能形成“意见”(doxa),因为在你说“某物是什么”的时候,这个事物已经变化了,而且也因人而异。从巴门尼德开始将“真理”和“意见”作为一对对立的范畴,将前者放在光明的世界,后者则置于黑暗的居所。
巴门尼德的这样一种“存在”表面上解决了无中为什么能够生有的问题,也排除了万物发展中的所有不确定因素和内部的矛盾性,只留下一个最普遍、最抽象、最纯粹的哲学范畴“存在”,应该说,这是从早期爱奥尼亚哲学家提出的一般性物质元素、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抽象的“数”的进一步抽象化和发展,在巴门尼德之后,希腊哲学进入到一个更深更广的领域,一般与个别、静止和运动、物质和精神、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成为哲学家们必须面对的普遍问题。
当爱利亚学派正在阐发他们的唯心主义“存在论”的时候,希腊哲学的另一种用某种物质性元素解释万物本原的自然哲学传统也没有中断。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哲学家恩培多克勒(约公元前483—约前435年)对早期的爱奥尼亚哲学进行了新的综合和发展,提出了世界是由水、火、气、土四种元素的结合和分解而形成,即著名的“四根说”。这一说法是对巴门尼德的抽象而空泛的“存在”的有力回应,打开了人类认识物质结构的大门,代表了探索自然物质的新水平,并为后来原子论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前提。
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随着经济繁荣、国力日盛的希腊城邦雅典逐渐成为新的文化中心,希腊哲学研究的中心也开始逐渐转移到希腊本土。在这个过程中,阿那克萨戈拉(约公元前500—约前428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生活在雅典的第一代启蒙哲学家,他首先将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带到希腊本土,提出了别具一格的物质结构说——“种子论”,从而为原子论的形成铺平了道路,同时提出了作为独立的精神本原的“努斯”,因而在希腊哲学中首次提出了一种二元论倾向的哲学,使存在和思维的对立进一步明朗化。在这个意义上,阿那克萨戈拉成为一个承上启下的哲学家,使早期希腊哲学的两种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碰撞和融合,也为下一个以德谟克利特及其原子论和柏拉图的理念论为代表的古希腊唯物论和唯心论哲学的“双峰”的建造提供了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
古希腊哲学从泰勒斯开始,经过了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到了公元前5世纪末和4世纪初,随着古典城邦文明进入盛期,希腊哲学也正在走向成熟和辉煌。在这当中,留基伯开创、德谟克利特建立的原子论哲学是希腊早期自然哲学的大综合和巅峰之作,是爱奥尼亚哲学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大变革,是人类认识自然世界的历史上又一次巨大的飞跃。
爱利亚学派把一和多、运动和静止完全割裂开来,因而陷入了不可自拔的矛盾之中,原子论的提出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与爱利亚学派只承认“存在”的存在,否认“非存在”的存在不同,他们认为,不但“存在”存在,“非存在”也是存在的,那就是“虚空”,充实的存在就是原子,原子既是不变的“一”,同时原子在虚空中运动,就成为“多”,无数原子在虚空中的结合和分离就成为万物的生灭、运动和变化。这样,一与多,运动和静止、本质和现象再次被有机地统一起来,爱利亚学派面对的难题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