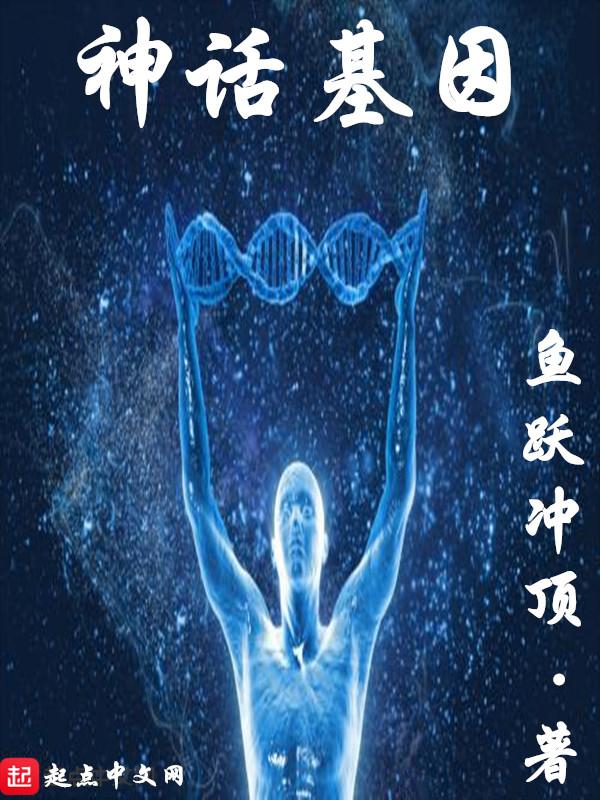奇书网>病美人崽崽三岁半[快穿 > 5060(第28页)
5060(第28页)
“我讲没讲错。”严义陈述着,一如既往地作为一个旁观者,不关注已经溃不成军的苏鹤声的情绪,“他不愿意开口说话,几乎把所有伤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
“但苏鹤声,你跟他结婚不是一天两天了,头一次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吗?”
还有一句话严义没讲,可苏鹤声已然明白。
假使说这段婚姻里有什么变化,让他们走向如今的沼泽之地,那这个变化就是苏鹤声。
沈砚之姿自始至终都没变过,变的是他苏鹤声。
爱没变,但习惯渐渐改变。
可沈砚之尚且不能接受这样的改变,在身体和心理的重重高压下,他提出了离婚,以一种广而告之的方式,告知他苏鹤声一个事实——到了如今,沈砚之即便万般不舍,也不得不跟苏鹤声离婚。
严义说:“那天你前采回来,碰到我跟砚之在医院门口,我跟他说不然顺其自然地让你误会好了,说不定能顺利离婚。”
“他说你不会相信。”
“从最开始,我就知道你们离不了婚,他自始至终都觉得你很好,是他没被爱,即便知道自己得的罕见病,想的也是跟你一刀两断,以免徒增挂念。”
严义叹息:“苏鹤声,你真该好好反省。”
第59章第59章无微不至
实实在在的疼一场极其消耗精神和体力,但沈砚之再次醒来时,天已经很晚了,屋内很安静,沈砚之睁开眼,眨了眨。
“醒了吗?”
黑暗中,身边传出一道低哑的嗓音。
苏鹤声耳尖地听到被子摩挲声,悄然起身查看,便看见沈砚之正在眨眼睛,就这样悄无声息的,除了长长的睫毛,他一动不动。
沈砚之将手从被子里拿出来,揉了揉眼睛:“你怎么了?”
“什么?”苏鹤声疑惑,抬手将床边的可视小夜灯打开,小心查看沈砚之的状况。
沈砚之又眨了眨眼,微微歪头,看向苏鹤声:“你怎么了,感冒了?”
“……”
苏鹤声顿了一下,想到估计是自己有鼻音,嗓子也是哑的,所以叫他误会了。
可想到这儿又是一阵鼻酸,砚之刚醒,第一时间注意到的却是他的异样。
苏鹤声摇头:“没有,太久没说话了。”
他吸了下鼻子,问:“要起来吗?”
“…嗯。”沈砚之闭了闭眼。
虽然一觉醒来精神尚好,倦意和疼痛散了不少,但身上的酸乏依然存在,没有消失殆尽,持久地磨着沈砚之。
沈砚之被扶着坐起来,才小小的,长叹出一口气。
他朝窗户看了眼,窗帘是拉上的,苏鹤声注意到他的视线,去拉开了窗帘,外面的城市夜灯透过落地窗折射进来,黑漆漆的屋内亮了一些,月亮高挂,视野开阔。
沈砚之动了动身子,肚子上一翻身掉下来一个热水袋,伸出去的手立刻又被收回来,他摸了一下。
还是热的。
“我睡多久了?”
“二十五个小时。”苏鹤声答,语气轻快了一些。
沈砚之这一觉从昨晚睡到今天晚上,这二十五个小时,几乎每隔两三个小时,苏鹤声就会探一下他的鼻息,然后再向严义追问一遍,他睡这么久是不是正常的。
但他现在好像对“正常现象”几个字有点应激,尽管严义反复强调,沈砚之的睡眠是自我修复过程,但苏鹤声仍然坚持不懈地做探鼻息这个行为。
沈砚之转了转脑袋,脑袋不重,很轻松,但脖子酸的厉害,他瞥了眼苏鹤声,总觉得他奇怪的很,死死的盯着他,目光可怜兮兮的。
把人看的都不自在了。
“鹤声,给我揉一下。”沈砚之喊他,声音很轻,是飘到苏鹤声耳朵里的。
苏鹤声云里雾里,跪在他身边,力道适中的给他摁后颈,抚摸后背,像撸猫一样。
“还好吗?”
“嗯…”沈砚之上半身顺势贴在苏鹤声身上,轻轻呼吸,睫毛慢慢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