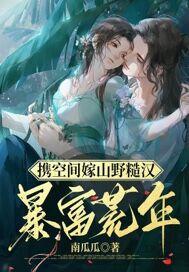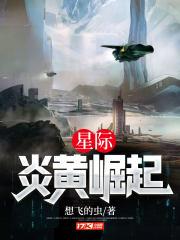奇书网>明末我崇祯摆烂怎么了?!txt > 第340章 祖大寿 你看那阿济格屁股又大又圆(第2页)
第340章 祖大寿 你看那阿济格屁股又大又圆(第2页)
陕西境内,李自成军中再度爆发激烈争执。李岩手持一份《京报》副本,激动道:“你们看看!朝廷已在山西试行‘均田册’,丈量土地,按实际耕种面积征税,豁免贫户。还设立了‘义仓’,丰年储粮,荒年赈济。百姓称颂‘圣天子出,万民有靠’!我们若再打着‘均田免粮’旗号攻城掠地,岂非成了劫匪?”
牛金星厉声反驳:“这是缓兵之计!朱由检想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等他腾出手来,第一个杀的就是我们!况且,他启用卢象升、孙传庭,重建边军,分明是要武力镇压。我们若不趁势而起,迟早被剿灭!”
两人争执不下,李自成最终道:“传令全军,暂缓进攻,派出细作潜入山西,查证‘均田册’是否属实。若是真的……咱们就得重新想想,到底为谁而战。”
细作回报:山西某县,一户佃农因官府重新丈量土地,少缴赋税七成,激动得跪在田头大哭。另一村,里正私藏肥田被揭发,革职查办,土地分给无地农户。短短两月,已有十余万流民返乡复耕。
李自成听完,久久不语。他望着帐外茫茫雪原,低声道:“原来……老百姓想要的,从来不是打家劫舍的‘闯王’,而是一个能让他们安心种地的朝廷。”
与此同时,蒙古草原上,林丹汗亲率三万骑兵南下,与明军约定会师辽东。朱由检亲赴居庸关犒军,赐将士每人白银十两、御酒一坛。他在点将台上高声道:“朕知道你们苦。边军多年欠饷,盔甲残破,马匹瘦弱。但从今往后,每一两军饷,朕亲自盯着户部拨付!每一副铠甲,工部限期打造!朕可以三年不修宫殿,但绝不让你们赤手空拳面对敌寇!”
三军齐呼万岁,声震山谷。
阿巴泰在沈阳得知明蒙联军逼近,又闻郑芝龙投降、卢象升控制东南沿海,已然明白大势已去。他召集诸贝勒议事,沉声道:“明国皇帝已非昏庸之主,其志在复兴,其手段狠辣果决。我军若硬拼,必败无疑。不如遣使求和,暂保辽东,积蓄力量,待其内乱再起。”
多尔衮却坚决反对:“和?当年努尔哈赤起兵,为的就是取明而代之!如今眼看就要成功,你却要跪下去舔他的靴子?”他猛地抽出佩刀,“我宁可战死沙场,也不做降虏!”
兄弟二人拔刀相向,险些火并。最终阿巴泰妥协,同意分兵两路:多尔衮率主力迎战明蒙联军,他则带部分兵力护送皇室眷属北撤,准备退守黑龙江流域。
决战前夕,朱由检登上长城烽火台,遥望北方。王承恩递上一碗参汤,轻声道:“陛下,此战若胜,天下可定。”朱由检摇头:“天下从未真正安定过。今日平了后金,明日会有倭寇、有西洋红夷、有新的权臣、新的贪官。但只要这火种不灭,总有人愿意为百姓说话,为江山流血。”他饮尽参汤,将碗摔碎于地,“传令全军:明日出击,不留俘虏。让建州女真记住,背叛大明者,虽远必诛!”
次日黎明,大战爆发。明军火器营率先发威,数百门佛郎机炮齐射,炸塌清军前沿阵地。蒙古铁骑趁势冲锋,如洪流般席卷敌阵。多尔衮亲自督战,身中三箭仍不退缩,最终被卢象升率玄甲军包围,力竭战死。其首级悬于长安街三日,诏告天下:“逆贼伏诛,边疆永宁。”
战后清点,俘虏中竟有数百名汉人奴工,原是被掳掠的山东、河北百姓。朱由检亲至营地,见他们衣不蔽体、骨瘦如柴,不禁潸然泪下。他下令即刻释放,发放衣物粮食,并派医官诊治。一名老妇扑通跪下,哭喊:“皇上啊!我们以为再也见不到天日了!您真是我们的再生父母!”
朱由检扶起她,声音哽咽:“是朕来晚了……对不起。”
凯旋之日,北京万人空巷。朱由检骑着林丹汗所赠白马,缓缓穿过正阳门。道路两侧,百姓自发焚香叩拜。孩子们挥舞着写有“圣天子出”“万民仰赖”的纸旗。张皇后站在城楼上,含泪微笑。
然而,就在庆典当晚,赵九渊匆匆入宫,带来惊人消息:骆思恭在太原密室被人毒杀,凶手在现场留下一枚虎头印??正是当年魏忠贤的标记。更诡异的是,骆思恭临死前用血在地上画了一个符号,形似八卦,却又不同于任何已知卦象。
朱由检盯着那幅拓图,瞳孔骤缩。他猛然想起周延儒供词中的那句预言:“大明气数将尽,唯改姓易制,方可续命。”而那个符号,正是“空相”僧人口中所说的“天命之纹”。
“还没完……”朱由检低声说道,“真正的敌人,从来不在外面。”
他转身看向紫禁城深处,那里,无数宫灯摇曳,仿佛藏着千百双窥视的眼睛。他知道,这场博弈远未结束。权臣死了,奸宦灭了,外敌败了,但“影朝”的根系仍在地下蔓延,等待下一个春天破土而出。
但他不在乎了。
第二天,他颁布一道前所未有的诏书:废除“避讳”制度,允许百姓直呼皇帝姓名;开放内阁议事记录,每月公布于《京报》;设立“谏官擂台”,凡有才能者皆可挑战现任官员,胜者取而代之。
他在诏书中写道:“朕非圣人,亦会犯错。但大明若要重生,就必须让每个人都有权利说‘皇帝错了’。唯有如此,火种才能永不熄灭。”
孙世绾在冷宫读到这道诏书,老泪纵横。他再次取出那封信,添上最后一行字:
“吾儿,当你长大执笔书写历史时,请记住:最黑暗的时代,也曾有人选择点燃自己,照亮他人。那光,便是希望本身。”
白鸽再次振翅,飞越宫墙,消失在辽阔蓝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