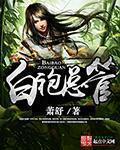奇书网>影视剧本创作基础 > 第二节 怪诞化作品例析(第1页)
第二节 怪诞化作品例析(第1页)
第二节“怪诞化”作品例析
例析一《审判》
法国1963年出品
编导:奥逊·威尔斯(根据卡夫卡的小说改编)
剧情简介:
一个流浪汉走向法律城堡的大门,要求卫兵让他进去,却遭到拒绝——尽管穷汉一再申辩说:法律大门应向一切人敞开。穷汉年复一年地等候在大门外,至死,也没能进入……
嘭然关上的大门,使小职员K惊醒:把他弄醒的却是前来逮捕他的警官A。A宣布K有罪:审判他的法律程序已经开始,但没有说他到底犯了什么罪。警官的助手企图劝说K行贿,还顺手拿走了K的衬衫。警官命令K随时候审,但允许他继续上班。
K从此进入现实中的“噩梦”。
K经不住邻居的妓女布斯特纳小姐的**,吻了她。但当听说他已被逮捕、要接受审判时,生怕“在政治上”受到牵累,大吼着将他赶了出去……
K自己也渐渐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强烈的负罪感……
K到公司上班,他的侄女艾尔米来找他。公司经理用怀疑的目光盯向他。K惶惑不安,连忙解释。但经理还是警告道:“你是很有前途的。别自己把事情弄糟了!”
布斯特纳小姐被房东撵走了,但K却觉得自己应负有罪责:因为自己吻过她……
K在剧院看戏时,被警官带走,要他到法庭接受审判。他按照警官给的地址找到法庭。法官却问他是不是一个油漆匠。K于是向大厅内的观众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演说:“刚才法官的问话,已经清楚地说明这场强加于我的所谓审判的性质!……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是无足轻重的,但是我认为,它代表了发生在很多人身上的事……”K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欢呼与掌声。但他突然发觉:所有听众原来都是政府各级的官员,他们之所以欢呼、鼓掌,只是为了诱使他说出更多的“错话”!K愤怒地离开了法庭。
K回到公司,发现地下室内有人正在受鞭刑,受刑者便是拿走他衬衫的那个警察。受刑者恨恨地告诉他:因为他向当局告了他们的状,才如此的。K想阻止行刑,他说:“应该受处罚的不是他们,而是那些地位在他们之上的人,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和整个机构。”行刑人根本不予理睬,反而抽得更加猛烈。K痛苦地逃离地下室,为自己的“罪过”呜咽起来。
K请求大律师为自己辩护。他来到律师事务所。在堆满法律文件的房间内,律师的秘书兼情妇莱妮勾引了K,并告诉他:大律师与法官是串通一气的,“你的错误主要在于太固执,又喜欢捣乱。”
K按照时间去法庭再次接受审判。法庭看门人的妻子希尔达告诉他说:明天才开庭呢。并告诉他:她可以利用法官对她的邪念来帮助K,并让K看法律书里的**插图:“这些书真是肮脏透了!”希尔达说着,也开始勾引K。此时,法官的学生(未来的法官)来到,将希尔达强行扛走了。K追出去,发现法庭办公室竟是一个极**的场所。他厌恶地离开了这里……
K又去找大律师,要解聘他。大律师则告诉他:“其实,套上锁链比自由自在更安全。”K迷惑不解。他看到一个“被告”竟然甘心情愿地忍受大律师的人身侮辱,还一个劲儿地趴在大律师脚下求情。他愤然指责大律师的虚伪、邪恶时,那个“被告”反而扑上来打他!大律师得意地告诉K:莱妮的一个怪癖就是追逐每一个被控告有罪的男人,然后再把她和他们每一个人的“经过”说给大律师听,以让他开心、提高性欲。K感到恶心至极,夺门而出。
K来到一个与法官有某种关系的画师处。画师说:K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假释,要么延期审判。但是又说:假释只会将被指控的阴影始终罩在你头上,而且每次假释之后,便意味着再次的被捕——因为警察永远不可能放过你;法庭也不可能总延期审判你,他们必定要采取种种措施、搜集到更多的“罪证”,以更严厉地审讯。画师最后说:“我这一辈子,还没有听说过有哪个被告被明确宣布‘无罪释放’的。”
K去找教士。教士则说:他的罪名大概已经得到证实了,只有向上帝忏悔……
“噩梦”终于有了结果:两个便衣警察抓住了K,把他推向一个深坑,并将尖刀举到他面前。K拼命挣扎。警察拿出一束炸药,点着了引线,然后跳出深坑逃走。K则把炸药远远地扔了出去。六声爆炸后,一股浓浓的黑烟弥漫了银幕。
化入片头:那座法律城堡的大门在缓缓地关上……
艺术剖析:
本片改编自卡夫卡的小说。因此,在剖析本片前,有必要先认识一下卡夫卡其人其作——
卡夫卡于1883年7月3日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犹太血统。在家庭中,父亲的专横狂暴,使卡夫卡的性格从小就印下了重重的阴影。而他所处时代的专制、强暴、阴冷、压抑,更使他成年后仍不能摆脱“父亲”的威逼,因此,表面的懦弱、隐蔽、羞怯、内向、孤独乃至麻木之下,则深深埋藏了审视、不平、叛逆、愤怒,以至抗争的强烈意识。而微茫的个人与强大的外力之间的极度失衡,其结果必然是前者的消沉与绝望:1924年6月3日,卡夫卡病逝,年仅41岁。
尽管卡夫卡创作时并不为发表,只是“纯个人写作”,只是一己的“我梦幻般的内在生活的表现”,但其作品一经创作出来,则必然就“非个人”,而必定具有时代印迹了。
奥匈帝国是欧洲有名的君主专制国家,哈布斯堡王朝长期以来对外侵略、称霸,对内实行家长式暴虐统治。但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帝国实际上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内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异常尖锐。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面对日益残酷的现实,卡夫卡作为具有敏锐观察力与严肃人生态度的人,不可能无动于衷。而这样的时代氛围,又不允许直接、公开的揭露、鞭笞,于是,具有特定心理状态的卡夫卡摆脱传统创作的羁绊、另辟蹊径、探索新的表现手段,就成为其创作风格的必然。
卡夫卡作品总的基调或曰主题便是:揭示社会现实的荒谬、非理性,自我存在的苦痛与原罪感,小人物在重重压抑下无法掌握自己命运、找不到出路的孤独、苦闷与恐惧,以及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
而在上述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要表现这种主题、基调,最适当的艺术手段,便首推“怪诞的抽象”(或曰抽象的怪诞)了。
卡夫卡的作品大都以明显的怪诞风格展开,主人公们大都无言以对地任凭荒谬生活的摆布。这里,荒谬当然不是胡编乱造,而是对现实社会中那些所谓的“正常”现象,以荒谬离奇的手法进行艺术表现而已。
比如在《判决》中,父亲判决儿子“投河自尽”,儿子就居然乖乖服从,投河而死;比如在《变形记》中,一个小职员梦醒后,竟然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并以甲虫自居而甘受他人摆布;比如在《老光棍布鲁姆费尔德》中,孤独的老人忽然有两个蹦蹦跳跳的赛璐珞球来与之做伴;比如在《乡村医生》中,出诊的医生在严寒中流浪,再也回不了自己的家中……而几乎所有篇章,又都是在具体的历史时间与地理空间之外展开:所述的故事都没有具体的时间,也没有确切的地点,更没有加以说明的“社会现实背景”。
卡夫卡就是通过这种怪诞的抽象,让读者在怪诞中受到现实的震动,在抽象里获得质感的悟觉。
由于特定的时代环境,卡夫卡的作品中难能避免地浸润着一种压抑与悲哀。他的作品大都描写孤独的小人物在各种异己力量控制下不断挣扎,但却更进一步异化、分裂、变态乃至死亡的命运。对个人命运、社会未来、人类前途,作品中常常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掩盖不住的消极、悲观意蕴。卡夫卡自己便直言:“目的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称作路的东西,不过是彷徨而已。”又说道:“巴尔扎克手杖上刻着的格言是:‘我粉碎了每一个障碍’,而我的格言却是:‘每一个障碍粉碎了我’。”
了解卡夫卡之后再看本片,便能有所把握了——
这是一部以怪诞的风格揭露当时整个社会体制(以司法体制为表现点)的荒谬、丑恶的内幕,表现小人物受压抑的愤懑、被扭曲的痛苦与难以自己的无奈状态的影片。
在其中,既有变形,又含着错位:警察与被告、罪犯与法庭、庄严的法律程序与丑陋的司法内幕……乃至每一种具体的人事过程,都明显着异乎寻常的状态与品格。而所有这些,则构成了K处身其间的怪诞社会与人生环境,而这种怪诞的环境,又反过来迫使K无可奈何地也发生了自身的异化。
通过本片,我们还可以看到:作为艺术表现手段,怪诞往往与象征融合一处、互相彪炳;而现实的梦境与梦魇的现实也难分彼此(现实与幻境**)。这种现象在现代的艺术创作中,是多见且自然的。借鉴于此,我们在自己的创作中,也应切忌死板、僵滞地成为“手段”的奴仆,为了艺术表现的需要,而要“颐指气使”地成为它们的主人。当然,各种手段在具体运用中,还是有主有次的。在本片中就较明显:它的主要艺术特色就是怪诞,以怪诞的物象象征着真实的本质,以怪诞的艺术氛围表现着扭曲的社会现实。
本片改编自卡夫卡的小说,但与原作有一种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正如英国影评家艾·斯坦因所说:“卡夫卡的小说表现的是一个相当真实的世界,但里面居住着梦幻中的人,而在威尔斯(本片导演)的影片中,则是真实的人居住在一个噩梦般的世界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