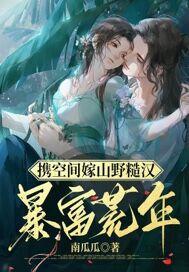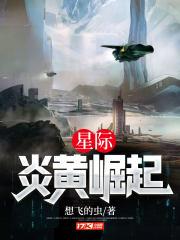奇书网>影视剧本创作基础 > 二想象类型(第2页)
二想象类型(第2页)
我常常出差,住旅馆,房间价钱很高。……去年,我去一个地方,一住就住到了旅馆。我看见一张价目表,一夜二十四元,我心里就急了,那个晚上我们都没有睡好。一块钱的骨头困在二十四元的**,这使我想到农村里面,群众做“油绳”去卖,这是很不容易的事,一天要跑很多地方……能赚到三块到四块钱,他们就非常高兴,因为在家里劳动一天,只能拿到几毛钱啦。那么,我就想到了:哎,你那个三四块钱,让你住这个旅馆试试!当时,这个想法就是这样引起的。从这个大框框出发,再来考虑整个布局的合理性……
至此,作者着重思考和解决两个难题:一是老农民要住进高级的县城旅馆,“一定要有个很得力的介绍人”。于是作者根据这种需要,想象出县委书记出场;二是要有恰当的理由:平白无故,县委书记为什么要请老农民住高级旅馆呢?“一定是出了什么不平常的事情。”于是,作者根据这种创作冲动,又接下去想象开来——
为什么不能回去了呢?那一定是生病了。生的什么病?生大病那就要送进医院。不能生大病。那就生小病,生感冒。……但陈奂生怎么感冒的呢?啊,应该是受了凉;为什么受了凉?没有戴帽子哟!……[12]
就这样,作者决定让小说主人公陈奂生进城住一次高级旅馆,而且凭种种需要,想象出他患了重感冒而又在车站巧遇县委书记,然后由书记吩咐小车司机开书记的车子送陈奂生先看病,再住进县委招待所……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想象,作品的大体格局才定下来,使预定的内容得以合理自然地向前发展。
这是理智想象的典型例子:作者预先有一个创作冲动(其中也就包含着自觉、不自觉的理性思考)、一个既定的创作意图,然后再在现实生活基础上展开充分的艺术想象,并使想象的内容朝着完满实现创作意图的目标前进。
2。情绪想象
情绪想象不同于理智想象之处是:它的实现过程并没有预定的创作意图,而只是一种特定的情感基调,在这情感基调、心绪氛围的左右下,它无既定路线但却沿着一个模糊性的方向自然展开,以渐次形成特定的形象群体。而在这形象群体的展现、扩充、选择与确定的过程中,甚至这个过程结束之后,才最终形成明确的艺术目的、构思框架。
我们且借用一个诗歌创作的例子来论证一下:
毛泽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曾传遍人间——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在这两首诗的前面,作者有如下题记:“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好个“浮想联翩”!一句道出此诗创作思维的过程——
听到血吸虫被消灭之事,作者心情激动。在这激动心情的影响下,江南的青山绿水、灾区的薜荔荒村、古时的名医华佗、现在夭亡的民众、大千世界、天上人间、春风杨柳、细雨银锄、新中国亿万人民的形象、祖国江山的无限风姿、牛郎无奈的苍凉、瘟神已去的欣慰……纷至沓来,以至“夜不能寐”,而所有这些内容绝不是按什么逻辑、循什么目标想象出来的,均只是在特定情感下、不由自主的“寂然疑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13],是在欣喜冲动的情绪基调上的自然展现。自然,实际想象的内容当远远不止诗中这些,一定会庞杂、阔大得多。但在这充分想象(通宵达旦)之后,欣然命笔之时,其创作意图才终于明确下来,这是毋庸置疑的:前一首以感叹为主线,后一首以欣喜为基调。可以说,这两首诗的创作,主要源于情绪想象,我们可触类旁通,进行影视剧的创作。
要注意的是:情绪想象不等于胡思乱想。一个作者,扩而大之,任何一个人的情绪想象,总还是有着一种基础氛围、大体范畴。因此,它尽管无既定的明确目标,却不能脱离特定的想象趋向——毛泽东虽“浮想联翩”,总还是围绕着血吸虫消灭一事的情境,并没有“离谱儿”地想象出第三次世界大战来。
理智想象与情绪想象虽各有侧重,但也不是截然分开的。理智想象中不可能没有丝毫的情绪想象成分,反之亦然。这一点,在理论上有了清楚的理解之后,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则不宜过于拘泥。否则,理论的探讨不但不能有益于创作,反成为累赘,就“南辕北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