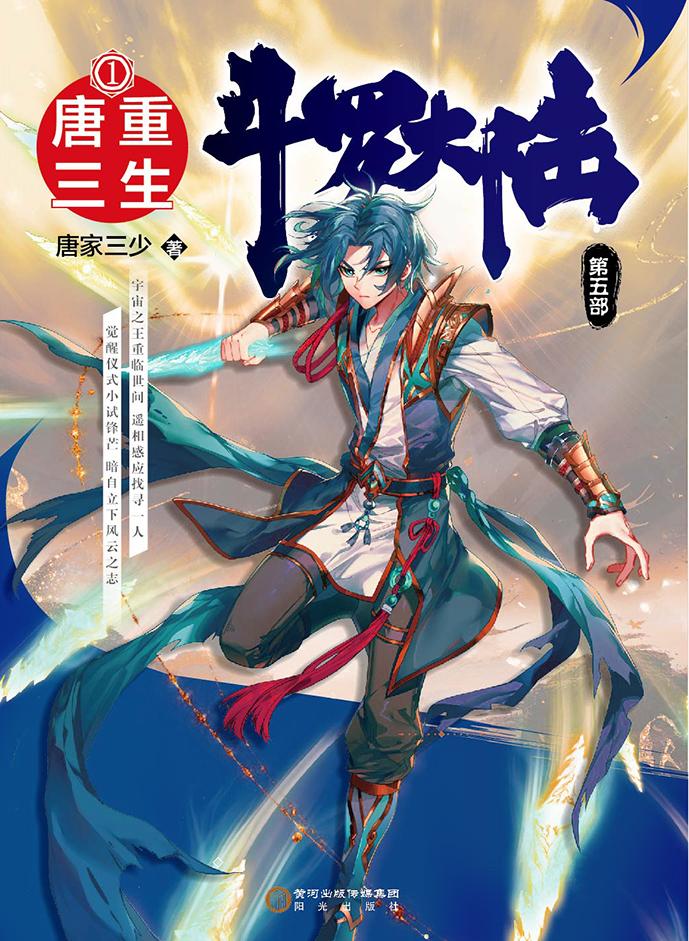奇书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观 > 第一节 生机 大母神崇拜与自然的丰产(第1页)
第一节 生机 大母神崇拜与自然的丰产(第1页)
第一节生机:大母神崇拜与自然的丰产
“大母神”一词是英文“theGreatmother”的直译,或作“theGreatGoddess”,是父系社会之前的最大神灵,也是史前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人类学家和宗教史家们确信,原母神是后代一切女神的终极原型,甚至可能是一切神的原始雏型。”[1]也就是说,大母神不仅是一切女神的终极原型,可能也是所有职能各异的众神的起源。由于女性被认为在生育上处于绝对的地位,且是大地丰产、自然蓬勃生机的象征,因此大母神崇拜就是对伟大生殖力与自然自由的崇拜。如此看来,大母神正是“伟大”和“母亲”两个词的概念的结合与感情的合一。
中国神话世界中,对大母神的崇拜是以女性生殖崇拜来表征的。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说明了女性繁茂的生殖能力在人类社会中的初始性地位,因此,崇拜母亲、信仰女性神灵在神话的原初秩序中是最自然不过之事。其中对始母女娲的崇拜与信仰便是典型一例。
女娲,作为最早的大地母神,她抟土造人、修补苍天、发明了笙簧、创设婚姻制度,在中国神话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书亦在其他章节中多有提及。但女娲虽然神格众多,但其母神的神格是最基础的,也是最初始的,而其文化英雄的神格则是后来的衍生与发展。也就是说,我们研究与解读女娲,首先也必须从她母亲神的神格与形象入手,这才是最真实、最初期、最纯净的女娲。
关于女娲的形象,汉代石刻画像和砖画中是“人首蛇身”或“人首龙身”的形象,这是先秦到汉魏时期中华民族原始神系大碰撞、大融合而使得龙成为高贵象征以后的产物,女娲的真实原型与蛙崇拜有关。由于婴儿的哭声和蛙的叫声相似,故原始先民认为蛙和婴儿,乃至和全体氏族成员同为一体,而汉语称小儿为“娃”,发音与“蛙”相同,根据中华语言音近义通的语用原则,蛙与娃、蛙与人也就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一氏族便叫蛙氏族,蛙则是他们的图腾神灵,而这一母系氏族的女族长便被尊称为女娲。女娲既为蛙图腾氏族的神灵,其神性必然和蛙相似。蛙类的自然繁衍过程,是将连成串的卵带排泄在浅水塘中,丝丝缕缕,连绵不断,然后借助水温来孵化。所以,蛙氏族创造他们的始祖女娲化生人类的神话时,自然而然就想到蛙类排卵的样子。当从蛙卵变为蝌蚪,从蝌蚪变成四肢的蛙,又从蛙化生出蝌蚪,生命可以通过循环或周期性变化战胜死亡,那么“蛙”便以永恒之神的身份被尊为图腾;而女娲则是通过人类生命一代又一代的繁衍、更替、成长而成为化育生命的象征和创造人类的大母神。在这里,她(女娲),或它(蛙),都是通过后代的延续完成个我生命的延续,从而实现作为“类”的永恒性存在,女性和蛙的生存性价值与自然性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同一性或者是趋同性。所以,一些彩陶蛙纹的下部特意描摹出圆圈以象征女性**。“人蛙一体纹的出现,表明在母系氏族社会的晚期,蛙不仅具有象征女性**的意义,而且发展出了象征女性的意义。”[2]
女娲最伟大与最基本的功绩便是造人,古代文献中多处有所涉及,如:
(1)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其腹化为此神。
——《山海经·大荒经》
(2)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做人,剧务,力不暇供,引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者,短人也。
——《太平御览》
(3)黄帝生阴阳,上骄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高诱注:黄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时,化生阴阳。上骄、桑林、皆神名。女娲,王天下者也。七十变造化,此言造化治世非一人之功也。)
——《淮南子·说林篇》
(4)传女娲人首蛇身,一日七十化。其体如此,谁所制匠而图之乎?
——《楚辞·天问》
(5)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
——《说文》
女娲抟黄土造人,是女性最基本的生育能力的反映,说其“一日七十化”,正是对女性强大生殖能力的歌颂与崇拜。《说文》中说:“化,变也。从到(倒)人,凡匕之属皆从匕。”我们知道,只有孩子出生的时候人是倒着的,那么这里的“化”字自然包含着生孩子之意。而《素问·五常政大论》中曰:“化不可代,时不可违。”和《礼记·乐记》中有着:“和,故万物皆化。”这里的“化”指的是自然的生长繁殖,也是主生殖之意。那么,“凡匕之属皆从匕”又是何意呢?我们可以从古代一个很有名的字“牝”中得以佐证。牝,母牛也,故坤卦中有着“利牝牛之贞”的卦辞,这里“牝”和“坤卦”相应,是阴性、母性的象征。而《老子》则有“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之说,这里的玄牝之门则是指女性**。如此看来,“牝”字中的“匕”就是雌性**的代表与象征,是一切生命的出生地。而雌性的**还有另一个功能,那就是与异**媾。这样,我们再来看女娲“一日七十化”中的“化”字,既然“属皆从匕”,是雌性**,和生育后代以及与异**媾有关,那么女娲“一日七十化”一定也就关系到生育、**二事。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女娲“一日七十化”中还有着“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的记载,也即是说,孩子的性别是黄帝决定的,耳朵眼睛是上骈决定的,手和臂则是由桑林决定的。从古代注释家的解说来看,黄帝、上骈、桑林都为古代男神的名字。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女娲的孩子身体的各个部分由不同的男神决定几乎是不可能的,神话所想表达的应该是,女娲有的孩子像黄帝,有的孩子像上骈,有的孩子像桑林,而之所以会像这些男神,是因为女娲在孩子出生前和他们先后**过,“像”乃是遗传因子的作用。再结合“化”字本原中有主生育与**之意来看,女娲“一日七十化”有赞美女娲强大的生育能力的意味,因为,伟大的母亲,必定为健康的女人,只有繁茂的性能力才能催生出强大的生育能力。只是因为,爱慕女娲的男神太多,以至女娲根本分不清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所以只好用“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这样的意象来表达。
随着时间的流逝,女娲繁茂的性能力逐渐被其强大的生育能力所遮蔽,以至人们在强化女娲人类始母这一角色的同时,几乎淡忘了她最真实、最美好、最**、最富魅力的女性本能。其实,在原始先民眼中,繁茂的性能力和强大的生育能力是交织在一起的,同样值得赞美、歌颂,乃至顶礼膜拜,正如同他们赞美丰沃的土地、绽放的鲜花、肥美的牛羊一样,这些都是自然生命力的代表与象征,是自然的丰收与自然的自由。而且,也只有丰饶、性感的女性之美,才能成就伟大的、慈爱的母性之伟大,繁茂的性能力正是强大生育能力的基石与发轫处。正如劳伦斯所说:“其实,性和美是一回事,就像火焰和火是一回事一样。如果你憎恨性,你就是憎恨美。如果你爱上了有生命的美,你就是在敬重性。性和美是不可分割的,就像生命和意识那样。那些随性和美而来,从性和美之中升华的智慧就是直觉。性是根基,直觉是茎冲,美则是花朵。”[3]
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在纳西族女神神话中得到印证:永宁狮子山是“干木”女神的化身,她是永宁地区的生育神,不仅掌管人、畜、庄稼的生殖,还主妇女的婚恋、生育和健美。“干木”是众神之首,周围的男性山神都要听从她的话,与她过“阿夏”[4]生活,其中,她跟四川境内的“瓦如卜拉”男山神为长期“阿夏”,和永宁境内的“瓦哈”、“则枝”、“托波”、“阿沙”交临时“阿夏”,几位“阿夏”之间甚至经常争风吃醋。当地人讲述“干木”神与她众多“阿夏”的故事时并无猥亵之意,甚至还要亲切地加上一句:“干木女神都要交阿夏,我们当然也要交阿夏!”[5]在这里,纳西族的“干木”女神和汉族的女娲一样,她随性、至真的没受世俗浸染的男女之爱,成为了人类生命和万物生命的起点。这就是说,性能力是伟大生育能力的起点与基础,只有拥有完整、蓬勃的性能力才有可能成为伟大的母亲,特别是化生人类与自然万物的人类始母,一定有着常人不具的繁茂的性能力与生育能力,是她们催生出精彩纷呈、生机勃发的自然世界。所以,《说文》中说到女娲除开化生人类,还化生万物;而“干木”女神不但主人类的生育,还主畜、庄稼的生殖,她们是人类与自然的始母与大母神。或者我们可以说,女娲们伟大的性能力与生殖能力正是一种蓬勃的生机与生命的冲动,人类世代繁衍、万物茁壮成长,整个自然界显现出一派旺盛、勃发的郁郁生机。这种生机是美、是真、是伟大、是慈爱,是人类全部美德之源头!正如荷尔德林的诗所言:“谁冥到这无边际的深,将热爱着这最生动的生。”[6]
“生殖之事,造化生生不已的大德”。人类的自然生命是从女性**——**中诞生的,由此,原始先民对女性的**产生神秘和崇敬之感,将自己最初的信仰定位于体现生殖功能的女性身上,并且极力地夸大她们的**,用它的肥硕来祈求人类繁殖的旺盛。1983年以来,考古学家们在辽宁发现旧石器时代,二三万年前的女性雕像,这些神像均为裸像,其身体的造型虽然各异,但引人注意的是她们都有明显凸起的腹部和着力刻画的**,许多神像还有肥大的**、巨腹、肥臀。[7]河北滦平县后台子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六具石雕**女像,这六具女像均是圆雕作品,其中最为完整的一件,高37厘米,为**孕妇形象,蹲坐姿势,腰腹宽肥,双手抚摸腹部,胸部两侧有**,表情自然。另一件头部残失的女像,残高20厘米,也为孕妇形象,身体端正,比例适中,颈后有突起的发辫,隆乳,曲肘,腰腹相肥,**表现夸张。而越南的女其泥像,则为一个坐着的女人,用手打开她的硕大无朋的**。这些巨腹、**、肥臀、**突出的女性的雕像,与其说是雕像人类女性本身,不如说是具象化地表现了人类始母的母性与女性的特征,是原始先民对大母神化育万物和人类女性繁衍后代能力直观认同的视觉转述。这种突出女性特征的雕像在世界各地均有发现,被人们称为“史前维纳斯”。
除开中国的女娲神话,世界很多民族与地区也都认为女性蓬勃与旺盛的生殖能力也就代表大自然的蓬勃生机与丰产丰收。在巴布亚基瓦伊部落,无论是农作物栽种还是收获,都有着一系列与性相关的巫术活动。在神话思维中,女性的性能力与生育能力,始终代表自然的性能力与生育能力,正是女性的**、肥臀和硕大的**孕育出子孙后代,化生出自然的丰产丰收。这说明了,女性的性自由与自然的生机是合一的,一旦女性的爱与性远离名闻利养,远离清规戒律,而仅是生命本能的勃发,那么自然也会彰显出一种蓬勃的性能力,于是草长莺飞,一派生命的新绿。
中国神话在强调与夸大人类始母的母性与女性特质的同时,还将其与土地这一自然基础相结合,称之为大地母神,于是便有了女娲“抟土造人”的意象。今天看来,原始先民的头脑中之所以出现女娲“抟土造人”,大概是因为他们看见自然万物都是从大地之中生长出来,如是自然而然地萌发了人类也是从大地之中而来的想法。而古文献亦有着“女蜗地出”的记载,既然人类的始母都是从大地中来的,她的儿孙们自然也是大地的孩子,是“地出”的。由于女娲是从大地中来的,她自然也就兼具庄稼神和土地神的性质,这和希腊神话中大地之母——女神盖亚颇为相似。盖亚最先孕育了天空乌拉诺斯,而后生了山脉、深海。她与广天**生了十二位神灵,人类则也是盖亚的后代。从神职上看,盖亚也是掌管大地和自然的神灵。此外,人类始母与土地相联系,还是因为大地与女性在自然属性上具有一致性:大地循环往复地孕育万物,并提供给维持生命成长的生物圈;女人则用自己的身体生儿育女,并转化为乳汁来喂养孩子,自然和大地一同被看作女性,是一位有生命的、有知觉的母亲。“在多产和生殖中,并不是妇女为土地树立了榜样,而是土地为妇女树立了榜样”。于是,人类有了两个母亲,一是女娲,一是泥土本身。如果没有女娲超自然的神力,泥土不会变成人;如果没有泥土,女娲也无法造人。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泥土给予人类的是物质生命,女娲给予人类的则是精神生命,而促使两者完整合一、融为一体的则是,母亲生养后代与大地滋养万物两者在特性上的高度契合。由是观之,女性在完成自身最大、最真、最完整的自然使命和社会价值——生育后代时,也就是超越主客体二元对立与自然物质紧密联系的过程。唯如是,才能彻底打破精神与物质的隔阂,实现神奇理性与热情生命力的合一。
除开汉民族广泛流传的大母神——女娲神话外,中国各个民族当中,都普遍有大母神以及关于她们创造世界与人类的神话,“有相当数量的民族,具有较为系统的神系,有众多值得称道的母亲神、女儿神、女孙神的女神神系”[8]。满族萨满教神话有“阿布卡赫赫”等300多位女神的庞大体系,壮族的“姆六甲”、苗族的“蝴蝶妈妈”、侗族的“萨天巴”、水族的“伢俣”、苗族的“罗迪”都是创世女神,是人类与自然万物共同的母亲,他们繁茂的性能力与强大的生殖能力催生出以自然性为价值基础的男女、人神、人兽、人物等和谐共生的多元图示。数量众多的各民族女神神话至今还在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流传着。例如,布依族神话中创世女神翁戛生出了天地、日月星辰,于是贵州布依族《古老歌》唱到:“哪个生出天?哪个生出地?哪个生出天亮?哪个生白天和晚上?哪个生月亮?哪个生太阳?翁戛生陆地,翁戛生天亮,生出白天和晚上,生出月亮和太阳。”[9]侗族的创世女神萨天巴,不仅生育了天地万物,也生育了人类的始祖,于是《侗族远祖歌——嘎茫莽道时嘉》唱道:“女神萨天巴生下地,生下天,生下众神,她还造火球、月球挂于天成了日月,撒汗毛、虱子于地育出了万千植物、动物。”土家族创始女神依窝阿巴得不仅成功地创造了人类,而且在人类将遭灭顶之灾时,提醒雷公有恩报恩,给人类送去葫芦籽,还教兄妹俩如何用生下的血团来繁衍人类。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自称为“布努”的瑶族人,把“密洛陀”作为普通的崇拜对象。密洛陀,布努瑶语,意为“母亲,”“洛陀”为女神的名字,“密洛陀”即“洛陀妈妈”。瑶族神话中,创世女神密洛陀创造了天地、万物,并用自己的奶水哺育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