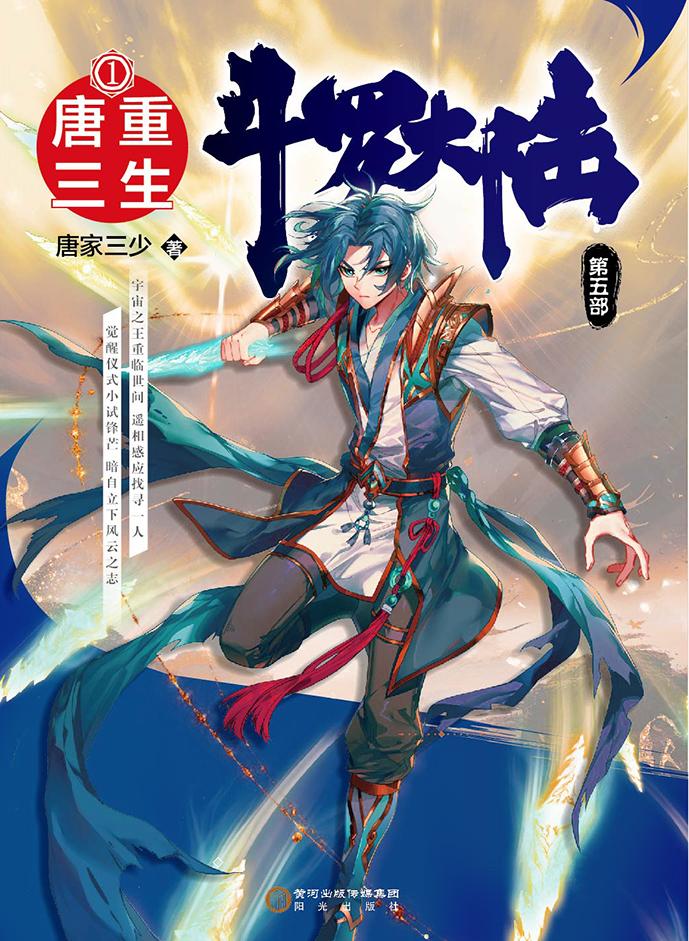奇书网>刑事政策原则 > 第五节 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刑事政策的定位与贯彻(第3页)
第五节 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刑事政策的定位与贯彻(第3页)
第四,完善无期徒刑的规定。建议将《刑法》第81条规定假释的适用条件中“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13年以上”,改为“实际执行20年以上”。建议将《刑法》第83条规定,“无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限为10年”改为“无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限为20年”,以有利于无期徒刑与死刑相衔接。
2。改进刑罚的裁量制度
贯彻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刑事政策,就刑罚的裁量制度而言,主要体现为加大对累犯的处罚与监控力度。累犯是高度危险的罪犯,由于其所具有的严重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一直是我国从重处罚的对象。目前,针对累犯的刑事政策在立法安排上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刑法总则中明确了对累犯从重处罚的基本原则;二是确定了一般累犯与特殊累犯制度;三是规定了累犯不得假释的刑罚制度;四是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毒品累犯的概念。[4]但是,关于累犯的规定也并不是完美无缺,有必要予以反思和完善。在此方面,笔者认为,可采取如下措施考虑予以完善。
第一,增设单位累犯的规定,并相应规定吊销企业执照等资格,以消除单位的犯罪能力。
第二,明确规定未成年人不构成累犯,以体现这一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的关怀。
第三,对累犯实行加重处罚。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与司法经验,对累犯由从重处罚改为加重处罚,以延长累犯的监禁期,从而控制罪犯出狱后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危险。对累犯可规定为应当加重本刑二分之一,对暴力犯罪累犯应当加重本刑至一倍。
第四,在监狱劳改场所设置严管设施,完善监控制度,对累犯分别关押,减少累犯对普通犯人的“感染”,以使累犯在延长刑期后在监狱能得到有效的改造。同时,完善累犯出狱后的社会回归机制,使累犯能够积极融入社会,并得到有效的管理,预防其再犯。
3。建立“严而不厉”的刑法结构
刑法结构的基本内涵是犯罪圈的大小与刑罚量的轻重的不同比例搭配和组合。犯罪圈的大小基本体现为刑事法网严密程度,刑罚量的轻重即为法定刑苛厉程度。由于受到我国立法技术与立法水平的历史局限,刑法结构基本属于“厉而不严”的结构。正如有学者指出,“从‘罪与刑’相对应‘严与厉’的关系上,罪刑配置不外乎有四种组合,即四种刑法结构:不严不厉,又严又厉,严而不厉,厉而不严。又严又厉的刑法结构在当今世界并不存在,典型的不严不厉似乎也没有。多数经济发达国家和法治水平较高国家的刑法大体上可归属于严而不厉的结构类型。而我国当前的刑法结构基本上算是厉而不严。”[5]
“厉而不严”的刑法结构,对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刑事政策的贯彻实施具有非常严重的不利影响,在实践中容易导致两方面的司法漏洞与混乱:一方面,由于刑法罪名体系的不周延,导致一些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无法入罪化,使刑事司法束手无策;另一方面,由于刑法罪名体系中的一些刑罚配置过于严苛,导致司法官在量刑时经常受到情与法的冲突困扰,为司法审判工作带来难题。因此,为了贯彻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科学地应用它,最为根本的是对刑法结构进行改造,严密刑事法网,调整刑罚结构。例如,对于当前一些严重侵害民生的行为,我国应当通过增补新罪名、降低入罪门槛、扩充行为类型的方式适度犯罪化。与此同时,对于一些刑法已有规定但处刑较轻的行为,则可以通过提高法定刑的方式加大惩罚的力度。
尽管刑事司法在很多时候比较主动地对严重犯罪给予严厉的惩处,但是,这并不是基于理性而实施的,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反应。显然,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刑事政策的正确贯彻,并不能仅仅靠这种自然反应来完成,相反,需要刑事司法机关以应有的理性主动地在刑事法律的适用中以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刑事政策作为指导,避免依靠自然反应打击严重犯罪所产生的一轻一重的结果。
1。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刑事政策的对象范围
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刑事政策,是一项针对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的刑事政策,由此决定了这一政策的对象范围仅限于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
第一,未启动刑事司法程序的严厉打击对象。未启动刑事司法程序时,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刑事政策所具有的作用主要表现为预防严重刑事犯罪的发生。一切行为在未进入刑事司法程序时,尚无法认定其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该行为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是大是小。此时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刑事政策的打击对象范围的划定,仅能根据刑法关于重罪与轻罪的分类规定。也就是说,在刑事司法程序启动以前,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刑事政策表现为预防严重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而此时的对象范围,应当是《刑法》规定的重罪。前文已述,重罪的范围包括刑法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全体罪名,以及基本罪状的法定刑为5年有期徒刑以上的罪名。任何人都能通过刑法本身的规定来了解刑事法律的打击重点以及国家贯彻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刑事政策的明确态度,从而不管基于何种理由避开实施犯罪。这其实也是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刑事政策在司法实务中得以实现的一种方式。
第二,启动刑事司法程序的严厉打击对象。启动刑事司法程序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刑事政策所具有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及时侦破刑事案件,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审判机关依法对犯罪行为裁量严厉的刑罚,从而全方位、立体地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启动刑事司法程序后,关于严厉打击对象的划定,应当从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进行衡量。因而司法机关既要查清犯罪行为在客观方面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又要认清犯罪行为人在主观方面所具有的主观恶性与其自身所具有的人身危险性。这样才能对某一具体犯罪行为进行法律价值的判断,不仅准确定性,而且合理地裁量刑罚。也就是说,此时严厉打击的对象,除包括上述未启动刑事司法程序时的严厉打击对象外,还包括人身危险性较大的犯罪分子,主要指累犯、再犯、连续犯、常业犯等。即使这些犯罪分子所实施的犯罪不属于上述严厉打击的犯罪范围,但因其自身所具有的特殊主体身份,使其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具有了较大的人身危险性,并因此而被划入严厉打击的对象范围。
在划定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刑事政策的对象范围后,该刑事政策的另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即为“严厉打击”。如何进行“严厉打击”?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严厉打击”当然应当秉承文明的刑事法治思想,以文明的手段对严重刑事犯罪进行预防与打击,以实现刑法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最后保障功能。
第一,未启动刑事司法程序时的手段要求。未启动刑事司法程序时,不仅要求运用刑事司法资源对严重刑事犯罪进行积极预防,更要求动用全社会的资源与力量对严重刑事犯罪进行预防。一方面,刑事司法应当构建严密的刑事法网,均匀地、科学有效地配置刑事司法力量,不仅仅是针对严重刑事犯罪的预防投入较高的司法成本,更应当以防微杜渐的观念对普通的刑事犯罪进行预防,力图通过以“打早打小”低成本的司法投入有效遏制严重刑事犯罪滋生的空间。通过此种刑事司法资源的均匀配置,以有效地防止如“严打”政策一样的情绪化司法现象的出现,避免刑事司法资源在某一时期之内过度消耗,而其他时期又投入不足。另一方面,刑事司法资源无论投入多少,其总量总是有限的。为了更加高效地实现刑事司法资源在预防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时的优化配置,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刑事政策必须以其他社会政策为辅助手段,共同应对犯罪问题。社会政策是指所有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政策。这些社会政策的科学运用,有利于调整社会关系,疏导社会矛盾,减少反社会情绪的积压,从而最终达到减少犯罪行为发生的防控目的。社会政策对于预防与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具有直接的作用,但从其作用程度与效果上看,属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刑事政策贯彻实施的辅助手段。
第二,启动刑事司法程序时的手段要求。进入刑事司法程序后,对于严重刑事犯罪的严厉打击主要体现在对严重刑事犯罪的及时侦破和判处严厉的刑罚。但是,严厉的打击,并非要求一切严重的刑事犯罪都要顶格判处。在刑事司法过程中贯彻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刑事政策,需要注意以下两点:其一,坚决贯彻刑法人道主义。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刑事政策的严厉性,不能违背刑法人道主义原则,根据刑法人道主义原则的刑法精神要求,一方面,应当禁止刑讯逼供;另一方面,应当罚当其罪,实现罪刑均衡。其二,重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应用。在刑事司法过程中,贯彻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刑事政策,应当不排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此时表现为,在对严重刑事犯罪量刑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察该犯罪行为的全部情节,不得忽视犯罪过程中的从宽情节。对严重刑事犯罪的严厉打击,是一种理性的打击,应当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辅相成,从而避免盲目的、过分的严厉。
3。构建新形势下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长效机制
为更好贯彻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有必要健全和完善严厉打击的长效机制,充分体现科学与法治精神,将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运动战向常规战转变,使这一刑事政策能够在动态社会中长期发挥预防和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作用。这一长效机制具有系统性、稳定性、统一性的基本特征,遵循法治原则、人权原则和效率原则,因而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构建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长效机制:
第一,严厉打击突出的严重犯罪活动,切实提高办案的质量和实效。
第二,加强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专业化建设,根据实际需要合理配置专门警力,确保足够的专业侦查和技术力量;加快侦查办案规范化执法体系建设;加强专业培训;进一步完善打击、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机制建设;整合各种刑事司法资源,形成打击合力,不断提高及时侦破案件的能力和规范执法办案的水平。
第三,积极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建立专群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全方位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第四,加强刑事司法信息化建设,以信息主导打击,切实提升动态环境下预防、发现和控制刑事犯罪,尤其是严重刑事犯罪的能力,提高精确打击的实效。
[1]郑善印:《新修正刑法之累犯规定是否违宪之研究》,载《自由·责任·法——苏俊雄教授七秩华诞祝寿论文集》,452页,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转引自于志刚:《论犯罪的价值》,53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于志刚:《论犯罪的价值》,537~53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卢建平:《刑事政策学》,30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5]储槐植:《再说刑事一体化》,载《法学》,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