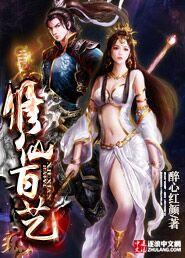奇书网>发掘美的真谛 > 九古典浪漫和现实的奏鸣曲(第3页)
九古典浪漫和现实的奏鸣曲(第3页)
尤金·德拉克洛瓦(1798—1863)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接受了完整的古典教育,18岁时进入了当时著名画家桂宁的画室,并在那里遇到了著名的浪漫主义画家席里柯,后者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25年他游历英国,在那里,他对英国的传奇文学和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等人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以后4年的创作中,主要创作这些文学作品中的某些重要的情节,在这些作品中他专注于同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同样的主题:对异国情调和受难的迷恋。1832年,他游历了非洲北部的摩洛哥,在这个阿拉伯国度里,他亲眼看到了仍保持着古代风俗的人们的生活,并在北非地区强烈阳光的照耀下,开始了对自然光线与色彩互动的敏锐观察,并把这些观察使用在了他的一系列画作中,如《阿尔及尔的妇女》、《被嫔妃环绕的摩洛哥苏丹》等。返回法国后,德拉克洛瓦利用他在官场上的良好关系,获得了许多重要装饰业务,成为巴黎画坛的首领。他作为浪漫主义的领军人物,一直与新古典主义的首领安格尔对抗,两个阵营口诛笔伐,相互激烈争辩,互有胜负。安格尔和他的学院派喜欢高贵冷淡的古典风格,以拉斐尔、普桑为典范;德拉克洛瓦则喜欢威尼斯画派和鲁本斯,他努力使自己成为反叛者,成为古典传统的颠覆者。
德拉克洛瓦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画家,他对绘画理论和艺术的精神探讨也非常感兴趣。他曾着手写作一本艺术词典,但未完成。他持续写作留下的日记,记录了他的私人生活,以及他对艺术奥秘的深湛的探究,为后来者提供了先行者的足迹。比如,他在日记中说:“壮丽适宜于绘画”,就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德拉克洛瓦的色彩感,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他对自然的认真观察;二是当时已经发展起来的色彩理论。如尤金·谢弗曼的科学理论。这种科学的色彩理论,也在19世纪的后半叶中带来了绘画革命。
图2-43《梅杜萨之筏》
虽然德拉克洛瓦深受席里柯的很大影响,被认为是席里柯精神的接棒人,但席里柯在艺术上虽然展示了浪漫主义的想象力和**的表达(图2-43),不过他对题材的处理上,还是严守了古典历史画的道德观念。德拉克洛瓦却远远突破了这一点,这引起了当时的巨大争论。他对画面那种幻想的、奇思妙想的形象,甚至是暴力的、充满刺激性的形象的追求,几乎不遵循传统的道德观念。这在他的《撒旦纳帕路斯之死》中达到了顶峰。他的画作不仅多为巨幅的,而且他所描绘的题材也多为群像、戏剧性的事件。他很少为某种单一而宁静的题材而绘画,他的画作多以戏剧性的冲突为主题,往往以激动人心的动**场面而引人入胜。他对色彩的使用更为大胆,在他的画面中色彩不再是沉着的、内敛的,而是艳丽的、跳**的,用这样的方式处理的色彩,仿佛具有一种触手可及的**和鼓舞人心的气氛。可以说,德拉克洛瓦的绘画对色彩的抒情表达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
我们先来看他的《台勒堡的战斗》(图2-44)。这幅画描绘的是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与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的一场殊死的战斗。
图2-44《台勒堡的战斗》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时,仿佛能够听到战斗中厮杀的呐喊、战马的嘶鸣和刀剑的撞击声。这个画面中人物、战马混杂在一起,扑倒的、厮杀的,马上的、马下的各种姿态交错一幅惨烈的场景。显然,德拉克洛瓦并不想按照古典的构图规则,把这个血腥的场面画得井然有序,相反,他是想通过这种混乱、无秩序感来强化战斗的残酷和惊心动魄。看着这个画面,我们就明白,画家只想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殊死战斗的**。
德拉克洛瓦把其笔触的力度、韵律保持在了画面上。用一种断断续续的笔法,使画面更有运动感和不连续的动**感。画面中色彩浓烈、厚重。画家对造型的追求也同样不在乎什么美,而是追求一种粗犷的力量和男性战争的狂放。
当时与浪漫主义一起,反抗古典主义绘画之固定程式的另一股思潮,是现实主义运动。现实主义运动在文学中的代表是诸如法国的巴尔扎克、福楼拜等,在绘画领域的主要人物,则是巴比松画派和居斯塔夫·库尔贝。
古典主义者认为,高贵的绘画只能画高贵的人和事,而那些做体力活的人,如仆从、农夫、工人,是不配做画的主人的。19世纪,人们已经看到这种现实的、真实的生活,也同样有它们“入画”的魅力和感动人的新鲜力量。
1848年的革命时期,有一批艺术家聚集在巴黎郊区的巴比松,遵循英国康斯坦布尔所踏出的道路,以新鲜的、欣赏的眼光,来画乡村的风景和农民的田园生活。他们画出透着新鲜感和真实、朴素的乡村风景和乡村生活,非常感人。因为这批画家聚集于巴比松周围,画的也是巴比松及巴黎近郊的乡村,故而被称作巴比松画派。
巴比松画派中间有两位主要的画家,一位是柯罗(1796—1875),一位是让·弗朗索瓦·米勒(1814—1875)。
柯罗是19世纪最伟大的乡村风景画家,在发展户外光绘画技法方面,扮演过重要的角色。除了画风景和肖像画外,他完全置身于当时法国社会变动之外。
图2-45《阿沃瑞村》
这里有一幅画是柯罗所画的他父母在巴黎郊区一个村庄购买的房(图2-45)。这幅画清纯、透明、新鲜而宁静。画面所展现的是一个村庄如梦似幻的早晨,毛茸茸的树枝仿佛在飘动着,显得轻盈而透明,树丛的两边有两个割草的农夫;中景是一大片湖水,湖水映着早晨银白色的天空;阳光照射在房舍上,在湖中投下了晃动的影子。整个天空画得清新、明亮,仿佛一切都失去了重量感。
这样的乡村景象,在柯罗的色彩阐释下,却变得如此具有诗意,如此清新感人,这就是柯罗的魅力。
米勒出生于诺曼底的农家。在巴黎度过一段艰难的日子后,落脚到了巴比松。在那里,他发展出了他的绘画世界——乡村题材绘画。他主要是将风景画的方法扩展到画乡村人物画中。他想要画出现实中的农民生活,画出在田里干活的男男女女。这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但在那个绘画题材和方法还由古典主义和学院派笼罩的时代,可谓真正的革命。因为,在古典主义和学院派看来,农民是乡巴佬,是下等人,是被嘲笑的对象。米勒却不仅要画他们,画他们真实的生活,而且还要把他们画得同样富有魅力。他最著名的画就是画于1857年的《拾穗者》(图2-46)。
图2-46《拾穗者》
这幅画中,没有戏剧性的故事,丝毫没有逸闻趣事的痕迹,画面是一个纯粹的劳作的场面:前景是三个捡拾麦穗的农妇,其中两个正弓着腰,在捡拾落在地上的麦穗,另一个则正从弓身捡拾的动作中挺起腰来,整理捡拾到的麦穗。她们既不美丽,也不优雅,甚至穿着粗糙,但她们劳作的姿势却既认真,又质朴,其中饱含对劳动果实的珍惜之情,展示出劳作者的艰辛和为生存而努力的态度。她们的动作和姿态缓慢而专心,她们的身体宽阔而结实。画家没有刻意美化她们,而是真实地画出了她们劳作的场面。人物轮廓简单,毫无浪漫和所谓古典的英雄气概,但她们简单而结实的体魄,却比学院派的画法显得更为自然,更为有力。
画面的远处,是堆积如山的金黄色的麦垛,有更多的农夫在那里整理着收割后的麦子。更远处,天空中布满了云朵,仿佛是黄昏时分,一层淡淡的金黄色正洒满天空和大地,映照着麦垛和大地,将劳作者的身影投在大地上,使整个画面具有一种诗的意境。
另一位将巴比松画派所开启的绘画现实主义道路推向顶峰的,是法国画家古斯塔夫·库尔贝。
古斯塔夫·库尔贝(1819—1877)1855年曾在一个棚屋里举行个人画展,他给画展起名为“现实主义,G。库尔贝画展”,从此“现实主义”就成了一场绘画艺术革命的标志。库尔贝的性格很像卡拉瓦乔,他不希望拜任何大师为师,而只是以自然为师,他的绘画理想不是好看,而是真实。
19世纪50年代,他的现实主义美学思想开始成熟:只关心“真实和存在的事物……想象力在艺术里是知道应该如何将存在的事物用最完整的方式呈现并组合在一起”。实现这一想法的方法是直接用调色刀,在画布上作画,使颜色具有逼真的质感和生动的力感。他希望用逼真的现实“惊吓有产阶级”,以表现出艺术的真诚、对抗古典的俗套和程式。1854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希望永远用我的艺术维持我的生计,一丝一毫也不偏离我的原则,一时一刻也不背离我的良心,一分一寸也不画仅仅为了取悦于人、易于出售的东西。”这鼓舞了当时的一些艺术家,他们决意只按眼睛看到的世界的样子来作画。
库尔贝的现实主义原则,在他的《采石工人》(图2-47)中得到了充分展现。这个题材是库尔贝偶然看到的,他看到一老一少两个工人在路边干活,劳动的艰辛和体力的巨大消耗,给他以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就想把他们直接画下来。他付钱给他们,请他们到画室来摆姿势做模特儿,以便能够更逼真地表现他们的劳动。显然,画面中人物身体的姿态是有意安排的,他让人物只以侧面出现,一个人物在把一筐石头吃力地端起来,另一个人物则单膝跪地,举起铁锤砸石头,这就构成了一起一落的动感韵律和平衡。同时,画家只在画面的右边留下了一小角空白,其他部分则全是实的,这又使画面维持了虚实的平衡。从这些方面来看,不能说库尔贝完全放弃了古典构图的原理。也正是这些构图原理承载了古典的尊严。
图2-47《采石工人》
现在我们来看画面中的“现实主义细节”。画面中的细节是触目惊心的,因为这幅画的画幅很大(213cm×312cm),人物与真人一样高,他们穿的袜子上的破洞也与真实的破洞一样大;他们身上的衣服不仅破烂,而且上面糊满了泥浆,在这里没有任何美化,有的则是对非人的劳动的控诉,库尔贝曾说这幅画是“对困苦和贫乏的一种难得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