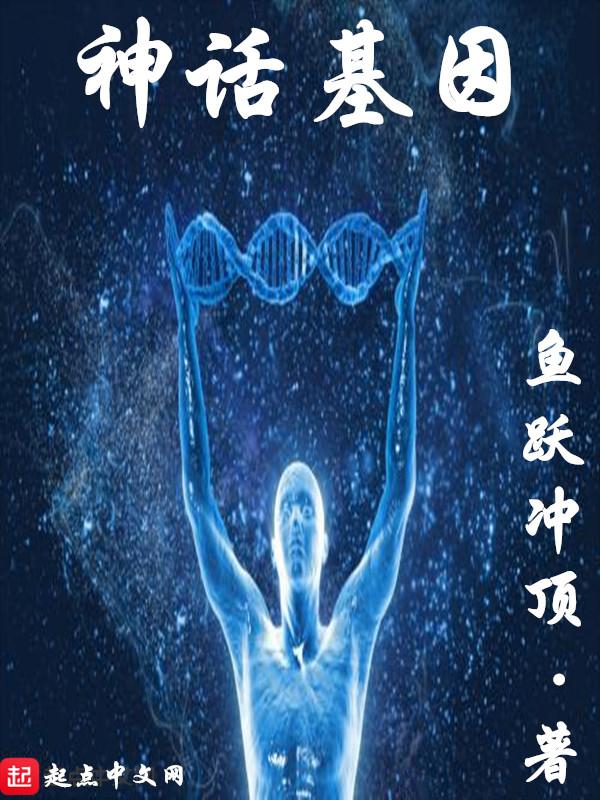奇书网>十种寂寞简媜在线阅读 > 第2章 黑夜(第1页)
第2章 黑夜(第1页)
第2章黑夜
晚霞在天边烧得橙红,
早月已升空,
这时分正是倦鸟归巢的时刻,
唯独他在秋风中朝向未知的暗路。
1
拍桌声,“安啦!”
“有我黑三在,这摊大的,稳赚!”原本敞开的衬衫,经他这么一拍,扣子又往下溜开一个,露出肩头半条不知是虎是猫的尾巴刺青。
“来来来,干啦!”唤作“落脚仔”的高瘦男子顺势举起酒杯,碰了黑三及阿郎的杯,三人仰头饮尽。昏黄灯色下,脸色都泛出猪肝红,一手夹烟,喝完酒立刻吸一口,喷出灰雾,预先庆祝丰收。
这三个未到服役年龄的年轻人,曾在同一间以管教严格著称却效果不彰的穷乡中学落脚过,也常在朝会时被训导主任叫上升旗台当模特儿,公然罚站示众。虽然各自犯行不同,却十之八九都同台,太阳底下站久了,不免在麦克风放送罪行的声浪中、头低低貌似羞愧的姿态下交换几句自家兄弟才会说的干话,因此日久生情,生出革命感情。水塘里浮萍与浮萍的交情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往往跟豪大雨有关。三人先后因被学校记过满贯或是家中发生这般那般的困难而学业中辍,离开学校后失去音讯,再相逢,就是在白花花的太阳下、热滚滚的马路上,在一个无须躲避训导与教官、不必靠学历与操行成绩也可以活下去的江湖边缘。
将近子夜,黯淡无月的寒冬,小镇夜市已没什么人声,早过了店家拉下铁门的时间,几盏要死不活的路灯亮着,这时候会经过这里的人,不是迫不得已出门就是无家可归。
挨着夜市边界一处无须付租金又不必被驱赶的三不管空地,挤着两摊小吃。为了营生空间宽阔些,两家说定,卖车轮饼的白天开卖,小面摊从黄昏开火到夜宵。这时刻不可能有人来,老板也不希望再蹿出哪个三头六臂的饿鬼要他煮面。他女儿是唯一帮手,她此时双臂环抱上身,歪头靠在不远处民家墙边打盹。她身上那件外套单薄了些,煮面时哈着热气跟夏天似的,要是打盹那就是结结实实的冬天,冷气流不放过任何人。他看了心疼,那面墙后是茅厕,比臭豆腐还呛,若不是累瘫谁也受不了那股一直攻击鼻腔的骚臭味。他也烦,这三个少年仔是常客,有他们光顾是好事,但一来就喝到凌晨还不散,跟暗光鸟一样,七月半的鬼都比他们早睡。他尤其不喜欢那个叫黑三的,动不动两只眼睛扫他女儿胸部。他不止一次跟女儿讲:“你眼睛要睁大一点,以后千万不要交那种混江湖的,一辈子衰。”还好已托远房亲戚帮忙留意,说不定过完年后她将到台北工作,不必再跟他陷在这个饿不死吃不好的面摊里一世不能出脱。他打了呵欠,把剩下的面条一束一束地塞进塑料袋,锅碗瓢盘都收妥,就等这一桌完结。
“春如,拿啤酒来……”黑三的声音。
“春如累了在那边眯着。够了啦,要收了,这么晚……”老板好言好语。
“想死啊?叫你拿来你就拿来!”
他双手不自主地往围裙上又搓又揉,提起脚却不知该怎样迈步,还是弯腰心不甘情不愿地拉出一瓶啤酒,趁机嘟囔一两句。
“不过,黑三,万事还是谨慎一点好。前不久,碑头那一帮才被料理过……你知道的。再说,那只老猴也不是三岁囡仔,恐怕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有一双不成比例的长腿因而得到“落脚仔”绰号的他,比其他两人多一份小心。好似腿长天生看得较远,能辨识结实累累的果树高枝深处有潜伏的暗箭等着。四个小时前,他们分别乔装成路人、工人到“业主”宅屋周边勘察,确认被前波强台风扫坏的后院铁门尚未换新。他们早就锁定这只肥滋滋的老猴,其单纯规律的生活模式也渗透入他们的作息中。好一阵子以来,这位八十靠边的有钱老头好似跟他们一起生活,至少对负责摸清他作息的阿郎来说是如此。他任何时刻看手表,都能推算出老头现在正在往餐厅的路上,还是看过连续剧进浴室正要洗澡。如今,带给农渔业惨重灾情的强台风提供一个破口,倒像老天爷给他们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落脚仔,什么时候吃到女人口水变缩头乌龟,一点胆也没。放心,我全准备好了,软的不行来硬的,就算他是孙悟空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黑三那张脸现出狰狞奸笑,他侧身斜向落脚仔,低声说,“要是真不行,一不做二不休……”黑三竖掌猛力比出一个斜切的手刀,仿佛刀下人头落地。落脚仔持筷夹着的豆干落到桌下,眼珠瞪得像龙眼剥去白肉之后的黑籽,舌头就像碟子上卤得烂透的大肠,吊在两排牙齿之间。
“干!”啪的一声,筷子被压在桌上,阿郎倏地站起来,瞪着黑三。黑三那个斜切手势激怒了他,说好的,谋财不害命。桌上空酒瓶撞在一起,差点跌个粉碎,空气在瞬间凝固。黑三猛地灌一口酒,也站起来。
“少年仔,拜托别这样,我生意还要做……”老板手里牵着油污围裙,不知道该冲着黑三还是阿郎为难地摇头摆手,活像一只落水狗。
“有话坐着说,再商量再商量,自己兄弟,统统是自己人嘛……”落脚仔慌了,用力把阿郎按坐下去,再去按黑三的肩头,这两人从未这么僵过,他忙着按左按右,好似他们是他抽筋的两条腿。
黑三慢条斯理地张开那两片厚唇,嘴角刻意地压弯着,从齿缝间迸出话:“男子汉大丈夫,要干就干彻底。若像老鼠看到猫尾就破胆,我劝你回家温棉被算了,走这途,不狠无路!”
“黑三,少讲一句,阿郎心情不是很好,算了算了,自己兄弟,再商量再商量……”落脚仔用手肘推了推黑三,场面总算缓下来。
“家私我准备好了。”黑三的声音冷酷地刺入夜风的心脏。付过钱,各自无声地散了。
阿郎凝视远处一盏朦胧的路灯,年轻瘦削的脸有太多棱角,好像会割人,也像被什么力量硬是削出来,浓眉纠在一起,杂乱的发丝垂覆额头,血丝在他眼里结网但掩不住眼珠的黑亮,他的眼神看来遥远,漫着一层迷茫,像那一盏路灯。紧闭着嘴,一句话也不吭,沉默惯常是他的武器,也是唯一藏身的地方。
2
最后一次勘察地点后的傍晚时分,阿郎随便找一家自助餐厅吃饭,出来时带两个便当。冬风像一匹饥饿的狼,迎面扑进他微暖的胸膛。
老旧公寓顶楼,加盖的一间漏雨小房间。屋内黑,开灯,只见桌上散开的作业簿、铅笔及没吃完的泡面、萝卜干,好似底下有洪水猛兽,所有的日子都堆积在桌上,旧的新的生的熟的香的臭的,堆久了自成半壁江山、熟悉的小窝。六七坪破烂小房间,夏热冬冷,散着久未打扫的霉味与厕所飘来的尿骚臭。地上摆几个小桶小盆,随时准备承接雨水,桶子不够多,摊着几件破衣吸水,像阵亡者无人收尸。壁上叠挂大大小小的衣服,又是短袖薄衫又是套头毛衣,穷人家的夏天和冬天是一起来的,四季没什么意义。没有床架的双人床底下铺塑料布防水气,**蓬着两条太空被,被子里还藏着一件黑外套,没套子的枕头清楚可见黄渍霉斑,倒也不妨碍睡眠——累极的人只求一处淋不到雨能躺下来的地方,至于让他躺平的是床还是地板,没差太多。唯一的一张单人沙发上,家用杂物堆得像小丘,那沙发无辜地拐了一只脚,不知是捡来时就如此还是被压垮。其实,对受伤的人或物而言,怎么受伤怎么弄坏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把日子过下去。
门推开,声音像打破玻璃似的流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