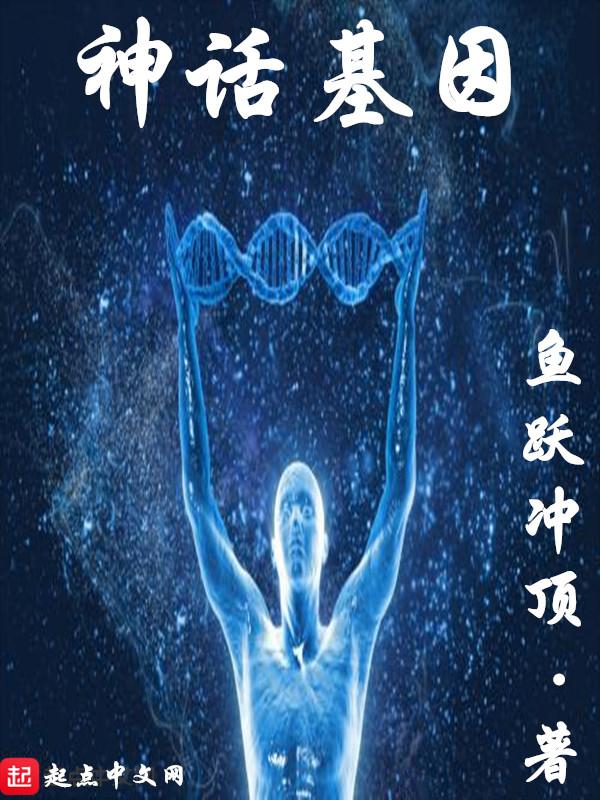奇书网>十种寂寞读后感 > 第4章 待续(第2页)
第4章 待续(第2页)
“我脑子里装的,正好是你这种人要扑杀的东西。”
她把这句话写在某本小说的最后一页,看起来像读后感。她知道有人会翻查她的笔记、日记,大概连**都会检查,断简残篇式的记录法适合用在独裁统治的家庭。
“人们依照她的指令来认识她,却没察觉每一套系统都是一种取消。”
哥哥看透这一切。
3
这个家有许多墙。
一墙之隔,阿嬷的房间常传来半呻吟半呼唤的声音,混杂在闽南语流行恋歌与盛赞保健食品功效的收音机放送中。恐怕是这原因,妈妈才把她的房间安排在这里。对一个“不上进”每天混日子的人来说,旁边是哀号病人或是动工中的挖土机,没什么差别。她最擅长的本事是无动于衷,能在补习班集中营老师的麦克风激动声中把小说看完的人,用她妈妈的话来说,根本就是个死人。收获也是有的,每天练闽南语,听久了也懂。“听众朋友,下一首是桃园的阿娥点的,好听的《春花望露水》……”当她正巧也躺在**发呆时,恍惚以为“这一生,像黄昏等待回航的船,回头只存冷冷的眠床,春花啊望露水,安慰一生的辛酸,操劳一生为子、儿孙”是唱给她这个等死的瘫痪老妇听的,刹那间吓得发颤,还好眨个眼回神,青春还在身上没少斤两。
“士婷喔,士承喔……今天几号?”
起初,她会放下书本,到她面前回应。隔不久,声音又响:
“士婷喔,士承喔……今天星期几?”
她还是去回应,顺便问她要不要喝水、尿布有没有湿。不久,又响了:
“士婷喔,士承喔,我的金孙啊,现在几点?”
她跟阿嬷不亲,一场中风外挂多重慢性疾病正好让独居乡下老厝的阿嬷合情合理地被送来与医生儿子同住。其他子女松了好大一口气,顿时对最有成就的大哥大嫂巴结起来,按季节宅配自种蔬果以表谢意。
“阿桑,你拿回去吃。”妈用脚把刚寄达的蔬果箱踢到门口,拆都没拆。
阿桑吃了这么多箱蔬果,难免说溜嘴跟来探视阿嬷的“寄件人”称赞并且请教种植之法。“寄件人”一听就知道他寄的菜阿桑全吃过,反倒躺在**的老母亲没吃过。那天他亲手拎一袋台农五十七号黄金地瓜加上刚采收的高丽菜、地瓜叶来,当下明白女主人眼里看不上这些沾泥带土的粗俗物,有钱医生家欠两把蔬菜三斤水果吗?遂恹恹地自觉猥琐不配在这间豪宅出入,从此不再寄,人也不来了。
“你这些兄弟轻松啦,把人丢在这里什么都不用管。以前还会寄菜,现在连菜也省了,当作人死了是不是。”她就是有这个本事,用最快速度让周围耳朵还听得到声音的人受伤。
每一句话,老人家都听在耳朵里——中风的人,垂手晃脚,偏偏听力不仅没受损似乎还升级。阿嬷是这个家的异乡人。士婷渐渐发现搁浅在**的她,用喃喃自语的方式返回稻田与菜园欣欣向荣的乡间,在长长的喟叹中跟熟识的老邻闲话家常、评议蔬果的丰收与价格,却靠听觉**回这间在乡人眼中有福报的人才能住的豪宅,呼来唤去儿子、两个孙儿及看护阿桑的名字。爸爸偶尔在上班、睡前出现,停留时间以分钟计,说的话多是短句,结束语不是“你莫想太多”就是“你好好休息”。哥哥鲜少到这个“回收站”来;妈妈要是现身大多跟喉头痒想骂人有关;阿桑需兼顾诊所庶务,三餐时间才会出入。表面上整天人影飘来晃去,热闹若是拖着一条长长的等待的尾巴就叫作寂寞,会回应的只剩她。
阿嬷一听到她回来的声音,开始喊“士婷、士婷、士婷”,像卧床的古堡主人拉铃唤地下室女仆,若不现身会继续喊下去。她做不到不理会,又觉得烦,以后便蹑手蹑脚开门进房间,像小偷。这让她无意间听到阿嬷的评论,对来探视的不知哪个亲戚悄声评论儿子媳妇:
“太忙啊,自早看到天黑,做医生真辛苦,三顿饭,一顿久久两顿相堵,身体都败了……她以为我听无,她咒我:你还要拖多久,你赖在这里做什么?她以为了不起啊,骂天骂地骂老母骂老爹。”
她听得毛骨悚然,不,暗中叫好。支耳往下听,却没捞到听者的回应,悄悄走到半掩的房门探望,房里除了阿嬷,没人,唯有的人声来自收音机。她忽然觉得与阿嬷像落在波涛汹涌的暗夜海面上,各自浮浮沉沉,鲸鱼、乌龟游来游去仿佛是路人甲乙丙。两人恰好被浪涛冲在一起,不是伸手互拉一把,是评估对方离灭顶还有多远。
她与哥哥也不亲,他的存在证明了她的无能,这个结到中学才算解开——解得开的都不叫结——其实跟他也没深仇大恨,干吗拉着他的衣角死命地跟呢?
资优生的背影是重的,挂着沉重的书包。他的作息从小被家教、补习班填满。她记得他那个念大学、具古典美的家教梅老师,教他国文与作文。她曾多次借口去借文具,趁机问一两个问题。老师曾说她是“女子中有英气的”,她以为是“阴气”,妈说的阴阳怪气。梅老师特别写在纸上递给她,她不懂什么叫“英气”,说难驯顽劣还好懂些,却留着那张纸,收在抽屉里。老师也看出兄妹之间的潜在矛盾,引了李白诗“天生我材必有用”之类的励志话。这个台阶还不错,被当作“朽木”当久了,也会摸索出“朽木虽不可雕,烧火可旺呢”的自我感觉良好心理。后来,梅老师上研究所辞了家教,哥哥专心去补习班安顿。兄妹俩各上各的补习班,各回各的房间,一家人很少在那张够坐十二人的昂贵柚木餐桌旁吃饭。
有一晚,她翘补习班的课在快餐店读小说,从窗边看到哥哥从另一家补习班出来,心生一计去跟踪,离他四步左右,看这个呆鹅何时发现。直到一小时后回到家进电梯,他才发现被妹妹跟踪,只有淡漠的两个字:“无聊。”
她从不曾那么专注地看哥哥这个人,一路上不眨眼地看身高一百七十五厘米的十七岁少年行走的样子,看他是否转头注意店面的陈设甚至兴起好奇心进去逛逛。是否回头多看一眼走过的漂亮女生,像雄性荷尔蒙分泌旺盛的高中生。都没有,他像被操纵的傀儡朝着一条熟悉的轨道前行,在站牌等车时仍拿着书本看,四周喧嚣的人事物像落叶浮尘,一切都在书本里,他活在里面,这个躯壳只是包装纸。
仅有一回,离他大考近了,她有点怪自己为何不用心记下那一日的所有细节,包括是否因为风太野把不知何处的鬼魅花香吹进他的房间,以致他放下书本钻回躯壳变成有血有肉的人。
他来到这个失败者居住的“流放之地”,进她房间,那时她正对着镜子剪发梢分叉,惊得本能地收起剪刀以为妈妈来了,看是他松了一口气。“钟士承你来干吗?”脱口而出叫他名字,不是平日习惯叫“哥”。太久没叫哥,当下记的是名字。
他从巷口“新星面包店”买了三个蛋挞,先拿一个给隔壁房间的阿嬷,用不流利的闽南语说很好吃,一个给她,自己垫着纸吃完一个,把纸揉成团以投篮姿势抛向垃圾桶,一跃往**躺下,“啊”一声,摸出压着的小说、漫画、偶像歌星CD、一把梳子及半包没吃完的王子面。
“现在的蛋挞没以前好吃,原来那个面包师傅结婚了,跟太太在菜市场边开面店。”她说。
“喔。”他随口答,翻着手冢治虫《怪医黑杰克》漫画,但显然兴趣不大,抛到一边。
“我去吃过,蛮好吃的。她知道我们家,每次都送我一条卤海带。阿桑说,那个老板娘是爸爸的病人,在我们这里做产检,有个八卦,说是之前在这里拿过小孩,现在回来做产检,一定要在同个地方把小孩生回来,好执着哟。你以后也要跟爸一样当妇产科医生吗?”
“不知道。”他翻另一本书,“原来你们女生都爱看这个啊?爱在远方……多远?十千米、隔太平洋还是外太空?男生送的!”书的扉页题了一行字,落款的是个男生名字。
她一把抢过来。
“他是谁?你跟他约会了?在哪里见面?”他显然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名字很感兴趣,像问案,问得津津有味。
她说:“你很无聊。你来干吗?”
“不要跟妈讲。”她避开这个话题。他也不追杀,眉眼间少了睥睨顿时柔和起来,看着妹妹剪发叉,咧嘴发出笑声,与其说笑声里有不屑的意味,不如说发现了他从未想过的奇怪事物感到新奇。他的五官清明,鼻梁特别挺,框着高度近视加上散光的褐框眼镜,却掩不住炯炯有神的眼睛,扫描一下,十之八九皆在掌握中。
“难怪你功课不好。”进房不到十分钟,他已扫描出房间里窝藏的违禁品不可能让念中段学校的她考上顶尖大学,更确认他与她的脑袋就像两个星球那么遥远。
“帮我剪一下。”他的头发天生自然卷,柔细带点棕色,头顶发旋处蹿出一蓬乱发。他真的低下头,好似等着妹妹帮他砍头。
她哪敢真的剪,意思意思修一下,看起来别那么蓬乱,翻着翻着,发现发旋边有个圆秃。
“惨了,你有鬼剃头,再秃下去以后交不到女朋友。”她大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