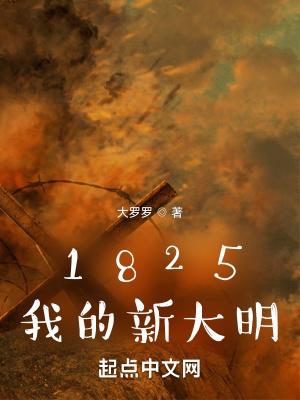奇书网>重生吕布三国 > 第203章 神兵天降邺城破(第1页)
第203章 神兵天降邺城破(第1页)
第三卷·官渡之战第203章神兵天降,邺城破!拂晓前的风像一柄冷刀,将城与野割成两半。邺城墙影沉黑,楼橹上灯火稀疏,值更的鼾声时断时续,仿佛一头吃饱了的兽在睡梦中打着呼噜。城外草原,十万甲胄静得只余皮革轻摩与马息细响。并州军列阵如山,却不鼓不号,唯有黑旗在风里缓慢舒展,像云脚下压住的一条河。吕布勒着赤兔,目光越过微白的天际,落在城门影处。他的呼吸极浅,像在倾听某种约定时刻的心跳。他身后,是张辽、高顺、陈宫、贾诩与沮授诸人。谁也不说话。昨夜血与火、勇与怒,皆已收束成此刻的寂静。“主公,”张辽低声,“若城门如常,强攻则多死,虽能取,非所愿。”“取城易,取心难。”吕布的目光不曾动,“今夜之后,天下人要记住的,不只是并州的刀,还有并州的法。”他压低嗓音,似对张辽,又似对自己,“三个前提:一,袁氏精兵尽在官渡,邺城守备空虚。二,彼料我分身乏术,必以常理度我。三,兵贵神速,未及反应,事已成。”他顿了一拍,眼底的光微微一收,“所以,我们等。”风更瘦削。就在黎明的边上,城内忽地升起一缕狼烟——不是警号,而是约定的印记。紧接着,城门楼上的锁链发出沉重的吱呀声,从城腹内部被缓缓卷起,门闸微开,石扇抖动,像一扇巨兽的颚在无声地张开。城上守卒起初还在迷糊,未觉其异;有驭门吏惊醒,俯身探望,却只看见门闩下方有一道细薄的影,像水里游过的一片叶。刹那,暗处银丝一闪,喉间一凉,惊呼未出,便已坐倒。门下绞车被卡入木楔,轮齿啮合,一寸寸挪开沉门。“龙越,已入位。”贾诩轻声向前一步,指尖垂落袖内,露出半寸青黑的小葫芦,“破门不在力,贵在静。静则守者不觉,觉则已晚。”他略一侧耳,远处链声与轧木声如暗潮徐徐推近。吕布抬手,方天画戟在风里一横,寒光像一枚压住天幕的钉——无声的号令。张辽、高顺齐应,陷阵营、狼骑如闸门开后奔突的水,悄然加速、继而轰然涌动,黑甲与马鬃在晨雾里化作两股铁流,直撞向那道正被暗力掰开的缝。——城内,另有一处静默的杀意正向门楼弥漫。龙越小队十余人,衣甲极轻,腰挎短弩与缚索,背负折叠钩爪。领队一声“抑息”,众人屏声屏气,手套在木栈上掠过,不出半点熟皮摩擦的声响。最后一名守门吏刚要提盏巡查,忽闻鼻端一甜,一只手从他背后捂住了口鼻。羊脂玉瓶中的蒺藜膏极淡极细,入喉即麻,不伤命,却能让人沉睡一刻。守门吏睫毛颤了颤,软倒。两名龙越兵以鱼骨刀挑断门闩旁的铜销,第三名把楔形木塞打入绞车齿间,用铜簧锁住回齿,防止守军逆转。钩爪从女墙内侧投下,银丝绷直,四人齐拽,绞车应力,门扉吐气。他们前一夜已精准截获袁营联络斥候——不是偶遇,而是预置。那斥候以为悄悄从西北角小巷穿出,刚拐过油坊的影,便被一缕白影无声挑翻;信简尚在腰间未及投递,已被装入油纸囊中,改头换面,成为龙越诱敌的第一枚“钉”。这“钉”让城守指挥误判攻点,把精锐换去北门,南门遂空。龙越在黑暗中,把“运气”按进了方案。“门四寸。”领队低语。门缝足可容两骑并过。下一息,城外铁流到来。第一队陷阵步卒不吼不喝,盾列压地,直楔门缝;第二队狼骑贴盾而入,蹄铁与木槛碰撞,爆出低闷的一串火花。守军惊起,仓皇提枪,尚未来得及结阵,便被锋刃自缝隙中逐段削裂:先膝,再腕,再喉。门内的小广场上,几名校尉高举狼牙棒欲集众反扑,却被张辽在马上以一记短枪横扫,连人带兵器掀翻在地。高顺背后三十名陷阵营老卒齐步踏入,每步相差半寸,刀光如同一朵花在空气里绽放又合拢,花瓣所过之处,只余人倒与血线。“守‘角’。”高顺声如铁。“先夺角楼,再断横街,然后席卷中轴。”并州铁令,字字入骨。从城门口到中轴街不过百丈。狼骑化作六股细流,沿雕栏、廊檐、房脊掠过,宛若城砖缝里钻出的风,直取钟鼓楼。钟未及鸣,钟正下的执槌兵已被一支短弩钉在槌柄上。龙越将一缕浸了油盐砂的麻绳顺势甩至鼓架,火花轻舔,鼓面缩卷。城中刺耳的警号,就此断了舌头。审配被急急唤醒时,外面已杀成一条响动更低的河。他撩起衣襟,跨出内堂,一名心腹迎上:“审公,城门失守,南市已乱!”“胡言!”审配怒极,“邺城重地,岂能一夜而破?”他话虽横,脚下却快,直奔吏部库房,欲取备用的号令木牌与印。才一推门,门闩竟空——印笏不见,内库文书散落一地。一个戴着面具的黑影从柜后起身,袖中猝然飞出暗钩,钩上绞着城门牙钥的皮条。黑影不言,执钩后退,一纵而没。审配这才明白,敌人不只在门,也在心。他胸口抽紧,喉间一股铁锈般的味道涌上来,仰头,只看见南天升起的黑烟卷着红光,像一张正翻过来的旗。,!“逢纪何在!”他厉声。“……逢先生方才出署,去集勇士。”心腹的声音在乱里发抖。下一刻,外头一阵马嘶,随即是刀环碰地的脆响;一队狼骑拐过横巷,斩马刀如水,逢纪被自斜街掠来的马队挟住,衣带缠足,跌倒在街心,尚欲挣扎,被横刀一按,血从颈侧流出,涌成一弯浅浅的小渠。审配僵在门槛,眼珠里倒映着那条小渠在晨光中闪了闪,象是他最后一丝“常规”的自尊,也被并州的“非常”踩碎了。——城门已大开。并州狼骑潮水般涌入,中轴上的石狮子在奔蹄下震得轻颤。张辽当先,高顺殿后,左右两翼的街口同时传来龙越的“清巷”手势:食指贴唇,掌心由上而下,表示——静、快、准。两列短弩兵在檐下翻身,弦声细微,箭头皆取军官肩章、鼓手臂饰,一息之间,中坚失指挥,千人之众,变作无头之蛇。“官仓别放火。”高顺一抬手,止住一名士卒的火折子,“城在,粮在。我们要取的不只是城,还有人心。”“是。”士卒将火折子捏灭,捏得指肚泛白。吕布策赤兔沿队入城,经过城门槛时,忽勒马,回首望了望闸牙上还挂着的两串断铜销。那是龙越留下的“签”,告诉他:城门并非侥幸,是算计。吕布的目光在那两串铜上停了一息,才又前驱。他心里一阵旷然:自乌巢之火起,天下把他当作在火里横冲直撞的虎;今夜之后,要有人知道,虎,也会算。东市的廊屋下,突然有十余名袁军弩手冲出,横列欲截。他们的动作不乱,但节拍满是空拍:这是被惊破胆后的“整齐”。张辽抬手,短枪斜指地面,“第三列,给我‘断节’。”三十名陷阵营老卒提盾半步冲前,每人只出一刀,不追第二刀,刀落即退,退时盾面一压。十余名弩手像被同一根无形的线牵拽,齐齐跪倒,弦声未出喉已断。“西角楼已下!”一名龙越士卒攀着绳索从楼脊滑下,掌心一翻,亮出一枚带血的铆钉——角楼绞链的最后一颗活扣,已被他们以铜楔替换,门闩再难复位。“中轴,进!”张辽枪尾一摆,狼骑呼啸而前。钟鼓楼前,审配带着二三百集结来的甲士试图立“壶口阵”。他深知若中轴被断,邺城便不再是城。然而阵才开半步,一侧屋脊上传来“嗒”的一声轻响——仿佛是谁把指甲敲了敲木梁——随即两缕银线如同燕子尾上的丝,悄然垂下,勾住壶口阵边缘两个小旗手的旗杆,一拽,旗倒、步乱,壶口顿失结构。审配怒极,提剑欲冲,却见对面黑甲将领策马上前,刀未举,眼神已象是一把稳稳按在他肩上、令他喘不过气的手。“审公,可降。”张辽平声,“城已定。”审配看着这名年轻的并州将军。那一瞬,他眼里闪过屈辱、愤怒、清醒与疲惫,最后都化作一声轻轻的叹。他把剑横在掌上,两手上举。张辽一挥,左右兵士上前解下其佩,押向后队。并州军队列仍不吼不叫,只在地面留下一串整齐的铁印。——战斗并未延宕到日中。大半个时辰之后,邺城的风向从杀意变作欢呼的热浪。中枢诸署皆在并州军掌控下,城头旗影交替,黑色“吕”字大旗从南门、东角楼、钟鼓楼一道道升起,最终在袁府上空展开,阴影压住了整片院落的瓦与槐。那字在风里猎猎,仿佛刚从火中走出。高顺巡过巷战余地,转过一个巷口,忽见一名陷阵营士卒靠墙而坐,手臂被短弩擦破,血浸了半袖。高顺俯下身,那士卒欲站起行军,高顺按住他肩,“伤口深,先扎。”“都督,我还能上。”那士卒咬牙,声音却平静,“能赶上今日,死而无憾。”“跟着主公,”高顺取出扎带与药粉,手法干净利落,“只有荣耀,没有遗憾。”他替士卒扎紧伤带,拍了拍他的肩,“坐半刻,再去收敌械。”吕布在袁府前勒马。阳光终于从云脊上掀起一线白,落在他甲片上,像一层薄霜。他缓缓翻身下马,从怀中取出一方白帕,仔细擦拭方天画戟上并不存在的血迹。围拢的将校与士卒屏住呼吸,那一刻,喧嚣仿佛被他帕上的轻拭一寸寸抹平。对他而言,这惊天动地的一战,只是棋盘上的一枚落子,准确、必要、无须多言。陈宫立在台阶下,仰望袁府之上“吕”旗初升,目中微光起伏。他忽然仰天长叹一声,道:“吾所以谋者,人道也;主公所谋者,天道也。”众人闻言,纷纷侧目。贾诩垂眸而笑,沮授扶着胸口,低低应了一声“是”。——回望破城之机,龙越之术在晨光里逐一显出暗纹:他们用的是纤维浸油的丝索,遇火不焦,遇水不滑;用蒺藜膏麻痹守卒,不杀不乱;用铜簧锁住回齿,使门闩失效;以鱼骨刀逆着木纹剖开闩槽,再以铁楔替代活销,确保门一经开,无力可反。这不是“武功高强”的戏法,而是手艺、纪律与算计叠加的结果。其行如影,其刃如针,正应了他们的绰号——“神秘的匕首”。,!有人在城楼上质疑:“邺城何以如此之易?”贾诩负手而立,淡淡道:“非城易,时势难。袁氏重兵系于官渡,邺守以为并州必不能两处俱至——思维定式也;又以为城门有铁,则可一夜安枕——守备怠也;复以为‘非常之举’不出法度——不知变也。三者叠加,非我之幸,彼之必败耳。”吕布听罢,只抬眼看那面旗,未置一词。他的沉默里有火也有水——火,是方才刀背上的热;水,是此刻大局上的冷。他明白,胜利的姿态当是收与放:收住贪杀,放开仁威。于是他命令:张辽接管军政衙署,高顺严禁掠夺,违者军法;贾诩、陈宫拟定“城内安抚三策”——先安留守官吏之家,后收军械,再整保甲,以令行禁。“审配押解府中,以备听审。”张辽回禀。“暂不辱之。”吕布一扫众人,“城中老小,皆袁氏所系。今日并州入城,须是天光,而非火光。”他转首向沮授:“先生伤未愈,然烦你先做一张‘城内家口籍’,文武百官、宗室外戚,一一登簿,不许人间一言惊惶。”沮授躬身:“谨遵。”他的指尖在帛上轻点,仿佛又在为并州算一笔远大而细密的账。城头的风换了方向。南门外,百姓初敢探头,有孩童趴在城砖上看那面陌生而威严的黑旗,眼睛被光晃得眯成一条缝。有人小声问:“这……还是袁家的邺城吗?”“今日起,”有士卒扶起一个老者,轻声道,“是安城。”“安城?”老者讶然。“安于民心之城。”士卒笑了笑,把手里的干粮塞进老者怀里,复又提刀去追他的队。他背影笔直,像这城墙新竖起的一根梁。——午时未至,大局已定。袁府内院,绣屏帷幕还未撤尽,庭中花木在风中轻摆。吕布立在阶前,看见一串鸟从榆树上惊起,又落在另一处屋脊。他默然片刻,低声对陈宫道:“今夜乌巢之火,今朝邺城之门。天时、人心,皆可借,唯不可骄。”陈宫点首:“我自此后,当以‘驭后’为先:城内人质、官绅、商旅三册,分而安抚。否则大胜之后,反生乱源。”贾诩笑意更浅:“袁绍在官渡前线,闻讯必狂。狂兵易动,动则露背。丞相……曹操,亦必侧观,甚至推波。诸侯将以此战为‘分水岭’。”吕布微微一笑,不语。他忽想起白门楼的风、宛城的巷、乌巢的火,再到此刻袁府的静。他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听见一个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向前。于是他把方天画戟在阶前轻轻一点,像在这城心上落下一个稳稳的句号。他回身上马。赤兔掠过院门。城中钟鼓楼上空,黑旗猎猎,仿佛天穹落下一角夜色,压住了昨日的名字,写下了今日的新名。“启禀主公,”一名龙越队长掩面来报,“署中人质多,皆袁氏家眷、外戚与文武百官之家口。请示处置。”吕布收缰,沉吟少顷,道:“不辱,不杀,不乱。先封户籍,遣医入府,给以粮盐。至于罪与责,待审配等人陈情,三司同议。告诉城中:并州不抢人,只夺心。”龙越队长领命而去。陈宫听罢,心头一松,像压在弦上的指蓦地抬起。贾诩望着吕布的侧脸,忽然低声道:“主公今日所夺者,不止一城。”吕布看他一眼,目中平静,似云开日出一线。——远在官渡,袁绍帐前,急报交叠,如雪飞舞。有人嘶声:“邺城——破!”袁绍手中玉如意堪堪坠地,额上青筋胀如蚯蚓。郭图、辛评跪而叩:“丞相,罪在臣等!”袁绍胸膛起伏如鼓,久久,方吐出一口如刃的气:“调兵!”曹操闻讯,立于帐门之外,眼角的笑意如刀背上极细的一层光。他低声与郭嘉道:“并州,取了‘根’。接下来,看他如何收。”郭嘉拄着柱,笑而咳:“也看袁本初如何怒。”风从北原吹往南城,带着火熄后的灰与血的腥,穿过余烟未散的乌巢,吹进新落的黑旗。旗在风里展开,像一场刚刚开始的长歌。——黄昏,邺城中央广场。并州军列阵受降,审配等人被押至台下。吕布骑在赤兔上,从广场一端缓缓行至另一端。阳光再一次把他的影子拉长,落在石砖上,像一条黑色的河。他收缰停步,回身望向袁府屋脊,那面“吕”字旗仍在高处猎猎,替他说了千言。他忽然笑了笑,那笑淡得像风刮过雪面——无声、却冷冽。他知道,这一刻,官渡战场的秤砣已被他按断一枚;他也知道,将要补上的,是更重的砝码:家眷、百官、袁氏反扑、诸侯观望。那些沉甸甸的问号,像城心之下未曾熄灭的炭。“陈宫。”他轻唤。“在。”“收兵,闭城,三日不许扰民。于城门贴榜两行字——‘并州不夺财,不夺女’,‘敢犯军令者,斩’。再于袁府门上贴第三行——‘今日胜,不为辱人,只为安天下’。”陈宫躬身,转身而去。行到半途,他回头望了一眼城头的大旗,恰逢风口,旗面扑地,黑影如潮,压得他心里也沉下一块石。他忽地又想起早前所言,便在心里复诵了一遍:“吾所以谋者,人道也;主公所谋者,天道也。”他知这句今日既是赞,也是劝:天道高远,人道不失。广场上,军士们把敌旗一面面卸下,叠成整齐的方块。高顺将那名受伤士卒唤至,命其持旗入列。士卒挺胸而立,旗影掠过他的颊,像从少年脸上抚过的一根鞭子,疼,却骄傲。天色渐暗。城墙上最后一串烽火被浇熄,只余新旗在风里。吕布拨转马头,赤兔踏碎一滩晚霞,铁蹄声敲在石上,叮叮有节。他的背影被夕光镀成一层薄金,既像人,也像一柄插在城心上的戟。而在更远处,官渡的鼓正重新擂响,袁绍的怒潮堆起新峰。风从城中穿过,带走白昼里喧腾的热,留下夜的冷。有人在墙头小声说:“这仗,还没完。”当然未完。城门是开了,城与天下的门更在此刻敞开——它们所迎来的,不止是胜利,还有审判、选择与更大的刀光。邺城既破,局势才始。:()重生三国:吕布,一戟破万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