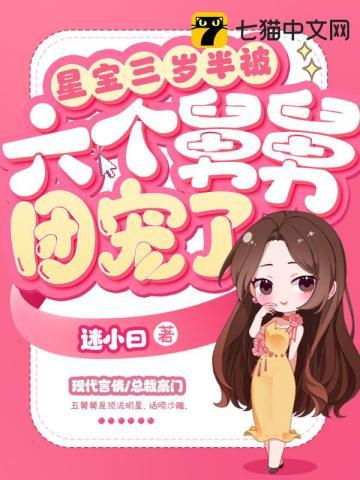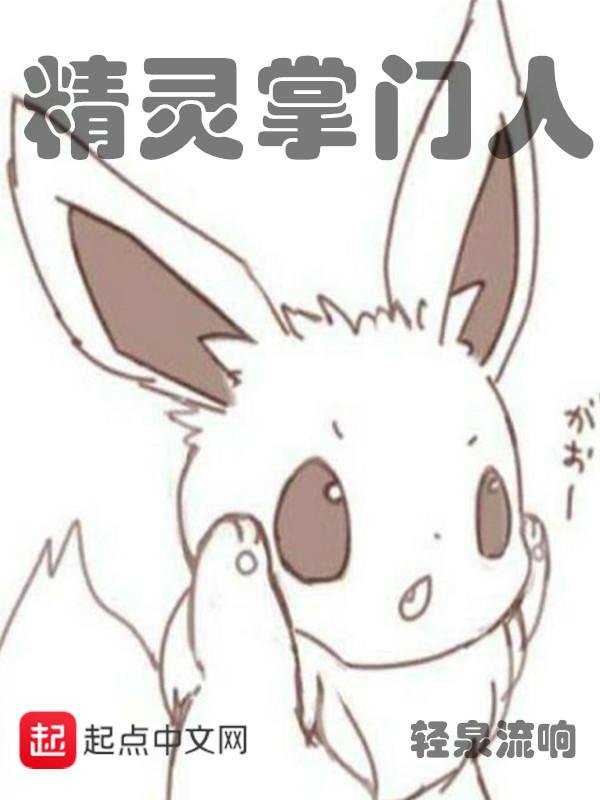奇书网>南国之冬是讲什么的 > 第8章 诗诈(第2页)
第8章 诗诈(第2页)
这两首七律里面,其宛转邃密的用意是一层,而其狡猾巧诈的动机是另一层,我像剥洋葱似的一点一点推敲出来,觉得有一种在深深的隧道里透见遥远之处微微露出一点光明的欣喜,不意正是这样,已然落入了胡导演的陷阱。我开始对“扮皇帝”三字有了别样的体悟——“扮皇帝”当然不是真的当皇帝;果若为皇帝而不当真,则非一般人所谓的拥权自重之徒,那么,胡导演想要让我去揣摩的袁世凯,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在近代国史上形象如此鲜明巩固的一个人,还能有什么新的角度去加以映照逼视呢?
一九九七年一月十四日,胡金铨导演遽尔过世。在葬礼上,人人红着眼。除了排队行礼如仪,坐着的、站着的,无不喁喁互道逝者未竟之功、长遗之憾。我也像是着了寂寞的传染,流连不忍去,同许多电影圈儿里相熟或不熟的前辈瞎三话四,才猛可发现成为一张巨大遗像的那个人居然有那么多想干而没干了的活儿。想干而没干了的活儿一经全面比对揭露,给人的感觉就不只是可惜,甚或还透着几分荒谬之感——我想:就算是再给胡导演一百二十年,他也拍不完想拍的故事。
“我想就是再给胡先生一百年,他也拍不完想拍的故事呀。”说这话的是个小个子,在给那张遗像行鞠躬礼的时候,小个子与我并排。我们并不相识,但是面前庄严的死亡让随机而遇的我们看起来仿佛一对老友。队伍缓慢地前进,或一排两人,或两排四人,有的更多些,都算是一个致祭单位。我身边这矮个儿接着忽然用一种听得出生硬的口音问我:“我不是很熟悉这种场合的做法,先生你是哪一个单位,我就跟你一起,这样可以吗?”
站进行告别礼的队伍之前,我用的是“张大春工作室”的名义——在九十年代初的几年里,我制作兼主持好几个电视节目,会计告诉我:无论什么开销,都得报到公司的账上,这叫搜集发票。我一向不知道送奠仪可不可以报账,然而当参加公祭之时,人家安排你上香,请问你属于哪个单位,开发票的本能便蹦出来了:“张大春工作室。”
我冲小个子点了点头,并且顺手掏出一张名片递过去,说:“‘张大春工作室’,可以吗?”
那人双手捧住,似乎十分意外,又似有更多的惊喜,连忙要掏名片给我,不意却教司仪的呼唤打断了:“‘张大春工作室’,上香——献果——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成!”
不,礼没有成。我身边算是本工作室临时员工的这位,竟然猛可朝前一步,趴下身去,深深地、缓缓地、有如虔敬之极地对着微笑中的遗像拜了下去,额角贴伏地面——所谓顶礼——之际,口中还咿咿唔唔吟哦起来。这个突兀的动作使我相当尴尬。我并不想跪拜,而一个忽然算是我的员工的家伙当众行此大礼,我总感觉要为他执拗的敬意或者疯状尽点儿什么责任,于是只好愣着、杵着、等着。这位矮个子立时成为焦点,吸引了所有在场之人的视线,连带地我也遭殃,像是牵了头特别调皮、不听使唤的宠物,进了兽医院。原本该悲凄、起码肃穆的场合居然点缀出了荒谬的趣味。
小个子行完了他自己的那套礼,站起来朝我一摊手,像是咱俩早就商量好的这一幕,我却似乎丝毫没有反抗的能力,顺着他手掌指示的方向,从厅堂的侧门就出去了。当我再一回身,他的手上多了一张名片,十指密捧,恭恭谨谨递上前来:“张先生,这一次我来参加胡导演的告别式,也是特别来想见你一面的。”
名片上黑大光圆四个正楷字体居中:藤井贤一。
“有什么事吗?”我问。
“关于胡先生生前的一个拍片计划,胡先生曾经同我说过:要向张先生您请教。”说着,他像是对着遗像一样深深一鞠躬。
“是那个《扮皇帝》吗?”
“呃——这个嘛,”藤井贤一迟疑了片刻,笑了:“《扮皇帝》也可以,《窃国风云》啦、《护国记》啦也可以,什么《南国之冬》也可以,最不重要的就是名字。计划是有一点改变了,是的。我们可不可以谈谈呢?”
“现在?在这里谈吗?”我回顾一下灵堂,里头正在献果的是香港来的媒体人李怡和金钟。
“只要张先生有时间,现在谈也可以,我们再约一个会也可以的。”
“老胡死了,我是没有兴趣再给人写本子了。”我收起了那张名片,掠过一个无关紧要的念头:这名片上的正楷颇有碑体的底子,还真是一笔好字。
藤井贤一似乎早就料到我会这么说,立刻道:“不不不,不是写脚本,是提供一些具体的思维。”
“提供一些什么?”
“一些具体的思维。”他坚定地再说了一遍。
老实说,我对于一转念就变卦十万八千里远的那种电影发想会议已经倒足胃口。通常就是这样的:一群抽着烟、嚼着零食、甚至喝着烈酒的汉子,围坐在一间密不通风的冷气房里,晨昏不辨,朝夕不停,随口胡诌一些带着九成欺罔性质的奇遇或幻想,再把这些彼此原本无涉的段子用简陋的情绪因果或者比被雷劈的几率还低的巧合串连到一起,讨论的人们在热切而充满夸张惊讶的气氛之中误以为这就是惊人的叙事艺术。我一想到这种场面,就觉得厌烦。而且,每一次我参加导演或编剧的告别式的时候,都觉得这种会议和他们的离世才有着不可切割的逻辑关系。
如此转念一想,我更觉得和这个藤井贤一再谈下去已经有对死者不敬的意思了,便不耐烦地说:“你对这种题材有兴趣,请胡导演可能是找错了人,跟我谈更是浪费时间。”一面说,我一面朝庭院走去。
不料这小个子一窜身横在我面前,一面伸手从上衣内袋里掏出一方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米白色信笺——一看就是胡金铨上一次参加东京影展时在神保町买到的宝贝,之后他再回到寄居的加州帕萨迪纳,给老朋友写信,总爱用这种仿毛泰纸的日制洒金笺。
洒金笺抖擞开,上头是寥寥几行:
贤一吾兄鉴:前信言及“扮皇帝”事,须从辛亥前后革命实务考察入手,非有具体之思维,不可得故事。弟即将赴台作心导管手术,谅能一晤。弟抵台北后再约大春,若能与兄见面详谈,可望于农历年前打定初步预算。金铨。十一月二十三日。
胡金铨是老派人,不大用新式标点,所以引号“”很可能就代表着书名号《》——换言之,就是作品的意思。如果说“扮皇帝”是《扮皇帝》,那么,这会是一部筹拍中的电影吗?而另一个引人遐思之处是:明代正德皇帝的风流故事,老早就被一年前故去的李翰祥拍成了一部黄梅调电影《江山美人》,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若说胡导演真要重拍此片,会是带着一种追怀故人的心情而为之的吗?这难道是他另一个没有来得及实现的梦想吗?
信的确是胡金铨导演的亲笔,看信末所署日期,是他回国前不久写的——甚至还可能是大导演在人世间留下的最后一封信函。
然而令我吃惊的是那引号里的三个字:扮皇帝。“扮”字写得很含糊,又像“换”字;提手偏旁涂改过,又像是“火”字偏旁的“焕”字。说他写的是“扮皇帝”,乃基于《江山美人》而显得顺理成章,理解起来并无不妥。若说原文其实是“换皇帝”,用来旁注于民国新成之时,袁世凯暗存复辟思想,后来还果然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随即“龙驭上宾”,虽说是闹剧一场,但是与藤井贤一所说的什么《窃国风云》啦、《护国记》啦,之类的名称,倒也理路一贯。
至于“焕皇帝”,不但不为荒唐错谬,“焕皇帝”还真有其人!而且,这个“焕皇帝”还真和“辛亥前后革命实务”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