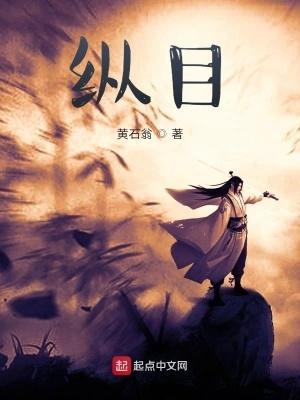奇书网>年轻人最喜欢的茶 > 谷雨(第2页)
谷雨(第2页)
在隋唐时,宫廷以紫色为尊贵。唐齐已《寄情曾口寺文英大师》有诗为证:“着紫袈裟名已贵,吟红菡萏价兼高。”但到了明代,因为皇帝是朱姓,所以官服和宫内的帐幔,禁止使用紫色。敏感多疑的朱元璋,是否因了孔子《论语》里“恶紫之夺朱也”这句话,而废掉紫笋贡茶呢?当然,我也只是猜测。但在尊儒崇佛的明代,孔子的话是有相当分量的。朱元璋和孔子的论调应该是一致的,他们厌恶和不希望紫色代替朱色而成为正色,因此紫色的物品,包括紫笋茶,因为有了“紫”字,而不受皇家待见,这是有道理的。在清代,反清复明的文人,曾骂满清王朝是“夺朱非正色,异姓尽称王”。废掉作为饮品的紫笋茶,与朱姓皇家政权的合法和稳定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带着对紫笋茶的思考,我走进了顾渚山的古贡茶园。茶园被遮天蔽日的毛竹包围着、覆盖着,半人高的古茶树,丛丛簇簇,自由散漫地生长在沟壑边、竹根旁、碎石间,与杂草藤蔓混生错杂着。不规则的茶园边,涧流潺潺。古茶山的松风幽径、迤逦气韵,也只有用张旭的诗来形容了:“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轻阴便拟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千百年来,隐迹于翠竹幽篁、甘泉流淙的竹木丛林中的古茶树,其环境、植被、土壤等,确实高度契合陆羽《茶经》对紫笋茶“上者生烂石”,“野者上”,“阳崖阴林”,“紫者上”,“笋者上”,“叶卷上”的记述。
这些古老的紫笋茶,目前主要分布在顾渚村的桑坞岕、高坞岕、竹坞岕、狮坞岕、斫射山一带。我仔细观察,古茶园的野生紫笋茶,基本生长在山之阳、烂石上、溪涧畔、竹林中,茶树高低粗细大小不一,茶树的根部丛生着野草杂花,腐殖土疏松肥沃。再看,那些留着雾气水滴的茶树,新芽肥硕,芽头比第一叶长出许多。刚刚萌发的芽头,呈春笋状,嫩叶被卷着。另外,紫笋所谓的紫,并非现代人认为的单纯紫色。我穿行于古茶园,从数千株紫笋野茶中,去观察辨别紫笋茶的紫。我发现紫笋茶的紫,是专指如新笋状的芽头,而不是指叶片。那种紫,应是淡淡的粉红里透出的微微紫韵。等新芽发出的第一个叶片绽开后,芽头呈现的紫色会逐渐消褪,不再明显,此时的一芽一叶,开始呈现正常的淡绿色。
紫笋茶新萌发出的笋芽的紫韵,既不像西湖龙井的群体种,在强光下变异后,出现芽叶永不褪去的紫红色;也不像云南高原上浓妆艳抹的紫芽和紫鹃,呈现的那种浓浓的深紫色。顾渚紫笋的紫,是一种含蕴着诗意变化的品种特征,并非是花青素在阳光下合成过多而产生的紫色。另外,花青素含量高的紫色茶,滋味苦涩,过于浓强刺激,是不适合做贡茶的。
冠于他境的紫笋茶,因为茶圣陆羽的推荐,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贡茶。生态优美的顾渚山,又因产贡茶而闻名天下。又因为茶,仅唐代就有二十八位刺史被吸引到顾渚山,其中有我们熟悉的颜真卿、皎然、张文规、皮日休、陆龟蒙、杜牧、白居易、刘禹锡、苏轼、陆游等等。可见茶的诗意与清香魅力之大。
张大复在《梅花笔谈》里描述紫笋:“松萝之香馥馥,庙后之味闲闲,顾渚扑人鼻孔,齿颊都异,久而不忘。”由此看出,张大复认为紫笋茶在明代是好过松萝和岕茶的。过去的紫笋茶如何迷人,我只能艳羡于古人的描述,已无法亲自体会。如今,我在古茶园看到的紫笋茶,已经革新为烘青绿茶了,但香气依然清冽幽微,能与醍醐甘露抗衡。
千古清芬,绵绵余韵的紫笋茶,而今已成过眼云烟。时至今日,紫笋青芽谁得识?但茶仍然是茶,不失本分。春来发几枝,清香犹在,妙韵永存。节同时异,茶是人非,历史若无轮回流转,贵为贡茶曼妙的紫笋,怎会是我杯中的一片绿,心中的一抹香呢?
今年的霜降,我又一次从顾渚山前走过,在大唐贡茶院的清风亭前,与双且、老崔、都雪等友,用金沙泉的泉水,瀹泡我在古茶山亲自采摘、亲自手工炒青的紫笋茶,清甜香幽,水滑汤厚,真是应了汪士慎的诗句:“共对幽窗吸白云,令人六腑皆清芬。”不过,良辰美景再让人留恋,此时的茶、水、人、景、物,都是充满禅意的一期一会。
·安吉茶山又逢君
和郑雯嫣长兴别过,我与大茶、沁慧师妹一起去安吉问茶。
安吉是一个古老的城市,建县于公元185年,是由汉灵帝赐名,取《诗经》“安且吉兮”之意。我最早知道安吉,是看了李安的电影《卧虎藏龙》,影片中那片碧绿无垠的波澜竹海,让我对竹林掩映的安吉充满着期待。
雨雾中,我们先到了溪龙的白茶园,一碧万顷的茶山,山势葱茏起伏。沁慧指着茶园中白墙黛瓦的别墅告诉我,那是电视剧《如意》中的谭家大院,那个位置就是号称白茶第一村的黄杜村。《如意》我没看过,听说是一个充满茶香的爱情故事。
茶园的空气新鲜,我深吸一口,甜丝丝的凉润。眼底雾气中的茶芽,清灵娇黄。金黄嫩白的叶片上,叶脉如翡翠的翠根渐变散布。芽翠如花,叶白如玉。放眼远处,娇黄的油菜花,一片片地盛开,鲜亮的色彩与茶山的翠绿,自然混搭得美丽无双。薄雾中连绵起伏的山峦,有几枝水红桃花掩映在山脚,像吴昌硕先生洇湿的丹青写意。这片茶山,那片桃花,墨痕深处,是昌硕老人熟稔的故乡情深。
我离开溪龙茶山,去恒盛茶厂找大锁兄喝茶。见面拿出的招待茶,是级别较高的天目御白和头采的安吉白茶。一滴水茶馆的钱馆主说过,用月白色的龙泉青瓷杯冲泡安吉白茶,最能表现出白茶的玉色娇白。当然,也可用玻璃杯,以观杯中的妙曼茶舞。
明前的安吉白茶,色调青黄,不似后期的翠白,但比后期的茶要香细清甜。安吉白茶,特有的芽形、稀有的兰蕙香和鲜爽香,常让我想到深山的淡竹掩雪,幽谷里的竹影娑婆。可以不夸张地说,安吉白茶是绿茶中最有诗意、最具娇色的茶。
不久,大锁拿来新做出的茶让我品饮。我看着干茶的卷曲玲珑,黄白隐翠,心生欢喜。细嗅干茶,甜馨的兰花香浓。便问大锁兄,此茶有多少?大锁兄说第一天做了八斤半,明天能做四十余斤。我贪心又起,笑着说:“茶色如玉,其香若兰,其味似乳,其形蜷曲,白中泛金,翠中有韵,取名叫玉玲珑吧!另外,这两天的茶我全要了。”大锁顿时面露喜色。我心中明白,辛苦踏实的做茶人,当茶的品质被人迅速认可时,是最感幸福和欣慰的。
我取玉玲珑三克,用中投法。即先在杯子里倒三分之一的水,投茶后,再向杯子里注水至合适的位置。沸水杯泡,茶汤入口,果然令人惊艳,回甘甜润,香气若兰,似玉米蛋花汤的细腻醇鲜。观杯中叶游水中,翠白隐绿。品啜可口,赏鉴悦目。等茶汤凉了,冷品水香清远,颇有韵味。在和大锁的交谈中,我得知玉玲珑的制作,采用了传统的滚筒杀青工艺。
今春的安吉白茶,前期遭遇阴雨连绵,茶青含水率高,如采用白茶的常规萎凋、机械杀青、理条、干燥等烘青工艺,做出的白茶青气重,茶汤的苦涩味显。而玉玲珑采用了滚筒高温杀青,茶青的叶张杀得透彻,低沸点的青草味物质能够全部挥发出来。并且在瞬间高温杀青后,干茶自然卷曲似螺,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茶的原色,保持了鲜香的茶氨酸等物质不被破坏。
下午,在恒盛的茶室,我接受了《浙江壹周刊》问茶栏目的采访。我高度赞赏了玉玲珑的传统工艺。我说,玉玲珑是迟暮的白茶市场上,升起的一道绚烂的彩虹,是白茶市场上同质化剧烈竞争突围中的亮剑。一款未来有所期待的新茶品,一定是靠近传统的创新,也是继承优秀工艺基础上的厚积薄发。像这款玉玲珑,既能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茶中呈味物质的鲜美,又因为敢于高温杀青,久饮不会过于寒凉而伤胃肠,所以才会受到市场的欢迎和追捧。
相对于市场的某些创新茶,过于注重外观秀美和颜色翠绿,工艺上采用了低温杀青。为掩盖低温杀青造成的青气和苦涩,又采用了高温干燥提香的工艺。这种干茶的外观翠绿养眼,干茶香高,但瀹泡后就会原形毕露,苦涩汤绿有青气。久饮寒凉肠胃,身体便会不舒服。
茶是用心喝的,不只是用眼看的。好的口感与翠绿鲜艳的干茶外观,正如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好事不必苛求成双,不完美才是人生的真实。此岸与彼岸的风景各异,如何正确地选择决断,是考验内心究竟需要什么的智慧。人间正道是沧桑,茶也如此,一款有传承的有底蕴的佳茗,是会脉脉而语的,就看我们能不能听得懂。
玉玲珑的干茶外观
安吉白茶,其实是白叶茶,是一种珍罕的低温敏感型变异茶种,其阈值约在摄氏23℃。以原产地安吉为例,春季低温,因叶绿素的缺失,在清明前萌发的嫩芽为白色。在谷雨前颜色渐淡,多数呈玉白色。谷雨后到夏至前,逐渐转为白绿相间的花叶。到夏至,芽叶恢复为全绿,与一般绿茶无异。
安吉白茶属于绿茶,是因为采用了绿茶烘青的加工工艺。真正的传统白茶,像白牡丹、白毫银针,采用的是不炒不揉、萎凋干燥、轻微发酵的白茶工艺,其白在毫。武夷岩茶中,还有一种滋味清美的白叶茶,叫白鸡冠,已经是乌龙茶的范畴了。
安吉白茶,高氨低酚,香高味鲜。冲泡似片片翡翠起舞,表里昭澈,又如玉之在璞。饮此茶,我常想起有“凌波仙子”美誉的水仙花。二者都具仙骨,清寒雅致。借水而开时,香远益清。那“水中花”淡雅的可让人没有欲望,倒有在花下安眠的心思了。细究起来,也只有《红楼梦》中的史湘云,能安然地头枕落花囊,卧于落花雨下了。
安吉白茶,淡洁清雅,如花似玉,是我见到的最清丽脱俗的茶。它可远观,可静赏,有兰之幽,而少孤傲。似梅之洁,却无清寒。一如从西子湖畔、断桥残垣走来的白娘子,衣袂飘飘,凌波微步。
初识安吉白茶,微醺仙风道骨,妙得淡中滋味,安且吉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