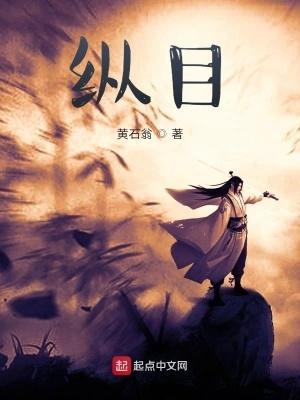奇书网>紫禁城的黄昏英文版 > 第二十二章 颐和园(第1页)
第二十二章 颐和园(第1页)
第二十二章颐和园
我们应该永远记着,在“优待条件”中有这样一条,虽然朝廷可以暂时继续留在紫禁城,但清朝皇帝的永久居所是颐和园。外国人把皇室的这个乡间居所称为夏宫。
从我担任帝师的第一年起,就不断提请王公、内务府以及皇帝本人,要注意这一条款,敦促他们主动履行。我之所以赞成自愿退居颐和园的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到目前为止,民国履行这些条款规定义务的方式仍有诸多不足之处,皇室却不能以此为由不遵守契约。确实,除了袁世凯,民国还未正式要求皇帝履行第三条,从紫禁城搬到颐和园去。而且,只要皇帝不直截了当地拒绝履行该条款,他便不可能被判定违约。然而,他“暂居”紫禁城的时间已经延长至12年(1923年底)了,而且皇室还没有表现出任何搬迁的意向。这很容易成为一个严重的投诉理由,成为指控皇帝的依据,即他即便没有在文字上违约,但在精神层面他已经违反了退位协议。那些希望协议取消的人(他们中有一大批是非常活跃且恶毒的反满政治家,还有越**动的学生),自然会乐意把取消协议的责任从他们自己身上转移到皇帝身上。如果皇帝不迁到颐和园,而他们又找不到更好的证据来证明皇帝不遵守协议,那么毫无疑问,他们定会利用这一事实来发难,宣布协议无效是合情合理的。
其次,我认为满族宫廷在颐和园的生活方式一直比在紫禁城简单得多,所以搬过去就有可能大幅度削减开支,甚至能给皇帝积累一些储备金,几年后就足以使他不再依靠目前不稳定的收入来度日。迁居过去,还可以大幅裁减服侍人员,并会出现撤销闲职的绝佳机会。
这一论点直击要害,朝廷官员及其同党极为反感。1923年,我记得我曾就这个问题与耆龄进行过一次长谈。他反对皇帝迁入颐和园,主要理由是那里的居住面积太小,无法满足内务府官员的需要。当我指出颐和园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皇室、所有的朝廷官员和仆人时,我遭到的只是断然拒绝。他认为,我所说的与皇帝搬迁的事情间没有任何关联。裁减现有工作人员的做法是不可行、不可取的。我建议大幅削减朝廷开支,这样就有可能积累一笔财政储备,供皇帝在不久或很遥远的将来陷入困境时使用,但他对我的这一建议也丝毫不感兴趣。
我经常和耆龄的同事们讨论这些问题,他们的态度和他如出一辙。他们的国君可能会陷入绝望的陨灭和悲剧中,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用自己的饭碗把他从灾难中救出来。裁减工作人员、薪金或额外津贴,取消闲职,以及撤回迄今为止一直用于维持一个庞大而毫无用处的机构的资金,都将遇到他们的愤怒阻击。而这些只在嘴上忠于皇帝的人,必将不惜一切代价地予以抵制。
除了皇帝身上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利益外,他们对皇帝的命运漠不关心。我也就不指望他们会注意到我的第三个主要论点了,即换个生活环境对皇帝的身心健康非常有利。在这一点上,我很难想象会有多大的分歧。一个人,但凡知道皇帝从小到大生活的紫禁城有多么不利于健康,意识到他在颐和园工作和玩耍的气氛又多么有益健康,在选择这两处哪一个更适合他安家的时候,是不会犹豫的。在我看来,当张勋(无疑是在许多利害关系人的迫切请求下)劝阻袁世凯不要要求皇帝迁去颐和园时,他的忠诚用错了地方。而皇帝接受并利用张勋的干预,同样也是错误的。
内务府对皇帝迁入颐和园的想法持有强烈的敌意,他们想尽办法发挥所有的影响力,阻止皇帝去颐和园,甚至连去那里看看都不行。他们想让皇帝相信,颐和园已经破败不堪,根本入不了皇帝的眼,更不用提居住了。他们还断言颐和园附近有大批强盗出没,如果皇帝离开城区那么远,他的生命就有危险了。这些威胁如果不是来自土匪,那么就是来自政治阴谋家,或者是来自那些“爱国者”。他们认为只要皇帝还活着,就会对民国构成威胁。
在我看来,让皇帝尽可能长久地留在紫禁城,正当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把这么多的珍宝和价值连城的艺术品搬到颐和园去不太现实,而如果把它们留在紫禁城,就意味着它们会立即被民国当局查收。我同意,如果这些珍宝留在紫禁城,皇帝可能就再也见不到它们了。他的所有权可能会引起争议,或者更有可能被忽视。然而,在我看来,所有权的问题应该彻底解决清楚。如果皇室对紫禁城的珍宝把持得太紧、太久,皇族最终将被强制剥夺所有东西,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可能性越来越大。然而,如果皇室表现出妥协的意愿,主动建议委任一个联合调查委员会,把那些可以合理视为国宝的物品分配给民国,那么皇室就可以在毫无争议的情况下占有剩余的。
郑孝胥被任命为内务府总管,这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并进行了比以前更充分的讨论。我很欣慰地发现,虽然他和我在一些细枝末节上意见不同,但在总的原则上是一致的。他同意我的意见,认为应该做好准备,履行“优待条件”的第3条,让皇帝自愿迁入颐和园。但他坚决认为,筹备工作需要一些时日。而且,首先应该改革和重组颐和园及其周边广阔土地(包括一些耕地和玉泉山一带)的管理工作,将数量庞大而无用的工作人员削减至可管理的范围,还要对颐和园进行一些修葺和改建,并有序安排宫廷的财产。
到目前为止,颐和园一直由内务府管理。现在,郑孝胥向皇帝举荐,任命我做钦差大臣,全权负责颐和园各项事宜,并直接向皇帝本人汇报。因此,1924年初内务府受到严重打击,这可与此前废除宦官制度、任命汉人为内务府总管相比了。他们竟然被置于汉人的统治之下,这在大清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他们看来这糟糕透了。现在更糟糕的来了,相当一部分宫廷管理权将完全脱离他们的掌控,落入一个西方野蛮人的手中。也许最苦的部分,是我的任命圣旨必须经由内务府传达给我。下面是这份前所未有的文件原文:
内务府信笺
敬启者本日总管内务府大臣面奉谕旨:著派庄士敦管理颐和园、静明园、玉泉山事务,钦此!用特肃函奉闻,即希遵照可也。专此藉送时绥。
内务府启
内务府体验了祸不单行的痛苦。颁发这道圣旨的第二天,又有一道霹雳落在他们中间。在与我进行了简短磋商后,皇帝宣布他和皇后打算当天对颐和园进行首次参观。他命令准备好他和皇后的车,两小时后出发。此前,皇帝最远的旅程是到达父亲的住所,即位于京城北部的北府。他从未走出过北京的城墙。内务府说尽了所有可能发生的祸事,诱使他改变主意,但皇帝不为所动。这时,名义上的内务府总管邵英请求我劝阻陛下不要进行这一鲁莽的冒险。我回答说,我完全赞成这次冒险。他怒火冲天,威胁我说,如果皇帝陛下受到任何伤害,我将负全责。对此,我唯一的回答是,这个责任我乐于承担。
内务府致庄士敦函
内务府仍不甘心,继而同民国政府进行沟通,希望他们驳回皇帝去颐和园的计划。他们的这个打算也未能得逞。只是,民国当局派了一支由六辆汽车组成的“护卫队”,护送皇帝进行他大胆的旅程。毫无疑问,民国此举是为了确保皇帝不会在中途突然改变目的地,去参观使馆区而不是颐和园。内务府另外租了六辆车供自己使用,其中包括绍英本人。就这样,我们便在预定的时间从神武门出发了。我们排成了一个十四辆车的车队,我和皇帝坐在领头的车里,后面跟着皇后和淑妃的车。
撇开内务府,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这次冒险都相当成功。皇帝初次到乡下,更是第一次来到颐和园,他非常开心。园子本身并没有变成废墟,远远高出了他的预期。他满心欢喜,在园中漫步,在许多分散的建筑物间穿梭。皇帝游览了一座座亭台阁楼,又登上了万寿山顶。之后,我们上了一艘船,皇后、淑妃和侍女们乘另一艘船紧随其后,去探访龙王岛,那里可是颐和园的一颗明珠。
就在同一天,我正式走上了新岗位,与众多颐和园的官员进行了初步面谈。他们当中有许多官阶很高的人,现在都成了我的直接下属。从那时起,我的时间几乎全在紫禁城和颐和园里度过了,只是偶尔去我的四处居所之一的樱桃沟待一会儿,那里最能让我心情愉悦。从那以后,皇帝频繁地出入颐和园,每次都有官员和士兵组成的车队陪伴,但这样的安排纯属多余,还要花费钱财。有时,他作为我的客人,在颐和园同我共进午餐。就这样,他结识了我的许多外国朋友和一些谨慎挑选出来的中国人。
1924年8月,我陪他第一次在山间漫步。他参观了西山山坡上的八大处寺庙群,其中一座是他的先祖乾隆帝最喜欢去的地方。
颐和园中的昆明湖里泊着的船个个都很笨重。置办的这些船本来是给慈禧老佛爷和她的太监们使用的,所以对于一个想学划船的年轻皇帝来说,几乎没多大用处。当然,对于我这个打算教皇帝划船的外国人来说也是一样。为了皇帝的利益,也为了我自己,我分别在天津、烟台和上海建造了三艘船。一只带有滑动座椅的舷外支架,我给它起名“爱丽儿”。另一艘是有固定座位的小划艇,名字叫“阿特拉斯的女巫”。第三只是个独木舟,当时已经完工,只是还未送至紫禁城。但1924年11月发生的事让我在颐和园的职务走到了头。“爱丽儿”和“女巫”,尤其是前者,在宫里的工作人员中引起了极大的惊奇,他们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的船。起初,当他们看到天子完全可以把划船这种辛苦而卑贱的工作交给水手,却偏偏自己动手时,他们的惊奇中又带着一丝恐惧。
由于我可以自由选择在颐和园的住处,便首选了龙王岛。但我发现这个宜人的地方不适合处理公务,就搬到了一个僻静的花园。四周围墙环绕,有亭台楼阁,还有一条小溪潺潺流过,这处美妙的隐居叫“湛清轩”,它是与之风格相似的“谐趣园”的一部分。
尽管我的办公环境十分宜人,但我所从事的工作却很艰难,我很少能从中感到“和谐的快乐”。有些人总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新人新政”威胁,我与他们的关系也是一言难尽。我在北京的一些欧洲朋友祝贺我可以把爱好当工作了,但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份工作有多乏味,我每天要遭受多少嫉妒和敌视,我每次尝试改革中国宫廷管理体制的固有弊端,人们会多么愤怒地反对。宫廷官员表面上彬彬有礼,但对我的实际帮助却很少,尤其是在我完成一项极其棘手的任务时,即通过裁员和调整薪俸来削减开支。在夏天,一位宫廷要员去世了,我很快就收到了许多关于晋升的推荐信。当我宣布这个职位纯属多余、将被取消时,大家公开表示了对我的厌恶。
关于不同建筑的修缮问题,我提出的方案同样遭到了坚决反对。他们给我提了附近海淀村两个承包商的名字,并向我保证,在过去的许多年里,颐和园的修葺工作都是委托他们完成的。我向这两个人询问价格时,结果高得出奇。于是,我便在北京城秘密投标找承包商。这一操作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以至于中国报界都进行了评论。结果,这项工作得以有效完成,所需费用还不到那两个承包商报价的七分之一,而我的下属还曾试图说服我他们的报价是合理的。
渐渐地,我成功说服了几位比较有头脑的下属,使他们相信改革和紧缩政策是有可取之处的。我们应该尽己所能为皇上服务,这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对我正在做的工作产生了兴趣,开始与我合作。成功来得没有我希望的那么快,但在夏天结束前,我对结果已经很满意了。颐和园过去一直都在大量消耗皇帝的资金,现在它可以自给自足了。收入来源包括农田租金,颐和园和玉泉山的开放日门票收入,出售湖里的鱼,以及当地某些企业的利润分成,如玉泉山上的一家酒店、一家苏打水厂、几家茶馆和一家摄影店。
这帮人不择手段地想让我辞职的行为略显幼稚。1924年,我收到了许多恐吓信,其中有一封据说是出自某个对我极为尊敬的人之手,他认为有责任警告我,有人要谋害我的性命。有人雇了一帮土匪,准备在我往返紫禁城和颐和园的途中(我通常骑马)枪杀我。事实证明,这帮土匪肯定是些笨手笨脚、优柔寡断的家伙,根本不够资格。因为我骑马往返颐和园的次数太多了,可他们一次都没有利用好。
我所承受的反对和敌意,不仅源自紫禁城里内务府和颐和园里那群无用食客的嫉妒,更有来自新闻界由学生把持的某些报纸刊物。那个时期关心政治的学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与苏联大使馆有密切联系的极端激进政治家的影响。代表他们观点的报纸欢迎任何攻击“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国报纸)或皇帝(他们总是轻蔑地称之为“溥仪”)的机会。1924年,他们发现了许多一石二鸟的好机会。至于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下面这个例子便是很好的说明。
1924年9月初,北京一份叫《大晚报》的报纸登载了一段极其下流的话:据说,“溥仪”的英语老师动机不良,把自己的女儿带进了紫禁城,介绍给了“溥仪”。她很漂亮,“溥仪”都看呆了。英语老师出于某种考虑,便把她交给了“溥仪”。
即便是用英文写出来,这些话也是相当无礼的,原本的汉语措辞更是不堪入目。要是我认为有必要对皇帝和我自己受到的卑鄙指控做出回应,我可能会诉诸各种辩护的说辞。但其实只需说出一条便已足够,那就是我根本没有女儿。
胡适博士在给我的信中,表示了对北京新闻界竟能沦落到这类下贱的地步深表遗憾。1924年10月10日,他在信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