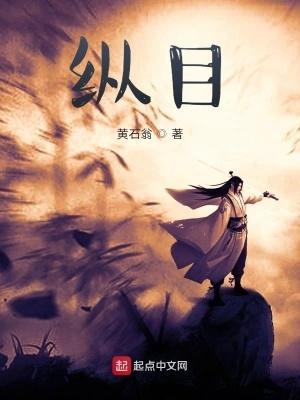奇书网>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 > 第二十四章 龙陷困境(第1页)
第二十四章 龙陷困境(第1页)
第二十四章龙陷困境
11月5日深夜,我回到家时,发现我的佣人们都很紧张。紫禁城里发生的惨事,他们或多或少听到了一些谣传,而我又很多天没有回家,他们便更加惊慌失措了。他们告诉我,警察和侦探全天严密监视着我的宅子,还把所有来拜访的中国人挡在了门外。后来我才知道,其中有位客人是我的朋友,名叫傅泾波,是来安慰我的。他一度非常担心我的人身安全,并一再提醒我随时可能坠入的险境。
如果这种危险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那很可能会在政变前的几个星期显现。现在皇帝被逐出紫禁城已是既成事实,曾被认为会阻碍政变的外籍帝师,已经不再构成威胁,因此取消其资格的主要原因已不复存在。但很快就有证据表明,我为皇帝寻求外交干预,却招致了人们的憎恨。6日早晨,我的车被拦在了醇亲王府的大门口,我得知自己被严禁入内。接下来的三个星期,我都没有见到皇帝。
起初,除我之外的所有人也被禁止出入北府。6日和7日两天,除了王爷的几位家庭成员,其他人一概不许出入北府。之后,我的中国同事可以进出,郑孝胥和绍英也获准了,但针对我的禁令却始终没有放开。我的抗议只导致了一个结果:禁令限制的人员范围扩大到了所有外国人。
政变的主谋认为,他们本想说服全世界相信他们在紫禁城采取的行动不涉及武力或恐吓,但我让他们的这一希望破灭了,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希望世人相信皇帝没有受到任何身体或精神上的胁迫,是自愿离开紫禁城的,并为自己获得的自由而感到高兴,他们不择手段地买通中外媒体,试图通过他们向世人传达这种假象。他们不仅希望说服中外民众接受这种解释,还要对皇室及其追随者进行恐吓,让他们三缄其口。
结果,三位欧洲公使向“外交总长”王正延发出抗议和警告,致使这一精妙的计划遭到挫败。要说服中国政府相信冯玉祥的行动是出于对“紫禁城囚徒”的善意关注,或者是“囚徒”自己欢迎冯玉祥的士兵解放自己,这是不可能的。唯一相信这个版本的人是冯的一些传教士朋友,他们视冯为英雄,为维护其名声,极其不愿相信冯会违背基督教的原则。
古约翰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他是“原教旨主义”观点的福音传道者和复兴主义者。据说,古约翰先生听到有人说“基督将军”变红了,他立刻回答说:“是的,他被耶稣的血染红了。”但不久之后,由于在战争中惨败,这位“基督将军”去了莫斯科朝圣。据胡适博士说,他在那里的多数时间都在用毛笔画列宁。从那时起,传教士界对这位“基督将军”的热情便消失了。
新当局者小心翼翼地为自己对皇帝采取的行动寻找正当理由,声称正是冯玉祥和他的同僚及时采取行动,才把国家从保皇派的复辟行动中拯救了出来。鉴于不可能指责张作霖是这场政变的主谋,黑锅就只好由他的手下败将吴佩孚来背了。
以下是一个英国人在危机期间故意散布的臭名昭著的谎言。这篇文章发表在11月6日的《东方时报》上,也就是暴行发生的第二天。
一起复辟帝制的阴谋昨天下午在北京被挫败了,这起事件与两百年前欧洲发生的“快乐王子查理”事件一般无二。几个满族人及其追随者试图利用这个国家不稳定的局势,密谋让年轻的宣统回归,坐上名副其实的皇帝宝座。最后的细节还未曝光,比如登基仪式上要穿的服饰、优先权、授予朝臣的头衔和其他琐事…现在可以披露的是这场令人惊讶的谋划及其可能的内在原因。毫无疑问,吴佩孚如果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将自己视为皇帝的保护者,就会走上复辟的道路。某些细节非常奇怪,至今仍秘而不宣,足可以证明他有这方面的打算。
四天后,同一家报纸又刊登了以下信息。
内战前,是否有位高级特者被派往洛阳就复辟一事试探吴佩孚,满族人已经不再争辩了。人们认为吴佩孚的回复是十分鼓舞人心的,他向前皇帝宣统报告说,他肯定赞成这个想法,一切都要看事态的发展……这个城市是满洲人的天下,所以发生政变的可能性始终存在,这是谨慎的人不能忽视的。基于这些考虑,自11月1日起,他们小心行事,逐步包围了紫禁城,还用沙袋封堵了大门。这之后,清宫和传国玉玺的交接方才进行。
所有这些论断中,只有一个真相,任何一个有见地的中国人都不会忽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中有很多人士,欣然接受这种自称为民国的疯狂的政治结构的崩溃,他们欢迎重建一个中国人民可以真正理解的唯一的政府制度。虽然人们会注意到,面对张作霖,《东方时报》谨慎地保持低调。而此前,他对帝制的同情一直是公众议论的话题,远比议论他的对手要多得多。不过,吴佩孚和张作霖在本质上都算不上共和主义者,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要说皇帝个人参与了任何帝制复辟的阴谋,那都是一派胡言。拥护帝制的人向来小心谨慎,避免让他卷入阴谋。至于内务府,它小心翼翼地避免参与任何可能损害其自身利益的政治活动。
11月11日,《华北正报》发表社论,表达了外国人和中国人的共同观点。《东方时报》曾报道过帝制复辟阴谋的报道,“众所周知,这纯粹是一场骗局”。同样,11月17日的《京津泰晤士报》也写道:
所谓的帝制复辟阴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更不用说皇帝还牵涉其中。所谓的复辟阴谋完全是捏造出来的,其目的是为其肆无忌惮的暴行进行辩护。王正延先生使出浑身解数,也找不到任何合理的借口来撕毁退位条约。现在很明显,对皇帝进行事实监禁,是为了防止他公开否认那些暂时掌握首都大权的无耻之徒强加给他的协议。
这段话里提到了“退位协议”,并不是由于作者粗心大意误解了“优待条件”的性质。下面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摘自同一篇文章:
王先生对于把“退位协议”视为条约的想法嗤之以鼻。但段祺瑞元帅发过声明,如果皇帝接受他的条件,人民军队就“承诺”将这些条件交由海牙法庭进行登记。虽然段祺瑞给皇帝上的请愿书是促成皇帝退位的决定性因素。那么我们就要问一句,将不属于条约性质的协定在海牙法庭登记是否符合惯例?除了表明共和政府方面有意把“退位协议”上升到条约地位之外,有没有可能以其他方式来解释这一承诺?退位条件本身就表明,双方的意图是要达成一项有约束力的协议,只有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对其进行修改,而不是像眼前这样,由在北京暂时掌权的少数布尔什维克暴发户单方面修改。
我曾尝试证明两点:第一,起草“优待条件”的人根本不是以皇帝的福祉为宗;第二,袁世凯签署这些条款,不仅欺骗了皇室,也戏弄了共和派,但毫无疑问,我们是否认为这些条款的效力等同于一项条约,但在没有另一方的自愿同意的情况下,共和党和皇室都无权取消或修改这些条款。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方法得当,皇帝会欣然同意他们的修正案。但他们使用野蛮的暴力行径,凭借一个已经失去自由的总统带领的非法内阁炮制授权,单方面取消这一条件,根本就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据我所知,构成11月5日法案唯一权威的实际授权,从未以英文或中文公开过。作为一件历史珍品,它是值得保存的,而内务府总管交给我了一份副本。
这份授权表示命令是由曹锟总统下达的。他当时被软禁在自己的住所,抓捕他的人威胁他发布了他们认为合适的所有命令。命令指出,鹿钟麟和张璧“被派去谈判‘优待条件’的修订方案”,但没有说明修改的具体内容。根本就没有任何形式的“谈判”。这份体现“修订”条款的文件是由“内阁”准备并送进紫禁城的。内务府只是被告知,这份文件要替代1912年签署的“优待条件”。
这项指令声称得到以下“内阁”成员的支持:
总理黄郛
陆军总长李书城
司法总长张耀曾
财务总长王正延
外交总长王正延
内务总长(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