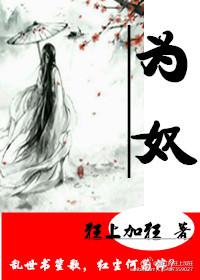奇书网>中国佛教史任继愈pdf > 第十四章 唐之诸宗02(第3页)
第十四章 唐之诸宗02(第3页)
此外《人天眼目》、《普灯录》、《五灯会元》、《五家正宗赞》、《续传灯录》、《会元续略》等书,尚说五家区别;《佛祖统记》、《佛祖通载》亦有此区别也。
此外临济宗有四料简或谓四宾主;即宾中宾,宾中主,主中宾,主中主是。三玄三要。三玄门:即体中玄,句中玄,玄中玄是。每一玄有三要门:即言前之旨珪,究竟直说智,及方便是。曹洞宗有洞山五位洞山五位,即正中偏,偏中正,正中来,偏中至,兼中到是。云门宗有八要。一玄,二从,三真要,四夺,五或,六过,七丧,八出。沩仰宗有九十六个圆相。南阳之忠,授之沩山,终传之仰山,遂成沩仰宗风云。法眼宗有天台德韶法眼之法嗣。之四料拣。即闻闻(放),闻不闻(收),不闻闻(明)。不闻不闻(暗)是。兹略之。
(五)密教
密教乃对于显教而言;凡释迦牟尼(应身佛)所说种种经典为显教;密教则为毗卢遮那佛(法身佛)直接所说之秘奥大法;其教理之组织,不易说明;与其谈理,毋宁崇实。盖密教自表面言之,则为祈祷宗;如何为佛?如何礼拜?如何崇奉?皆密教所注重者,可断其以仪式为主旨。其根本思想,虽不离乎佛教,然其实际,则凡作法礼拜崇奉诸事,合乎方法,即可成佛。推此理而广行之,必得佛神冥助,且有利益,此即所以为祈祷宗也。
密教特色,在事多神;其理论则以大实在为根据。但我国密教传来之初期,凡关于诸佛之供养、诸菩萨之礼拜、诸明王之真言、似杂然并传,无有系统。因而此等诸佛诸菩萨诸天善神等,皆认为实在。苟供养之仪式合法,则佛菩萨及神,必皆来集,听人请愿;故密教最重仪式。
密教所奉诸佛诸神,自婆罗门教转来者颇多;因之其礼拜供养之仪式,羼入婆罗门教风不少。故密教除经外,尚有仪轨;仪轨云者,依据经说,而示礼拜供养之实际仪式;此即密教与他教相异之点。密教除经律论三藏外,尚有仪轨藏。
(密教传入日本后,前后次序,颇加整理;并说明其理;俾实际易于行用;名之日次第。)
密教来华,当以西晋帛尸黎密多罗所译《大灌顶经》、《孔雀王经》为嚆矢(参看第二章)。然《经录》中载后汉失译者:有《安宅神咒经》(一卷)、《五龙咒毒经》(一卷)、《取血气神咒经》(一卷)、《咒贼咒法经》(一卷)、《七佛安宅神咒经》(一卷)。藏中现存者,仅《安宅神咒经》而已。唐代密教经典,翻译颇多;极古者以吴支谦所译《八吉祥神咒经》(一卷)、《无量门微密持经》(一卷)、《华积陀罗尼神咒经》(一卷)、《持句神咒经》(一卷)、《摩诃般若波罗密咒经》(一卷)、《七佛神咒经》(一卷)为最著。又东晋竺昙无兰所译者:有《陀邻钵咒经》(一卷)与上之《持句神咒经》,同本异译、《摩尼罗檀神咒经》(一卷)、《幻师跋陀罗神咒经》(一卷)、《七佛所结麻油术咒经》(一卷)、《大神母结誓咒经》(一卷)、《伊洹法愿神咒经》(一卷)、《解日厄神咒经》(一卷)、《六神名神咒经》(一卷)、《檀特罗麻油术神咒经》(一卷)、《麻油术咒经》(一卷)、《麻尼罗檀神咒按摩经》(一卷)、《医王惟娄延神咒经》(一卷)、《龙王咒水浴经》(一卷)、《十八龙王神咒经》(一卷)、《请雨经》(一卷)、《嚫水经》(一卷)、《幻师阿邹夷神咒经》(一卷)、《咒水经》(一卷)、《药咒经》(一卷)、《咒毒经》(一卷)、《咒时气病经》(一卷)、《咒小儿经》(一卷)、《咒齿经》(一卷)、《咒牙痛经》(一卷)、《咒眼痛经》(一卷)等。凡二十五部,皆密教经典也;然则昙无兰可谓在唐以前与密教关系最深之人矣。罗什尚译有《孔雀王咒经》(一卷)、《摩诃般若波罗密大明咒经》(一卷),其他译一二部密经之人或失译者,姑不具述。六朝末叶,陈阇那崛多所译密经甚多:《经录》所存者,则有《八佛名号经》(一卷)与《八吉祥神咒经》,同本异译、《不空羂索咒经》(一卷)、《十二佛名神咒经》(一卷)、《一向出生菩萨经》(一卷)与《无量门微密持经》,同本异译、《金刚场陀罗尼经》(一卷)、《如来方便善巧咒经》(一卷)、《东方最胜灯王如来经》(一卷)与《持句神咒经》,同本异译、《大法炬陀罗尼经》(二十卷)、《大威德陀罗尼经》(二十卷)、《五千五百佛名经》(八卷)等。唐时译密经最多者,为义净三藏;有《观自在菩萨如意心陀罗尼经》(一卷)、《曼殊室利菩萨咒藏中一字咒王经》(一卷)、《称赞如来功德神咒经》(一卷)、《大孔雀咒王经》(三卷)、《大金色孔雀王咒经》(一卷)、《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庄严王陀罗尼咒经》(一卷)、《香王菩萨陀罗尼咒经》(一卷)、《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二卷)、《疗痔病经》(一卷)等。就上所举观之:当唐善无畏、金刚智来传密宗之前密教经典之一部,中土业已广译。其中如《孔雀王经》,已译八遍;《尊胜陀罗尼》,已译五遍。此外显教经典中咒文陀罗尼,不遑枚举;其仅持诵密咒有不可思议之行,而与密教关系最深者,尚不乏其人;姑略之。
《释摩诃衍论》,相传为龙树菩萨所造;有谓为后人所伪托者,异说纷纷,莫衷一是。说者谓姚秦时筏提摩多曾译之;疑是新罗月忠所伪托,仅高丽《藏经》,加入藏中。纵此沦为姚秦时代所译出,我国释之者,无一人视为密教之书;其视为密教之书者,唯日本耳。故此书之翻译于我国密教上,无有关系。
自密教观之:佛教有理论实际二方面:经为理论,仪轨为实际。故有经则应有附随之仪轨;恰如婆罗门教《吠陀经》、有《曼荼罗》(赞诵);即有与此相当之不饶摩那(供牺法)同一理。婆罗门教梨俱吠陀,有《爱塔利亚》、《高希塔基》二种之不饶摩那;《夜柔吠陀》,有《胎梯利亚》、《谢塔婆塔》二种之不饶摩那;《沙磨吠陀》附属有八种之不饶摩那中以普饶达、谢特、维恩舍为最著名;《阿塔婆吠陀》有《果婆塔》不饶摩那是也。佛教之仪轨,虽非供牺法;然其礼拜供养之方式,与婆罗门之供牺法固相当,或且仿效婆罗门之法转化而出者也。然于事实上,佛教之仪轨,非必附随于各经;小乘全无;大乘有者,亦仅十之二三;例如《法华经》有《成就妙法莲华经王瑜珈观智仪轨经》(一卷)、《华严经》有《入法界品顿证毗卢遮那法身字轮瑜珈仪轨》(一卷)、《般若经》有《仁王般若经道场念诵仪轨》(一卷)之类是也。
无仪轨之诸经,造通用之作法以用之;日本密教,有为诸经通用之仪轨者。
诵咒祈神降魔等,婆罗门教,用之颇古。祈祷所用之曼荼罗,多有灵验。由祈祷文一变而信其言句文句有大不可思议之力,渐成神秘,终成陀罗尼。而此神秘的仪式作法,日渐复杂,进而至于《阿塔婆吠陀》;风尚所趋,遂开秘密佛教之端绪。故佛教虽无附随经文之仪轨;然别本之单纯咒文至多;因此深信其能攘恶鬼、免灾祸也。
又婆罗门教,以声音为一种神灵的而极重之:如声论派(婆罗门之一派)创声为常住不灭之说,可以为证。由此声在宗教的信仰上,遂发生一种关系:如“阿母”表湿婆神之声;“乌”字表毗修奴神等;文字声音,各有宗教的意义;终成由“阿”字母音以及一切子音,皆有深远之意味;推而极之,万神皆有表其神之声音文字矣。佛教密宗诸佛菩萨,皆有种子;一切声音,母音子音,共有宗教的深义者,其端盖发于婆罗门教无疑。佛教之述此声字者,则有《瑜珈金刚顶经》有不空译《释字母品》一卷、文殊问经字母品(一卷)不空译、《华严经》第七十六卷、入法界品、有不空译《入法界品四十二字观门》一卷。及《大庄严经》之《示书品》、《大日经》等。《大智度论》(四十八卷)在释《四念处品》中,亦举四十二字观,说明各字之意义。但《大智度论》、《华严经》等,唯以譬喻观文字之意义:例如阿字为一切法初不生;罗字为一切法离垢;波字为一切法第一义等;渐次观之:则此音声毕竟不可得;文字者,色法也;色法之文字,因身业而现;身业先有口业之音声;依此音声,立种种之名称,妄想分别;实则声音本依因缘而生;一时触耳,再闻不得;如斯由文字音声上,观诸法空不可得之理;谓为四十二字观。《华严经》则先观阿字本不生;以阿字之中,融摄其他四十一字之深义;次观伊字一切法根本不可得;亦融摄其他四十一字之深义于其中;如是四十二字各观,俱摄其他四十一字;观各字之玄义,互为不离融摄者,即所谓字轮观;由此以观华严之事事无碍之理者也。此等皆以文字为观法之譬喻观;而密宗则直视此文字为佛菩萨之代表,作种子观:例如观大日如来,先观道场坛上所现之大日种子,即阿字;次变大日之三摩耶形(译为本誓);即观变作五层塔;更一转而观尊形,即大日如来之像;即就种子、三摩耶形、尊形三段而观,乃密教观法之通轨。故密教之声字观,较《智度论》、《华严》之文字观,更进一步。三摩耶形者,为表佛菩萨誓愿之器物;最初本无何种深意;如湿婆等为破坏神之化身,手持武器;毗修奴等为保护神之化身,手多持花;乃自然感情上之表现耳;其后遂谓何神持何器,为何种意义;似乎所持之器有深意存焉者。此种思想,亦自婆罗门教之神,转入佛教者也。
密教除口诵之真言陀罗尼、观心之种子、三摩耶形、尊形外,尚有印契:以手指作种种之结,表种种之意义;此亦自婆罗门教转来者,所谓口真言、身印契、心观念,身口意一致,三密相应者也。印契即目帝罗,婆罗门教已有之;初为单纯动作,不过于祈天祷神攘魔时,口唱祈祷文,以手表哀愿意,或示驱逐意而已;后思其动作,如有神助;终遂以种种印契,寓种种之意矣。印契,非仅手指之形也;广言之,身之诸业,皆目帝罗也。《大日经义释》曰:“凡有所作,皆为利益,调快众生;随作施为,无不随顺佛之威仪;是故一切所有举动施为,无不是印也。”盖即此意。
密教所供多神,与婆罗门教诸神,杂然陈列,互相影响;即佛教带婆罗门教之风,其外形遂似婆罗门教也。如是聚诸佛诸菩萨,名为曼荼罗;此曼荼罗者,亦源于婆罗门教,然则婆罗门教风,迨转入于佛教乎?加之曼荼罗中,多有婆罗门教神转入于佛教者:例如胎藏界曼荼罗之外,金刚部诸神,来自婆罗门教,持明院之五尊中,除般若菩萨外,如不动、降三世、大威德、胜三世等忿怒尊,似为湿婆之化身也。
曼荼罗有二种区别:即善无畏三藏所传者,及金刚智三藏所传者是也。善无畏梵名戍婆揭罗僧诃,正译净师子,意译善无畏,中天竺人,唐玄宗开元四年,自西域由陆路来华,值唐代极盛之时。善无畏所译经中,最重要者,为《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七卷即《大日经》。及《苏婆呼童子经》三卷,即《密教律》,其《大毗卢遮那经》,乃应一行阿阇梨之请而译者;一行又将传自善无畏之言,解释此经,名之曰疏;即通称为《大疏》是也。此疏之中:于善无畏所传曼荼罗之事,加以详释;即世所称胎藏界曼荼罗是也。兹将今世所传胎藏曼荼罗之概要,示之如下。
按图、中台八叶院,以大日如来为中心;东方宝幢、南方开敷华、西方无量寿、北方天鼓雷音,此五佛也;东北弥勒、东南普贤、西南文殊、西北观音,此四菩萨也;合成九尊。遍知院七尊。观音院三十七尊。金刚手院三十三尊。持明院五尊,故又以持明院为五大院;所谓五尊者,即不动、降三世、般若菩萨、大威德、胜三世是也。释迦院三十九尊。文殊院二十五尊。除盖障院九尊。地藏院亦九尊。虚空藏院二十八尊。苏悉地院八尊。外金刚部院,四方各有一处,合成二百五尊。皆婆罗门教神也。
但此曼荼罗,与一行之说不合;殆善无畏所传,其后渐渐变化者耶?金刚智三藏,梵名跋日罗菩提,亦中天竺人;过南天竺,受摩赖耶国译名光明,一名秣罗矩吒,今印度南部东海岸,即沿马拉巴儿海岸之一国。王之保护,由海路履中土;时开元八年也;因称为南天竺人。其所译之经,以《金刚顶瑜珈中略出念诵法》(四卷)为最著名,即《金刚顶经》也。此经原有十万偈,今之所译,仅一部分耳。所传曼荼罗,即后世所称金刚界曼荼罗是也。
金刚界曼荼罗图
羯磨会以大日如来为中心,一千六十一尊。三摩耶会七十三尊。微细会亦有七十三尊。供养会尊数亦同。四印会十三尊。一印会即大日一尊。理趣会以金刚萨埵为中心,十七尊。降三世羯磨会七十七尊。降三世三摩耶会七十三尊。以上名九会曼荼罗;诸尊详数五百余。但《金刚顶经》之大本共有十八会;传于中国者,乃其略本;故仅传九会;一说大本为二十八会云。
曼荼罗虽从婆罗门教转入;以其内容言之:实包含佛教之根本思想;故中国密教,不得谓为有组织的教义;但从一方观之,则此曼荼罗,已足说明中国密教之教理;何则?曼荼罗以图示佛教之教理。其说明曼荼罗之处,即说明佛教教理之处也。唯图之所表示,为婆罗门教给与之方法;故不得不谓密教者,乃被婆罗门教之外装以施佛教者也。窃思善无畏、金刚智咸在中天竺之摩揭陀那烂陀寺,研究学问;故密教可谓由那烂陀寺佛教一转而成。然则金、胎两部曼荼罗之中央,为大日如来所在胎藏界八叶之中台,金刚界羯磨会之中心。四方为四佛所在胎藏界即宝幢、开敷华、无量寿、天鼓雷音是;金刚界即阿阙、宝生、阿弥陀、不空成是就;乃明法相宗之转识成智说,表现于图者也。即前五识转为成所作智羯磨部之不空成就;第六识转为妙观察智莲华部之阿弥陀;第七识转为平等性智宝部之宝生。第八识转为大圆镜智金刚部之阿閦。之说;以四识四智之说为组织者也。中央之大日如来,表示此四智根本,为宇宙之实在;当法相宗之所谓清净法界法相宗舍此四识,与清净法界,谓之五法。而法相宗以清净法界为法身;以成所作智为化身密教之不空成就,即释迦,所谓应化身;以其他三者为报身但此三智为法为报为应之说,我国法相宗,有异议焉。大日如来为法身,实为密教之所依据;若就彼此二者,互相参考,则此二宗之历史的关系颇深;且缘起的佛教与密教之关系,全在那烂陀寺佛教之连络;其故可推而知也。
第十六会,名无二平等瑜珈,于法界宫说;毗卢遮那佛,及诸菩萨、外金刚部等,各各说四种曼荼罗,具四印;此中说生死涅槃,世间出世间,自他平等无二;动心举目,声香味触,杂染思虑,住乱心皆无二;同真如法界,皆成一切佛身。
由此观之:胎藏界足当此十六会,可推而知也。
据又一说:大本金刚界曼荼罗,有二十八会;现所译者六会;然则今之九会曼荼罗云何?此乃以理趣会,降三世羯磨会,降三世三摩耶会,为后来所加者;而不空所译之《金刚顶经》,不出于六会。但自他一方言之:后加之三会,究在二十八会大本曼荼罗之中;除六品外,概括二十二会而为三会降三世羯磨、降三世三摩耶二会,概括十会;理趣会概聒其余十二会;故九会之中,已具二十八会全体者也。又以传于日本之曼荼罗言之:弘法大师所传,为此九会曼荼罗;台密之慈觉大师所传,单为羯磨会之曼荼罗。盖此羯磨之三十七尊,实为曼荼罗之根本;故虽属一会,而其理得包罗全体。即《十八会指归》所谓“瑜珈教十八会,或四千颂,或五千颂,或七千颂,都成十万颂;具五部四种曼荼罗、四印;具三十七尊、一一却具三十七,乃至一尊成三十七,亦具四曼荼罗四印;互相涉人,如帝释网珠,光明交映,展转无限”是也。
习俗相传,印度画曼荼罗于砂上,修法终则坏之,无画于纸帛者;又谓善无畏在印度,绘画现于空中;或谓金刚智既从龙智受两部曼荼罗者;而龙智南天铁塔所传之本,为绘曼荼罗,是印度早已有之;或谓不空自龙智所传之本,实似始于震旦;特彩色曼荼罗,经中早有此说。据日本所传,弘法大师之说:则彩色曼荼罗,当以惠果阿阇梨,传于弘法者为嚆矢。兹试就金刚界羯磨会三十七尊之事一言之:羯磨会曼荼罗,中央有五大月轮;其中轮之中台,为大日如来;从大日如来,现四佛于东西南北四方:东方为阿閦;南方为宝生;西方为阿弥陀;北方为不空成就;此五如来之四方,各有四菩萨;大日如来前,有金刚波罗密菩萨;右有宝波罗密菩萨;后有法波罗密菩萨;左有业波罗密菩萨。又阿閦如来前,有金刚萨堙;右有金刚王;左有金刚欲;后有金刚善哉菩萨;宝生如来前,有金刚宝;右有金刚光;左有金刚幢;后有金刚笑菩萨;阿弥陀如来前,有金刚法;右有金刚利;左有金刚因;后有金刚语菩萨;不空成就如来前,有金刚业;右有金刚护;左有金刚牙;后有金刚拳菩萨。以上五佛二十菩萨:加于此者,其内四供养:则有金刚嬉戏、金刚鬘、金刚歌、金刚舞四菩萨;外四供养:则有金刚焚香、金刚华、金刚灯、金刚涂香四菩萨;外加金刚钩、金刚索、金刚锁、金刚铃四摄菩萨,凡三十七尊。其外部别有外金刚部诸神;兹略之。
就密教相承之历史言之:所传怪奇之说极多;有谓善无畏与金刚智,同门受教;达摩掬多与龙智,同人异名。有谓《大日经》大本有十万偈;其次之大本有四千偈;略本有三千五百偈;中国所译,其略本也。又谓《金刚顶经》广本无量俱胝;其次之大本有十万偈;略本有四千偈;金刚智所译,亦其略本也。事载《金刚顶经义决》有三卷,今唯上卷存。盖此书乃金刚智之说,不空所记录者也。兹揭其说如下:
其中广相,根未有堪;此略瑜珈,西国得灌顶者,说授相付;而其广本亦不传之;其百千颂本,复是菩萨《大藏经》中次略也。其大经本,阿阇梨云:经夹广长如床,厚四五尺,有无量颂;在南天竺铁塔之中:佛灭度后,数百年间,无人能开此塔,以铁扉铁而封闭之。其中天竺国,佛法渐衰;时有大德,先诵持今大毗卢遮那真言;得毗卢遮那佛而现其身,及现多身;于虚空中,说此法门,及文字章句;次第令写讫即灭;即那《念诵法要》一卷是。时大德持诵成就,愿开此塔;于七日中,绕塔念诵;以白芥子七粒,打此塔门乃开;塔内诸神,一时踊怒,不令得入;唯见塔内,香灯光明,一丈二丈;名华宝盖,满中悬列;又闻赞声,赞此经王。时大德至心忏悔,发大誓愿,然后得入此塔中;入己,其塔寻闭;经于多日,赞此经王广本一遍,谓如食顷,得诸佛菩萨指授,所堪记持不忘;便令出塔,塔门还闭如故。尔时书写所记持法有百千颂;此经名《金刚顶经》者,菩萨大藏塔内广本绝世所无;塔内灯光明等,至今不灭;此经百千颂本,此国未有。
所谓大德者,乃龙猛,即龙树菩萨;此为密教有名南天铁塔谈之典据。弘法大师之《金刚顶经开题》有曰:“此经及《大日经》者,龙猛菩萨自南天铁塔中所诵出也。”又谓《大日经》出于铁塔,但此《金刚顶经义决》之文,无关于《大日经》,故弘法大师之说,殊无确据。真言宗之学者,则以此种种理解,无从探索。又《金刚顶经义决》述金刚智来华时,携百千颂本通谓十万偈本及略本而来;遇暴风于海上,船中物皆掷于海中,百千颂本亦失去;所持来者,仅有略本及《义决》而已。《大日经》有大本,一行之释屡述之。自《金刚顶经》之南天铁塔谈,有广本、大本、略本之说;略与《华严经》之龙宫谈此龙宫谈所载龙树菩萨之传说,与南天铁塔谈同。有广、大、上、中、下、略六本之说相似;或系不空摭《华严》所传之说;或系密教与《华严》有密切关系而然。盖不空解密教,往往取资于《华严》,观《指归》所引《华严》之文,可以明矣。
唐代密教之来,功归于善无畏、金刚智二人,其盛也,则借不空三藏之力。不空,北天竺人;南游阇婆国,遇金刚智,为其弟子,同履中土;年仅十六也。至二十八岁,金刚智入灭;遗命不空与弟子含光、慧等;于开元二十九年发中国,自锡兰入印度;留五年;携《大日经》、《金刚顶经》之大本,及其他诸部密教经典五百余部;具得指授口传;再还中土;时天宝五年也。不空所译经论,凡一百十部、一百四十三卷;《贞元释教录》。实玄奘以后一大翻译家也。但所传广本之《大日》、《金刚顶》,尚未全译;此外有《表制集》六巷,乃集不空表文,及天子批答而成者。代宗极重不空,因归依焉。永泰元年,赐特进试鸿胪卿,授大广智三藏之号;示疾之际,帝亲临其室;加开府仪同三司,封肃国公,赐食邑三千户;固辞不许;入寂后,帝废朝三日;其待遇不空,可谓优矣。
以事实言之:我国密教,殆无组织的理论之说明,而以实际的说明为主;盖《大日经》、《金刚顶经》,虽名为经,实异于常经,而以关于仪轨的实际的作法为多也。然就其间之学风说明之:则我国密教,自有二派区别:一为善无畏所传,一行阿阇梨继之;一行之《大日经疏》(二十卷),殆为密教最初之理论的解释书,在我国亦可称为唯一之善本。相传此书多记录善无畏之说,但其说明,近于天台之解释法,天台之意,未尝或离殆始终应用之。一行本属天台学者,故其趋向如是;谓《大日经》为实相的法门者,实自此始。一行又自金刚智受密教,其立足处则为天台。若不空则与之异;以大日为中心,而谓诸尊由之出生成为无量佛;其说乃是缘起的说相;其立足处在于《华严》之理论。盖不空亦非仅学金刚界;似与善无畏所传,稍异其趣。
一行、不空殁后,师资相承,彼此混杂,难以判别;然此二派潮流现尚存在之故,可以想像得之。一行、不空后,我国密教遂衰,著述流传者既少,《僧传》所载之人亦不多;但自传入日本后,乃极隆盛,至今不替;今就彼国东、台两密学者之传承,示其概要如下:
《表制集》(不空遗书)曰:“吾当代灌顶,三十余年,入坛授法弟子颇多;五部琢磨,成立八个;沦亡相次,唯有六人;其谁得之?则有金阁含光,新罗慧超,青龙惠果,崇福慧朗,保寿元皎,觉超。”海云血脉曰:“三藏和尚以此法付属含光阿阇梨等弟子五人:一含光、二慧朗、三昙贞、四觉超、五惠果。”
名下括弧内之金刚界,即传金刚界之谓;昙贞以外之人,皆由弘法大师所传血脉而增加者;此图可谓专为金刚智所传金刚界系统而设;独惠果自不空传两部,甚为可异。《表制集》以为五部琢磨之弟子;五部云者,即在金刚界曼荼罗中分为佛部(大日)、金刚部(阿閦)、宝部(宝生)、莲花部(阿弥陀)、羯磨部(不空)之谓;而以金刚界为限;足见金刚智、不空,纵传胎藏界,但此系统,不传于金刚界外之人。海云《血脉》谓善无畏、金刚智交换所传;东密等尚斥之;其所主张以金刚智已于印度自龙智受两部;不空受之,更于印度自龙智重受两部;是此血脉,应专属于金刚智所传金刚界之系统;惠果之传两部,别以善无畏所传受自玄超,决非由不空受胎藏界;是则密教似与金胎两部相并,方可谓之传两部也;两部名称之缘起,大概在惠果以后,当可置信。
惠果以后,金胎虽属并传,但据所传,二派已各异其趣。
(名上加△记号者,为此系统中出有二度以上之人;亦有上表所漏之人,因非重要,故从略。)
日本圆仁、圆珍、宗叡等东台诸家之人中国也,皆在唐末,俱为盛传密教而来;我国密宗之盛,可推而知;惜未几遭武宗会昌之厄,继以五代之战乱,学者著述,**然无存;纵使后来从事网罗,第废缺已多,末由考其状况。
日本密教中,台密、东密,其说大异;台密以胎藏界曼荼罗为果曼荼罗,以金刚界曼荼罗为因曼荼罗;东密反之;以胎藏界曼荼罗为因曼荼罗;以金刚界曼荼为果曼荼罗。又东密谓金胎两部大法;台密则谓此两部外,圆仁尚传来苏悉地法,称为三部大法;此苏悉地法,非弘法所传;在三部中,最为重要者也。因海云《血脉》载“玄超阿阇梨,复将大毗卢遮那大教王及苏悉地教,传付青龙寺东塔院惠果阿阇梨”等语;三部大法,即据以为证;此种议论今尚存于东、台两密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