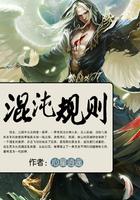奇书网>中国佛教史四大翻译家 > 第十六章 宋以后之佛教(第1页)
第十六章 宋以后之佛教(第1页)
第十六章宋以后之佛教
(一)概说
自武宗会昌之法难,继以五代之战乱,佛教之气运大衰。宋兴,佛教前途,欣欣向荣,如春花之怒发。盖宋太祖志在振兴文教,其于佛教亦然。建隆元年六月诏诸路寺院,经后周世宗时所废而未毁者不毁;既毁之寺,所遗留之佛像,亦命保存;且屡令书写金字银字之《藏经》;《释氏稽古略》称:“开宝元年,敕成都府造金银字之《藏经》各一藏。”又曰:“帝自用兵平列国,前后凡造金银字《佛经》数藏。”《佛祖统记》称开宝五年,诏京城名德玄超等,入大内,诵《金字大藏经》,帝亲临,并赐紫方袍云。所建之寺颇多。太宗虽信道教,亦未若视佛教之重也。
开宝四年,太祖遣张从信往益州成都雕《大藏经》,版成于太宗太平兴国八年,此实我国《大藏经》版之嚆矢。又印度西域之僧赍梵经来中土者,陆续不绝;国人之游历外国者亦多;翻译之业,以太宗时为最盛。至当时外人之来华者;太祖时,则有曼殊室利(中天竺人,与沙门建盛同来。)、可智、法见、真理、苏葛陀、弥罗(西天竺人)等。太宗时,则有法天、钵纳摩、护罗、法遇(中天竺人)、吉祥(西天竺人)、天息灾(迦湿弥罗人)、施护(乌填曩人,西北印度之一国)。此诸人中,以天息灾、施护、法天为最著名。
太平兴国五年,法天三藏始受命来京师;当以此时为译经之始。是年,天息灾(明教大师)、施护(显教大师)、法天(传教大师)、法护等诸三藏亦来,乃于太平兴国寺两,建译经院以居之,后赐名传法院;寺分三堂,中央为译经之所,东为润文之所,西为证义之所;法进、常谨、清沼诸人,充笔受缀文之役。是时天息灾定译经仪式,兹据《佛祖统记》所记者,列之于下:
于东堂面西,粉布圣坛;作坛以粉饰之;开四门,各一梵僧主之,持秘密咒七日夜;又设木坛,布圣贤名字轮,坛形正圆,层列佛大士天神名位,环绕其上,如车轮之状。目曰大法曼拿罗;请圣贤;阿伽沐浴,凡供养之器曰阿伽,此言沐浴之器。设香华灯水肴果之供;礼拜绕旋,所请冥祐,以殄魔障。第一译主,正坐面外,宣传梵文。第二证义,坐其左,与译主评量梵文。第三证文,坐其右,听译主高读梵文,以验差误。第四书字,梵学僧,审听梵文,书成华字。第五笔受,翻梵音成华言。第六缀文,回缀文字,使成句义。第七参译,参考两土文字,使无误。第八刊定,刊削冗长,定取句义。第九润文官,于僧众南向设位,参详润色;僧众日日沐浴,三衣坐具,威仪整肃;所须受用,悉从官给。
此时所译,皆入《藏经》。在译经院西偏建印经院;译毕,即在院开雕。又因天息灾等之请,选拔惟净以下童子十人,使在译经院习梵学;使译经业不至废绝。惟净未几为笔受,赐紫衣,及光梵大师称号;于梵语颇有发明,所译之书亦不少。太平兴国寺,本名龙兴寺;周世破佛,废为官仓;太祖复之;太宗改今名。
真宗时,外国僧来华者,则有法护(中天竺摩揭陀人),日称;仁宗时,则有智吉祥;其他则有契丹(辽)国师慈贤,或系摩揭陀人,但不能详耳。徽宗时之金总持,亦有二三译本。以上所举西域印度之人,于传无征者居多。真宗以后,来者尤众;因无关重要,故略之。
以《藏》中所存之经考之:法天所译,凡一百余部;以法天名译者,凡四十余部、七十余卷。以法贤(法贤学于中天竺摩揭陀那烂陀寺)名译者,凡七十余部、一百余卷。天息灾(北天竺惹烂驮啰人,惹烂驮啰,即迦湿弥罗。)所译,凡十九部、五十九卷。施护所译,凡百十余部、二百三十余卷。所译大小显密化制殆遍,龙树之书尤多。法护(谥普明慈觉传梵大师。)所译,凡十二部、一百余卷。我国人惟净等翻译亦不少,惟净所译五部、四十余卷。
太宗时,吴越王臣服于宋,赞宁随王入朝,赐号通慧大师。著有《高僧传三集》(三十卷)、《三教圣贤事迹》(一百卷)、《内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学集》(四十九卷)、《僧史略》(三卷)诸书。赞宁在吴越王下,为两浙僧统;入京之后,为左街讲经首座;后又奉命为右街僧录。
兹就宋世道教言之:太宗集天下《道经》七千卷,修治删正,写成三千三百三十七卷,赐各宫观。真宗之世选道士十人更详定之,增六百二十卷,共三千九百五十七卷,赐名《宝文统录》;冠以御制之序;此之谓《道藏》。宋世虽佛道二教并行,但遇有两教相毁訾之书,辄严禁出版;其制止两教之争,颇具苦心。
宋初以来,佛教之盛,既如上述。其间以天台山家、山外之争,为重要之事件。至于元照之《四分律》再兴。所受天台影响颇大也。
宋徽宗时,稍稍排佛;徽宗,北宋末之昏君也;极信道教,敬礼道士徐知常(赐号冲虚先生);此外,则徐守信、刘混康二人,亦有势力;后林灵素大博信用;帝自称教主道君皇帝;林灵素奏称天上有神霄玉清府,长生帝君主宰之;其弟青华帝君,皆玉帝子,下有左元仙伯以下八百余官;帝即长生大帝君,徽宗信之,故自称道君。造玉清昭阳宫(后改玉清神霄宫);置老子像,自为奉使;改天下之寺曰宫,改院为观,使安置长生青华帝君像;行千道会,每会殆费金数万缗。政和六年,诏于道箓院烧弃佛经。宣和元年,改呼佛为大觉金仙,菩萨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尼为女德士,皆使从道教之风;道士与德士,以徽章区别之;道冠有徽章,德士则无。命德士离寺,使道士入居之;盖徽宗固企图佛教与道教合而为一也。当是时:左街香积院之永道上书谏之;流于道州。翌年(宣和二年),复僧尼形服,去德士等称号,使复为僧。宣和七年,召还永道,赏其护法念笃,赐名法道;终赐号圆通法济大师。是徽宗排佛之举,为时极短;溯自宣和元年正月改佛菩萨号,翌年九月复旧:中间不过年余耳。
自宋兴以迄于亡,除徽宗稍稍排佛外,累代俱保护佛教。宋时,辽起于蒙古;辽衰,金起于满洲;此二国皆自北方,侵入我国本部。西则李元昊(西藏种之一,党项人)据有河西之地,建西夏国,窥宋西陲。而宋之内部,前则有王安石、司马光等新旧法之争;后则有秦桧、岳飞等和战之讧;谋国之论,殊不一致。徽钦而后,国步益艰;终至迁都临安。当是时,元太祖成吉思汗,铁木真,蒙古人。势颇强盛;自太宗(窝阔台)以至宪宗(蒙哥),领土日扩;东达朝鲜,西及小亚细亚一部;一军服俄罗斯地,一军进匈牙利,一军侵入德意志之西列西亚,夺我国扬子江以北之地,威力及西藏安南。至世祖忽必烈汗,全灭赵宋,一统华夏,国号曰元。
元世祖未即位前(即其兄宪宗时代),受命击西藏,即尊信西藏佛教(即喇嘛教);即位后,甚保护之;元代可谓为喇嘛教时代也。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谓道教书,皆后世伪造;除老子《道德经》而外,所有《道藏》,皆命烧弃;举凡毁谤佛教、偷窃佛语、贪财利、诳惑百姓之类,悉禁止;并刻石立碑,载其始末。此举实发端于宪宗之时,兹据《佛祖通载》述其次第于下:
乙卯间宪宗之五年,宋尚存;当宋理宗宝祐三年,迄至元十八年,殆为三十年前之事。道士丘处机、李志常等,毁西京天城夫子庙为文城观;毁灭释迦佛像、白玉观音、舍利宝塔,谋占梵刹四百八十二所;传袭王浮伪语,老子八十一化图,惑乱臣佐。时少林裕(福裕)长老,率师德诣阙陈奏。焚毁《道藏经》之碑文,载有罽宾大师兰麻、僧统福裕之名。先朝蒙哥皇帝(宪宗)玉音宣谕,登殿辩对化胡真伪,圣躬临朝亲证;李志常等义堕词屈,奉旨焚伪经;此时论议,帝师发思巴与道士难诘;焚伪经四十五部,亦见于碑文;罢道为僧者十七人;还佛寺三十七所;党占余寺,流弊益甚。丁巳秋(宪宗七年),少林裕长老复奏;续奉纶旨伪经再焚;僧复其业者二百三十七所。由乙卯而辛酉,凡九春(辛酉世祖即位之二年);而其徒窜匿,未悛邪说;谄行屏处,犹妄惊渎圣情;由是至元十八年冬,钦奉玉音,颁降天下,除《道德经》外,其余说谎经文,尽行烧毁;道士爱佛经者为僧,不为僧者,娶妻为民。当是时,江南释教都总统、永福杨大师琏真佳,大弘圣化。自至元二十二春,至二十四春凡三载,恢复佛寺三十余所;如四圣观者,昔孤山寺也。道士胡提点等,舍邪即正,罢道为僧者,奚啻七八百人云云。
由是观之:此种争执之大体可知矣。又焚弃道教伪经,宪宗之世,既已行之;其后尚实行数次;考其起因,实由于道教之徒,占领寺院,数侵佛教之范围;如孤山寺者,有名之伽蓝也,其时已化为道观矣。当时之道教,有正一教、真大教、太乙教,三派之别:正一教起自张道陵;其余二派,则始于金之道士:即真大教为刘德仁所唱;太乙教为萧抱真所唱;此等道教,至是皆受极大之打击。《辩伪录》(五卷)载《焚毁诸路伪道藏经之碑》,乃至元二十一年祥迈奉世祖敕所撰,专为破斥道教而设也。盖排佛之举,虽复见于明世宗之世;然在我国历史上观之:此次可称道佛二教争执之最后时期矣。
《佛祖通载》列此焚毁之《道藏经》书目,凡三十九部。又《辩伪录》载僧侣与道士论议者十七人,道士之归佛者十七人,所谓十七僧者:即燕京圆福寺从超、奉福寺德亨、药师院从伦、法宝寺圆胤、资圣寺至温、大名府明津、蓟州甘泉山本琏、上方寺道云、滦州开觉寺祥迈、北京传教寺了询、大名府法华寺庆规、龙门县行育、大都延寿寺道寿、仰山寺律主相叡、资福寺善朗、绛州唯识讲主祖珪、蜀川讲主元一是也。
元自世祖崩后,历七十余年而亡;盖世祖时代,蒙古极臻隆盛;殆世祖崩,元遂式微。其间喇嘛教,颇蒙保护;因保护之甚,酿成弊害;至于佛教史上,则别无显著之事迹。惟刘秉忠之历史,有足述焉:盖秉忠固助世祖立大功之人也。初蒙古都哈喇和林,世祖之时,移都燕京,建国号曰元;种种制度,多为秉忠所定。秉忠,本禅僧也;先是海云禅师应世祖之召,途次云中;闻秉忠博学多才,偕谒世祖,大合帝意;海云南还,秉忠奉命留侍左右,决大事者三十余年;官光禄大夫太保;死赠仪同三司太傅,封赵国公,谥文贞;秉忠虽位极人臣,尚斋居蔬食,终日淡然,无异平昔。
明太祖朱元璋,濠州人;少失两亲,入皇觉寺为僧。元末,各地豪杰并起,元璋亦起于濠州;随郭子兴,得其信任;终领其众而大兴;故即位后,颇保护佛教。不独佛教为然,即道儒二教,亦加保护。当时鉴于元末佛教流弊,以为不严重约束佛子之行为,则不得望佛教之兴隆,于是凡欲为僧者必考试经典,给度牒,不许任意出家;禁僧侣混杂俗人中生活,有带妻者,加以严惩;而鼓励避俗修禅山中者。于洪武二十七年,敕礼部榜示各条之中,一一举之。其文曰:“凡僧之处于市者,务要三十人以上,聚成一寺。”又曰:“僧有妻者,许诸人捶辱之;更索取钱钞,如无钞者,打死勿论。”又出榜文,张挂天下各寺;凡轻慢佛教,骂詈僧侣者处罚。
又为处理僧侣寺院(道教亦然)计,详定僧官之制;设僧道衙门,置僧录司、道录司,各任其官;品秩甚高,待遇优渥。大理寺卿李仕鲁屡上疏陈僧侣之跋扈,不采;仕鲁辞宫,帝怒而处之以死。兹将其时所设之僧官,举之于下:大体依据宋制。
僧录司,掌天下僧教事。(京师)
左善世(正六品)
右善世(正六品)
左阐教(从六品)
右阐教(从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