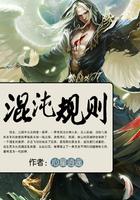奇书网>阴影中的爱百科 >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第2页)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第2页)
这样,日本人便完全抹杀了瑜伽在印度借以立足的前提。日本人极为酷爱“对事物的限制”就像古希腊人一样,因此它把瑜伽理解为使人完善的自我修养的方法,以及达到人与其行为之间“间不容发”的“练达”的手段。这是很有效率的自我依靠的修养方式。它的回报就在今世,因为它使人能在应付任何局面时都准确地作出不多不少、恰如其分的努力。他因此能控制本会反复无常的心神,并且外来的危险和内心的**都不会让他偏离正道。
当然,这种修养对武士和僧侣同样有益处,而且正是日本武士把禅宗变成了他们自己的宗教。无论在其他任何地方,你都很难发现有人会像日本人这样,用神秘主义的修行法来训练武士如何格斗,而不是用它来追求神秘的体验。然而从禅宗流行伊始就一直这样。12世纪,日本禅宗创始人就写了名为《兴禅护国论》的杰作,禅宗训练武士、政治家、击剑手和大学生去实现完全世俗的目标。正如查尔斯·艾利奥特爵士所说,在中国禅宗的历史中没有任何迹象让人想到,它在日本会成为军事训练的一种科目。“禅宗与茶道、能乐一样成了地道的日本货。这种神秘的冥想教义是叫人在直接体验中发现真理,而不是在经书中。因此人们可以料想,在12、13世纪这样的动乱时代,它会在逃避尘世的僧院中流行起来。但作为武士阶级所爱好的生活规则被接受是人们无法想象的,然而这却是事实。”
包括佛教与道教在内的日本许多教派都十分强调冥想、自我催眠和入定的神秘修行法。但是,其中有些宗派宣称这种修行是神的恩宠的体现,并把哲学基础建立在“他力”即“他人的帮助”上面,也就是建立在“神的帮助”上面。而以禅宗为主的教派则强调“自力”,即自己帮助自己。这些教派教导说,只有自己内身才存在潜力,只有自己努力才能增加潜力。日本武士感到这种教义正中下怀,而且不论作为僧侣、政治家还是作为教师——因为这些职业都是由武士来担任的,他们都可利用禅宗修行法来支持刚毅的个人主义。禅宗的教义极为明确:“禅宗追求的唯一目的就是发现自己身上的光明。妨碍这种追求的任何障碍都不可容忍。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全部除去……见佛杀佛,逢祖灭祖,遇圣屠圣。这是唯一的获救之道。”
探索真理的人不能接受任何间接的经验,不论是佛祖教导、祖宗经典还是神学。“三乘十二分教都是废纸。”读读也有些好处,但却不会产生灵光一现,但唯有这灵光一现才能叫人顿悟。在一本禅宗对话集中,一位弟子请求禅僧讲解《法华经》,这位禅僧讲得非常精彩,但听讲解的弟子却苛刻地说,“怎么?我还以为禅僧您蔑视一切经典理论和逻辑体系呢!”禅僧回答说:“禅宗并不是一无所知,而是相信真知(顿悟)只在经典、教义之外。你并不是来‘问道’的,而只是来听我解读经书的。”
教弟子“悟道”的方法是禅师们所教授的传统修行的意义所在。修行可能是肉体的,也可能是精神的,但学习者最终必须在内心确认它的效果。击剑手的禅宗修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击剑手当然要学习并经常练习基本的剑术技巧,但这只属于“能力”的领域。此外,他还必须学习变得“无我”。最初,他被命令站在地板上,全神贯注于脚下支撑自己身体的那几平方英寸地板。这块窄小的地板逐渐升高,直到剑客学会了立在四英尺高的柱子上,就像置身庭院之中一样,那时他就得到“真知”了。而他的心也会顺从身体,不会因为害怕和眩晕摔下去了。
日本人的这种站柱修行把众所周知的西方中世纪圣西门派站柱苦修者的修行变成了有意识的自我修养。它已不再是一种苦行。不管是禅宗的修行还是农村中的普通习惯,所有的日本的肉体锻炼都经历了这种改造。跳进冰冷的水中和站在瀑布下这类苦行修炼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存在。有的是为了锻炼身体,有的为了祈求上苍的怜悯,有时则为了引起人定。日本人最喜爱的寒冷苦行是在天亮前站在或坐在冰冷刺骨的瀑布下,或在冬夜用冰水浇身三次。其目的是把自己锻炼到感觉不到痛苦的地步。这种人的目的是训练冥想时无视干扰的能力。当他意识不到冷水的冲击和身体的颤抖之时,他便达到了“练达”之境。除此之外,别无所得。
同样,精神训练也必须自悟。你可以请教师傅,但师傅也不会对你进行西方意义上的“指导”,因为你从自身以外学到的东西都没有什么用。或许师傅会和弟子讨论,但却不会温和地引导弟子达到新的智慧的境界。师傅越粗暴,对弟子的帮助就越大。如果师傅突然打掉弟子送到嘴边的茶碗,或绊倒他,或用铜如意敲打他的关节,弟子就会如触电般地顿悟。这打破了他的自满。记载僧侣言行的书中这种故事有很多。
“公案”是师父们为使弟子拼命努力开悟而最爱用的一种方法,字面的意思就是“问题”,据说有1700多个。在禅僧的轶事集中,一个人花七年时间来解答其中的一个问题是不足为奇的。“公案”并不是为了寻求合理答案。比如“听孤掌之鸣”,或者“要感觉到在自己成为胎儿之前的思母之情”以及“背着死人走的是谁?”,或者“向我走来的是谁?”,又或者“万物归一,一归何处?”诸如此类的禅宗问题在12或13世纪之前的中国也曾被用过。日本在接受禅宗的同时也接受了这些东西,但这些却在中国绝迹了。在日本它们却构成了“练达”修行的最重要部分。禅宗入门书极为重视公案。“公案包藏着人生的两难处境。”他们说,思考公案的人就像“被赶进死胡同的老鼠”、吞“烧红的铁球”的人以及“要叮咬铁块的蚊子”。他如痴如狂,加倍努力。终于,隔在其心与公案之间的“观察的自我”的屏障被拆除,心与公案两者如闪电般合二为一,于是他就“顿悟”了。
在读了这些对绷紧神经的努力的描写之后,再去从书中寻找他们费尽精力所获得的伟大真理时就会怅然若失。例如,南岳花了八年时间来思考“正在走向我的是谁”这个问题。最后他终于搞懂了。用他的话说就是:“此地有一物,但随即又失去。”但是,在禅宗的启示中有一种通用的模式,从以下几行对话中就可窥其一斑:
僧问:“怎样脱离生死轮回?”
师答:“谁束缚了你(即把你绑缚在这个轮回中)?”
他们说,他们所学的东西用中国一个有名的成语来表达就是“骑马找马”。他们认识到“需要的不是网与夹,而是用这些工具捕捉的鱼或兽”。他们认识到,换用西方的话来说,就是两难处境的两端与困难无关。他们认识到,如果打开天目,现有手段就能达到目标。万事皆有可能,但是不能借助外力只能靠自己。
“公案”的意义并不存在于这些追求真理之士所发现的真理之中,这些真理与世界范围内神秘主义者的真理毫无二致。公案的真正意义在于日本人如何探索真理。
“公案”被称为“敲门砖”。“门”就安装在蒙昧无知的人性的墙上,这种人性担心现存手段是否够用,并幻想有大群专注的旁观者会作出褒贬。这堵墙就是日本人有切身体会的“耻感”。一旦用砖打破了门,人就来到了自由的天地,砖也就没用了。他不再继续去解决更多的“公案”。学习已经结束,日本人的道德困境得到了解决。他们以拼命的架势撞进了死胡同,“为了修行”,他们成了“叮咬铁块的蚊虫”,最后他们恍然大悟:根本没有死胡同。既无“义务”与“情义”之间的绝境,也无“情义”与人情之间、正义与“情义”之间的绝境。他们发现了出路。他们成了自由之身,从此能充分“品尝”人生。他们达到了“无我”之境。他们的修养已至“练达”。
研究禅宗佛教的泰斗铃木把“无我”说成是“无为意识的三昧境”和“不着力、无用心”。“观察的自我被排除”,人“失去了自我”,就不再是自身行为的旁观者。铃木说:“随着意识的觉醒,意志一分为二成为旁观者和行为者,并且相互必然冲突。因为行为者希望摆脱(旁观者的我)约束。”因此,而当“悟”时,弟子发现,既无“观我者”,也无“作为不知或不可知之量的灵体。只有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行为。人类行为的研究者改变一下描述方式,就能更准确地写出日本文化的特性。在幼年时期人受到观察自己的行为和根据他人意见判断自己行为的严格训练。他作为观察者的自我非常脆弱。为使自己达到灵魂的三昧境,他排除这一脆弱的自我,他不再感到“我正在做”。这时他感到自己精神修养已经成功,就如学习剑术的人站在四英尺高的柱子上而不担心自己摔下去一样。
画家、诗人、演说家和武士都同样地利用某种训练达到“无我”之境。他们获得的不是无限,而是对有限美的清晰而不受干扰的感受,或是对手段与目标的调节能力,从而使他们能够准确地用恰如其分的努力达到恰到好处的目标。
甚至从未受过此种训练的人也会有某种“无我”经验。当观看能乐或歌舞伎演出的人在看得出了神的时候,可以说他也失去了观察的自我,他的手掌出汗,他感觉到“无我之汗”。一个接近其目标的轰炸机驾驶员在他投弹之前也会渗出“无我之汗”,他并不意识到“我正在做”,他的意识中没有作为旁观者的自我。旁若无人而全神贯注于敌机动态的高射炮手据说也同样会渗出“无我之汗”,并失掉了观察的自我。凡是在这种场合达到这种状态的人都进入了最高境界。
这种观念有力地证明日本人把自我监视和自我监督看成是沉重的负担,他们说,一旦去除这些约束,他们便变得自由而有效率。美国人把观察者的自我与身上的理性原理看作一回事,并以临危不乱镇定自若而自豪。而日本人当进入灵魂的三昧境里,忘掉了自我监视所强加给他们的约束时,他们就得到了解脱。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的文化不厌其烦地在他们的灵魂中灌输谨小慎微的必要性,可是日本人却极力辩解:当心理压力消失时,意识才能进入更有效率的境界。
日本人阐述这种信条的最极端的方式是他们对“像已死的人一样活着”的人的高度赞赏。这句短语按字面意思翻译成西方语言就是“活死尸”,在一切西方语言中“活死尸”都是一种表示恐怖的措词。我们用这个短语来说明一个人的自我已经死去,只留下一具空的躯壳,这个身体已经没有丝毫生命力。而日本人则用“像已死者一样活着”来表示一个人生活在“练达”的境界,并常常用于日常勉励。有人激励一个对中学毕业考试感到忧虑的少年时会说,“就像死人一样考试,很容易就通过了。”为鼓励某个正在进行重要商业交易的人,他的朋友会说,“就当是死了,去干吧。”当一个人陷入暗无天日希望渺茫的绝境中时,他常常会用“像死人一样”的决心去脱离困境。在日本投降以后,当选为贵族院议员的基督教著名领袖贺川(丰彦)在其自传体小说中说:“像被恶魔缠身一样,他每天在自己房中哭泣。他的爆发性的抽泣接近疯狂。他的苦恼持续了一个半月,但生命最终获得了胜利。……他要以死的力量来生活。……他要像死人一样投身于战斗之中。……他决心做一个基督教徒。”在战争时期,日本军人说,“我决心把自己当成死人,以报答皇恩。”这包括一系列的行为,比如在出征登船之前举行自己的葬礼,发誓把自己的身体化为“硫黄岛之土”,决心“与缅甸之花一起凋谢”等。
以“无我”基础的哲学包涵着“像死人一样生活”的态度。在这一状态中,人抛弃了一切自我监视,从而也抛弃了一切恐惧和警戒。他变得如同死人一样,于是不必再为行动是否恰当而考虑。死人不再报“恩”,死人是自由的。因此,说“我将像死人一样生活”就意味着彻底地从冲突中解脱了。它意味着“我的精力和注意力可以不受任何束缚勇往直前地去实现目标。我和目标之间也不再存在观察者的自我和其他任何恐惧的负担。随之消失的还有干扰我努力的消沉倾向和紧张不安的感觉。现在对我来说万事皆有可能。”
用西方人的话说,日本人“无我”和“像死人一样生活”的习惯是排除了意识的。他们所谓的“观察的自我”“干扰的自我”是指判断个人行为的监视者。下面的情况生动地反映了东西方的心理差异:当我们说到一个没有是非之心的美国人时,是指他做坏事的时候并没有罪恶感。但日本人这么说时,他指的却是不再感到紧张和不再受妨碍。美国人指的是坏人,日本人指的是好人,修养有素的人,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的人。他指的是能完成最困难的工作、最大公无私的人。罪恶感是要求美国人行善的巨大强制力,一个人如果对失去罪恶感麻木不仁,那他就成了反社会的人。日本人对该问题的解释是不同的,根据他们的哲学,人性本善。如果他的冲动直接体现于行为中,他就会自然而容易地实践德行。因此,为了达到“练达”,他经受修行,以排除“羞耻”的自我监视。只有在此时,他的“第六感”才摆脱一切障碍,他才能从自我意识和冲突中彻底解脱。
如果你脱离了日本人在其文化中的个人生活经验来考察这种自我训练的哲学,这就会成为胡言乱语。我们已经看到,被他们归诸于“观察的自我”的这种“耻辱”是他们的一种沉重的负担,但是如果不讲述日本人的育儿方式,那么对其哲学中的精神控制术依然无法解释清楚。在任何文化中,传统的道德约束力不仅通过言论,而且通过长辈们对其孩子的态度传给新的一代。不研究该国的育儿方式,外国人就很难理解该国的大事。通过分析日本人的育儿方式,我们能够对日本国民整体的人生观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而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只是在成年人层面叙述他们民族的人生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