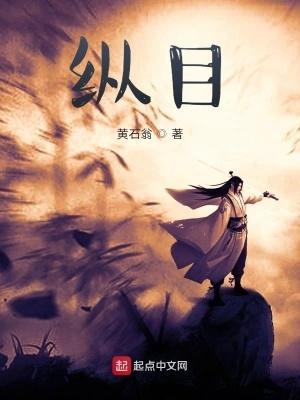奇书网>点茶 器具 > 拙朴紫砂器幽野之趣者(第1页)
拙朴紫砂器幽野之趣者(第1页)
拙朴紫砂器,幽野之趣者
纵向来看,
紫砂壶的发展过程
是从无到有,
从粗糙到精制,
从大壶到小壶。
紫砂陶器产自江苏宜兴,《辞海》对紫砂陶器的定义是:“紫砂陶器是用紫砂泥,红泥或绿泥等制成的质地较坚硬的陶制品,陶器外部不施釉,经1100℃—1180℃氧化气氛烧成。”由此点可以看出,一件紫砂器至少要经过1100℃的高温烧造方为合格。高温烧造的紫砂器结构致密,接近瓷化,但不具有瓷胎的半透明性,其器表含有细小颗粒,表现出一种砂质效果。紫砂泥大多是从开采的甲泥矿中精选出来的,它是紫砂土的主要矿源,甲泥在丁蜀地区俗称“夹泥”。制作紫砂陶器的泥料又称五色土,其不是单一的紫色。广义地讲,紫砂泥是紫泥、红泥、绿泥、团泥四种泥料的总称。
紫泥,属泥质粉砂岩,旧称青泥或天青泥,是制作紫砂器的主要原料。红泥,属泥质粉砂岩,红泥可分为紫砂红泥与朱泥两种,是以烧成后呈色命名的一个大类。朱泥制品收缩率高,成品率低,较高的收缩率使得原矿朱泥有“无朱不皱”之称。绿泥,属粉砂质泥岩,也称本山绿泥,其含铁量较低,多与紫泥、红泥配合后作为调配泥使用或用于粉饰紫砂胚体表面。团泥,亦称“段泥”“缎泥”,是以自然存在状态命名的,不是单一品种矿料,是各种矿料的共生状态,一般为绿泥和紫泥共生,烧成颜色多呈黄锻色调。同一泥料当中含砂量越多,收缩率越小;含砂量越少,收缩率越大。收缩率小的泥料所制壶的成品率就高,收缩率大的泥料所制壶的成品率就低。泥料中的含铁量决定了紫砂器烧成的色泽,铁含量越高,呈色越深。紫砂器在正常的烧成气氛中,随着温度的变化,胎质呈色也会产生深浅不一的变化,烧结温度越高,器物的颜色就会越重。同一泥料在不同的烧成气氛下,胎体色泽也会产生变化。清代吴梅鼎在《阳羡茗壶赋》中对紫砂制壶的色泽曾做过贴切描述:“夫泥色之变,乍阴乍阳,忽葡萄而绀紫,倏桔柚而苍黄。摇嫩绿于新桐,晓滴琅玕之翠;积流黄于葵露,暗飘金粟之香。或黄白堆砂,结哀梨兮可啖;或青坚在骨,涂髹汁兮生光。彼瑰琦之窑变,匪一色之可名。如铁如石,胡玉胡金。备五文于一器,具百美于三停。”
“耕而陶造”朱泥高梨形壶
客观地讲,用紫砂壶泡茶,并不是它可以使茶汤变得比其他沏茶器沏出的茶汤好喝我们才用,原因是在明代紫砂壶的朴拙与生俱来地带着一股幽野之气,与其时文人审美契合。昆石美玉,商鼎周彝,笔墨纸砚,梅兰竹菊都是文人身边的爱物,但是在使用的频繁度、亲切度上它们都无法与紫砂壶媲美。尤其是当壶中注入热水令壶有了温度后,壶与人的亲近感就更强了,这一点是其他物件所不具备的。
紫砂壶过去叫砂壶、窑器、或冲罐,“紫砂壶”是清末后才出现的叫法。既然有这么多颜色的矿料,为什么偏偏选择了“紫”这个字眼叫作紫砂,不叫黄砂、红砂呢?原因是紫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等级很高,皇帝的宫殿叫“紫禁城”;比喻高官显宦用“紫袍玉带”,“户列簪缨姓字香,紫袍玉带气昂昂”;瑞彩祥云说紫气东来。当人们把被赋予了语言文学特性的砂壶称作“紫砂壶”后,与生俱来的高级感就随之而来,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有意思的地方。
紫砂器的起源在学术界过去一直都有争议,由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无锡市博物馆、宜兴陶瓷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曾在2005年下半年对宜兴丁蜀地区古窑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根据文献记载以及传世实物综合考证,得出的结论是明早期墓葬中从没出现过紫砂器,有据可考的最早一件是南京市博物馆所藏于明代太监吴经墓中出土的嘉靖年间的提梁壶,所以紫砂被有目的性地使用,应始于明代的中晚期。明人周高起在其《阳羡茗壶系》中说:“创始: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矣。闻之陶家云,僧闲静有致,习与陶缸瓮者处,抟其细土,加以澄炼;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金沙寺在(宜兴)县东南四十里,唐代陆希声读书山房,后改禅院。”明代正德年间学宪吴颐山曾带着家僮供春居于金沙寺苦读诗书。家僮供春对寺内老僧制壶颇感兴趣,无事时经常溜入禅房偷看其抟胚做壶,逐渐掌握了制壶技术,遂“细土抟胚,茶匙穴中,指掠内外,指螺文隐起可按,胎必累按,故腹半矣”,制成了一把仿生树瘿茶壶,此即大名鼎鼎的供春紫砂壶,矗立起宜兴紫砂的第一座高峰。周高起说:“供春,学宪吴颐山公青衣也……世外其孙龚姓,亦书为龚春。人皆证为龚。予于吴周聊家见时大彬所仿,则刻供春二字,足折聚讼云。”金沙寺僧与供春为紫砂壶之创始之人,其后宜兴紫砂壶开始大量生产使用,人谓其“茗壶奔走天下半”,想见景况之盛。
“耕而陶造”老紫泥小宫灯壶
纵向来看,紫砂壶的发展过程是从无到有,从粗糙到精制,从大壶到小壶。我们由明代茶书对煮水、注水器的文字记录中来看看这一过程。明代最早茶书朱权1440年的《茶谱》中还未提及紫砂器,但已有瓷制煮水器出现,彼时所用的茶瓶“以黄金为上,以银次之。今予以瓷石为之”,顾元庆1541的《茶谱》说“茶铫、茶瓶,银锡为上,瓷石次之”,屠隆1590年的《茶笺》“所以策功建汤业者,金银为优……瓷石有足取焉。瓷瓶不夺茶气,幽人逸士,品色尤宜”,高濂1591年的《茶笺》:“茶铫、茶瓶,磁砂为上,铜锡次之。磁壶注茶,砂铫煮水为上”,砂器已然使用。许次疏1597的《茶疏》:“往时供春茶壶,近日时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盖皆以粗砂制之。”周高起1640年《阳羡茗壶系》:“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又近人远过前人处也。”
明代是绿茶散茶瀹泡的天下,紫砂壶诞生之初就是用来泡饮绿茶的。有明一朝紫砂壶名手辈出,代有大家。自供春树瘿壶问世以后,继起的制壶高手为“四大家”的董翰、赵梁、元畅、时朋及名家李茂林。董翰是最早创造菱花式砂壶的名手,其壶以文巧著称。提梁式壶,始创于赵梁,明代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赵梁,多提梁式,亦有传为名良者。”收藏家李景康、张虹合编的《阳羡砂壶图考》:“阳羡之作提梁式者,或以赵梁为鼻祖。后之提梁式有硬耳、软耳两种。其制作精美者,硬耳多见,软耳较罕也。”元畅制壶以古拙见长。时朋“即大彬父……供春之后劲也”。“李茂林,行四,名养心。制小圆式,妍在朴致中,允属名玩。”李茂林擅长作小圆壶,其壶于朴素端庄中见妩媚,世称“名玩”。值得一提的是,最初的紫砂壶是跟日用粗陶器皿混合在一起共用一窑装烧。自李茂林始,紫砂壶就被放在了匣钵里烧制,有效避免了烟火、柴灰等杂物对壶体表面产生的影响,使得紫砂壶的外观品相得到极大改观。其后,制壶大家时大彬及其弟子李仲芳、徐友泉亦名扬天下。
“陶家虽欲共春,能事终推时大彬”,时大彬(1573—1648),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人,制壶名家时朋之子。其壶艺在明代享有盛誉,多为文人记述。时大彬继供春之后,创制了许多制壶方法、工具、壶式。他开创了调砂法制壶,《阳羡茗壶系》记:“时大彬,或淘土,或杂砂土,诸款具足,诸土色亦具足,不务妍媚,而朴雅紧栗,妙不可思。”改进了供春“斫木为模”的制法,把打身筒成形法与镶身筒成形法结合起来,由此确定了紫砂壶泥片镶接成形的基本方法,这是紫砂壶工艺的一大飞跃。又创方形、圆形壶式,开启“方非一式,圆不一相”的新风貌,成为紫砂壶造型的典型壶式。日臻成熟的技艺使得时大彬的作品达到了“千奇万状信手出,巧夺坡诗百态新”的地步,史称“时壶”,其与陆子冈的制玉、江千里的螺钿、张鸣岐的手炉齐名,为人所珍。许次纾《茶疏》论:“往时供春茶壶,近日时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阳羡茗壶录》载:“名手所作,一壶重不数两,价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
时大彬在紫砂壶领域中还有一大贡献,即将紫砂壶在型制上由大壶向小壶进行了转变。如我们过去所说,万事的变化都有它的底层逻辑做支撑,那么紫砂壶由大转小的原因在哪里呢?这须得从明代一个非常有名的文人茶“岕茶”聊起了。前文有述,元初马端临编撰的典章制度史《文献通考》中曾记:“始知南渡以后,茶渐以不蒸为贵也。”自那时起至明代,绿茶散茶基本上以炒青、烘青工艺为主,有意思的是绿茶蒸青工艺却在晚明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绽放出一朵盎然之花——岕茶。明代陈继儒(1558—1639),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与董其昌齐名,学识广博,诗文、书法、绘画均所擅长。武英殿大学士黄道周给崇祯帝上疏曾言:“志向高雅,博学多通,不如继儒。”陈继儒在《白石樵真稿》中说朱元璋“敕顾渚每岁贡茶三十二觔,则岕于国初已受知遇,施于今而渐远渐传,渐觉声价转重。”可见岕茶在明初废团饼改散之后,未趋炒青大流,依然保留了蒸青工艺,岕茶工艺是先蒸后焙,明闻龙《茶笺》记:“诸名茶,法多用炒,惟罗岕宜于蒸焙,味真蕴藉,世竞珍之。”明晚期,岕茶名声渐大,陈继儒所辑《农圃六书》说其为“浙中第一”。
明时大彬紫砂壶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长兴顾渚山野生茶园
“岕”,指介于两山之间。岕茶,据长兴知县熊明遇约成书1608年的《罗岕茶疏》解释:“两山之夹曰岕,若止云岕茶,则山尽‘岕’也。岕以罗名者,是产茶处。”岕茶主要产于江苏宜兴与长兴交界处,稍偏长兴一侧的罗山。长兴、宜兴即唐代贡茶顾渚紫笋、阳羡茶的产地长城、义兴。
周高起于1640年左右成书的《洞山岕茶系》说:“至岕茶之尚于高流,虽近数十年中事。”岕茶保留蒸青工艺是有原因的,熊明遇记:“茶以初出雨前者佳,唯罗岕立夏开园。”立夏开园的茶青枝叶成熟度高,不再细嫩,这种茶青如果再用炒青工艺制作已不适宜。这一点许然明在《茶疏》中做了详细说明:“岕之茶不炒,甑中蒸熟,然后烘焙。缘其摘迟,枝叶微老,炒亦不能使软,徒枯碎耳。”明末张大复《梅花笔谈》中说:“松萝之香馥馥,庙后之味闲闲,顾渚扑人鼻孔,齿颊都异,久而不忘。然其妙在造,凡宇内道地之产,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可见岕茶的品质优劣与工艺是分不开的,“其妙在造”。
周高起说岕茶“叶筋淡白而厚”,“入汤,色柔白如玉露,味甘,芳香藏味中”,令人叫绝的是,岕茶更有奇妙的乳香。熊明遇《罗岕茶记》就说洞山岕“味甘色淡,韵清气醇,亦作婴儿肉香,而芝芬浮**,则虎丘所无也”。怎么来理解这个“婴儿肉香”呢?想象一下,你怀抱着一个正处于吃奶期的小宝宝,然后你把鼻子附在他的身上,吸气,闻,就是襁褓中孩子身上带着的那种淡淡奶香的味道,有生活经验的朋友一听我这个话就明白了。这个淡淡奶香实际就是茶氨酸的味道,这也是我多次给朋友们讲茶时候提及的,乳香在茶的香气中是非常高等级的一种香味。如果一款茶,它的汤水中带着乳香,那么这款茶的生态一定是非常好的,茶品应为一流水准。《续茶经》引明人沈石田《书岕茶别论后》对岕茶有这样的评价:“昔人咏梅花云:‘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此惟岕茶足当之。若闽之清源、武夷,吴郡之天池、虎丘,武林之龙井,新安之松萝,匡庐之云雾,其名虽大噪,不能与岕相抗也。”
冒襄(1611—1693),字辟疆,明末清初文学家,在《岕茶会钞》中冒襄回忆产量稀少的上品岕茶:“忆四十七年前,有吴人柯姓者,熟于阳羡茶山,每桐初露白之际,为余入岕,箬笼携来十余种。其最精妙不过斤许数两,味老香深,具芝兰金石之性,十五年以为恒。后宛姬从吴门归余,则岕片必需半塘顾子兼,……每岁必先虞山柳夫人,吾邑陇西之倩姬与会共宛姬,而后他及。”虞山柳夫人是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中有着高尚民族气节、愧杀明末无数须眉的奇女子柳如是,宛姬即冒襄小妾聪明灵秀的窈窕婵娟董小宛。在被后世称为忆语体文字鼻祖的《影梅庵忆语》中,冒襄记自己与董小宛品岕茗:“姬能饮,自入吾门,见余量不胜蕉叶,遂罢饮,每晚侍荆人数杯而已。而嗜茶与余同性,又同嗜罗片。每岁半塘顾子兼择最精者缄寄,具有片甲蝉翼之异。文火细烟,小鼎长泉,必手自炊涤。余每谓左思《娇女诗》‘吹嘘对鼎?’之句,姬为解颐。至‘沸乳看蟹目鱼鳞,传瓷选月魂云魄’,尤为精绝。每花前月下,静试对尝,碧沉香泛,真如木兰沾露,瑶草临波,备极卢陆之致。”与冒襄、侯方域、方以智合称“明末四公子”的陈贞慧在《秋园杂佩》中说:“色香味三淡,初得口,泊如耳。有间,甘入喉;有间,静入心脾;有间,清入骨。嗟乎!淡者,道也。虽吾邑士大夫家,知此者可屈指焉。”《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中辑历代茶书114本,这其中关于岕茶的专著就有六本:明代熊明遇《罗岕茶记》、冯可宾的《岕茶笺》、周高起《洞山岕茶系》,周庆叔的《岕茶别论》,佚名的《岕茶疏》、清代冒襄的《岕茶汇钞》,可见,岕茶清饮在明末清初文人雅士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至上。
吴中文人所贵的岕茶,是江南茶史的一个剪影,昔年的茶人如一缕清幽的茶香倏忽而逝,目不能及。要领略岕茶历史的温度需得走进山中,循道而行。每年立夏,我都会到长兴山中做一点岕茶,以“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岕茶那种带着乳香、素水兰馨的口感令人神驰,印象中只有清香型的极品白水观音方能达到类似感觉。
明代散茶壶泡省去了唐宋制饼、碾茶、罗茶这些繁复的流程,拉近了泡茶器与茶人的距离,客观上为茶壶这一具体茶器的发展与繁盛提供了条件。岕茶本身属于小众茶,最了解岕茶的就是明末的那些文人士大夫,他们的饮茶趣味和习惯直接影响了泡茶器具的变化。紫砂壶跟茶人的日益亲密接触,又使得茶人对茶壶的审美成为必然。万历之前,崇尚大壶;万历之后,壶型日渐缩小,这一变化起于时大彬与陈继儒的交游。《阳羡茗壶系》记时大彬“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壶,后游娄东,闻眉公与琅琊太原诸公品茶施茶之论,乃作小壶。”娄东即现在的江苏太仓,自古为文人荟萃之地。陈眉公就是陈继儒,琅琊是明末清初的画家王鉴。太原为王时敏,明末清初画家,善山水,开创了山水画的娄东派。王鉴与王时敏被时人推为画坛领袖。
瀹饮岕茶
早期时大彬受供春的影响所制均为大壶,大壶非为泡茶之用,而是用于煮水、煮茶,如明代吴经提梁壶,高17。7厘米,口径7厘米,估计容量得有1000毫升。江苏泰州出土壶底钤印“时大彬于茶香室制”的圆壶容量达900毫升。后来时大彬到江苏太仓交游,与名士陈继儒交往甚密。期间,时大彬与岕茶铁粉陈继儒及陈好友王鉴、王时敏一同品岕、赏壶、论道。这些文人士大夫阶层对岕茶雅致的品评在相当程度上启发、引导了时大彬,令其领悟了中国茶文化的深厚底蕴及彼时茶人品茗对器具的审美偏好,如许然明《茶疏》之语:“茶注,宜小不宜甚大。小则香气氤氲,大则易于散漫。大约及半升,是为适可。独自斟酌,愈小愈佳。”时大彬茅塞顿开,于是开始尝试把文人美学趣味对茗壶制作的要求融入自己的创作中去,“乃作小壶”。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现藏有一把白泥瓜棱壶,为公元1609年时大彬专为陈继儒而制。壶底刻款:“品外居士清赏,己酉重九大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