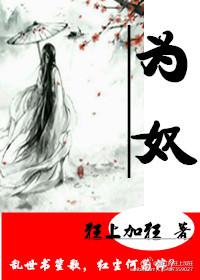奇书网>在印度看印度作者图片 > 第二章 定居印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002(第3页)
第二章 定居印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002(第3页)
“Paratha”最常见的馅料有三种:土豆、胡萝卜、奶豆腐,只要不容易出汁水的食材都可以作馅料。吃的时候主要有三种辅料:黄油、酸奶、腌芒果——在刚出锅的热饼上放一块黄油使其自然融化,再配着酸奶或腌芒果吃。这个腌芒果(AamKaAchaar)的味道对我来说非常惊悚,但印度人非常喜欢,堪称印度老干妈。
我第一次吃“Paratha”是2013年在旁遮普邦阿姆利则的一个茶摊,当时我对印度食物的了解还很肤浅,十分缺乏想象力(在印度旅行最大的意义之一就是不断挑战你的想象力)。茶摊做的“Paratha”已经涂好了黄油,同时给了我一小碟酸奶,我看当地人都用手撕下一块饼,然后包着酸奶吃(印度的酸奶是半固体的),觉得难以接受——这种又咸又油的饼怎么能跟酸奶一起吃?!然而尝试之后,我竟然迷上了这种搭配,酸奶刚好中和了饼的油腻和咸辣,简直完美!以至于我后来吃“Paratha”时要是没有酸奶,那就难以接受了。
通过这件事,我发现人的味觉的可塑性是很强的,一开始无法接受的“黑暗组合”,吃着吃着居然就爱上了。当然,能接受印度食物,不代表我愿意天天吃,对中国胃来说,最大的慰藉还是一碗干干净净的热汤。
“Roti”这一系的饼,最常见的就是上面这几种,其共同的特点是:全麦、死面。由于对和面、发面、揉面没有任何技术上的要求,在印度,上至八十老妪、下至六岁孩童都能做。
然而,从个人口味上来讲,我从来都没喜欢过“Roti”(我知道有不少人还是挺喜欢的)。在印度餐厅里,我吃正餐点主食的优先顺序是:1。飞饼(喂,你都还没讲到飞饼呢!继续卖关子!);2。馕;3。炒面;4。米饭。如果以上主食都没有,我才会吃“Roti”系的饼。
第二大系:异域来客——馕
馕(Naan)这个词来自波斯语,意思就是“面包、食物”,据研究,最早可能是古波斯人在烧热的石头上烤出来的一种面饼。我相信馕应该是最古老的面食形式之一,毕竟小麦这种作物便是起源于西亚农业起源中心区的。烤馕的技艺长期以来历经千锤百炼,如今已臻化境。
不少中国人可能觉得我国新疆的馕和意大利的匹萨看起来那么像,是不是有关系呢?所有以小麦为主食的民族都会烙大饼,然而馕和匹萨并没有可比性。正儿八经的“馕”,必须得用馕坑来做——馕坑里的饼可不是水平放置的,而是贴在炉膛上的。你倒是把匹萨贴在炉膛上试试。
中国的烧饼很可能也是馕的一个分支,烧饼相传是东汉时期由班超从西域带入的。做烧饼用的炉子跟馕坑看起来很像。
馕坑是一种底大口小的烤炉,这玩意也是古波斯人发明的,在波斯语里叫“Tanur”,意为泥炉,传到印度变成了“Tandoor”,用馕坑烤制食物的方法则叫作“Tandoori”,这个词音译成中文就成了“唐杜里”。有一道在海外印度餐厅很出名的印度菜叫作“唐杜里鸡”,不明就里的人可能会以为是某个叫“唐杜里”的人做的鸡,听起来很高大上,然而兜个圈子再意译回来,其实就是“馕坑烤鸡”。
虽然世界各地有不同的馕,但我坚定地认为,只有馕坑烤出来的才是真正的馕。
以前在上海的时候,我吃过馕,从来没觉得馕特别好吃。直到去了新疆之后,才明白馕一定要趁热吃。馕是一切面饼类食物登峰造极的终极形态,没有任何一种面饼,能够在不用油和其他辅助调味料的前提下,比新鲜出炉的馕更好吃。
如果你觉得馕不好吃,那只有一个可能——你没有吃到真正好吃的馕。
打馕跟茶道一样,是一种玄学。顶级的馕可遇而不可求,你会觉得那根本就不可能是凡人的双手做出来的食物。一旦吃到,从此其他的馕都成了浮云,而那块馕会成为你记忆中永远的美好珍藏。
我生平曾有为数不多的几次,被某样食物的美味感动到像吃了“黯然销魂饭”那样想要流泪。其中有两次都是因为吃到了天才般的双手制作的“顶级馕”,一次是新疆的某个路边馕,另一次是克什米尔的某个弄堂馕。那番滋味,堪称“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我最早吃到南亚的馕,是在拉萨的一家叫娜玛瑟德的尼泊尔餐厅,回想起来,那个馕的水准相当高。真的到了南亚,反而未必能找到这么好吃的馕。娜玛瑟德餐厅的馕是水滴形,这是他们拉薄面饼的一种手法,后来在有“亚洲十大餐厅”之称的德里卡里姆餐厅(Karim’s)吃到的馕,也是这个形状,非常松软可口。
我有段不得不吃酱油拌饭的日子,最大的享受莫过于跑到列城的老城区,买几个热腾腾的烤馕,看着黄油在馕上融化……这种“碳水炸弹”(16)入口之后带来的莫大的慰藉感,是什么山珍海味都比不上的。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笔墨描述馕的美味呢?因为在了解印度这些饼的制作原理之前,我一直很困惑:大家都是拿面粉做的饼,明明有“馕”这么好吃的做法,为什么还要做“Roti”这种淡而无味的东西呢?如果说“Roti”是小麦面饼最原始的形态,那么馕就是我能想到的小麦面饼最巅峰的形态了。
后来我才明白,馕和“Roti”的差别,简直比小米粥和大米饭的区别还要大。除了需要用馕坑之外,大部分的馕都是用精白面粉做的,会加盐和酵母;有的馕吃起来非常松软且有奶香味,这是因为和面的时候使用了酸奶,乳酸菌发酵饧出来的面团别有一番风味。
我太太在家里也做过馕,用酸奶和面,面团擀薄之后用手拉长,贴在平底锅里,成型之后用明火燎一下,吃起来居然跟外面的馕还挺像的。
总之,馕作为一种传到印度的食物,自成一派,由于需要馕坑,不是每个饭店都供应得上,跟本土“Roti”系面饼有很大的区别。
第三大系:南印度特色——米饼
无论是“Paratha”还是馕,这类面饼都在北印度更为流行,南印度人有他们自己的心头好。你如果去一些印度餐厅,会发现“南印度菜”被单独列为一个类别。
“南米北面”的传统在印度同样成立——北印度吃面饼,南印度吃米饼。南印度系的饼也是自成一派,而其关键原料就是——发酵过的米浆。
南印度最流行的饼是一种叫作“Dosa”的脆薄米饼。根据对古代泰米尔的文献研究,这种食物在公元一世纪左右就已经出现了(个人对印度的这一历史考证表示存疑)。我第一次在印度吃到“Dosa”的时候,心想这不就是中国的杂粮饼嘛——一块架在灶头上的大铁板,倒一点油,碎米浆往上面一浇,然后拿个勺斗刮平,做好之后是一种略带酥脆的饼。
但是这个“Dosa”吃起来的口味跟中国的杂粮饼可大不一样。首先,“Dosa”的米浆,不仅仅是大米,里面还混有印度人最爱的黑豆(17)(需要先去皮,也可以用其他豆子代替);其次,这个米浆要提前做好,然后发酵一晚上,所以“Dosa”吃起来会有股酸酸的味道,很奇怪;第三,“Dosa”被端上桌的时候,通常已经把馅料卷在里面,这会破坏饼皮的酥脆,而最常见的馅料就是玛萨拉洋葱土豆。
“Dosa”总的来说可以接受,有些挺好吃,有些不那么好吃,跟所有“薛定谔的印度菜”一样,都是非标准化的,好不好吃要看运气。我在印度吃过的最好吃的“Dosa”是在亨皮景区里的亨皮村(Hampi),那里有一家专门做“Dosa”的家庭小餐馆,根据游客的口味调整了配方,用的是没有发酵过的米浆,做出来是比较正常的米饼味道,并且还有“香蕉Dosa”“蜂蜜Dosa”之类的非传统风味。
饭店里那种大尺寸的“Dosa”需要一块大铁板,一般人家里没有条件做,南印度人家里一般就用做“Roti”的塔瓦锅做小号“Dosa”。既然这是一种公元一世纪就已经存在的食物,自然也有许多变种。
“Dosa”有两个常见的变种:“Appam”和“Uttapam”。
“Appam”这种饼简单又美味,在米浆里面加上打碎的椰子肉,然后就像烙饼一样烙单面,中间部分是软软的椰香米糕,两边是又薄又脆的饼边。“Uttapam”外观上有点像米饼做的迷你匹萨,在“Dosa”的基础上加厚加料,会在上面加各种各样的蔬菜,需要正反双面煎。
南印度人明显对这种发酵过的米浆上瘾,用“Dosa”完全相同配方的米浆,还做出了一种蒸米饼——“Idly”,其流行程度跟“Dosa”不相上下。
“Idly”是印度为数不多蒸制的食物,也是到目前为止,我最不习惯也最不喜欢的印度主食。“Idly”的卖相其实相当好,看起来“眉清目秀”的,跟中国国内的米饭饼很像。但是吃到嘴里你就会发现,这确实是米饭饼,不过是“馊”掉的米饭饼。因为“Idly”的米浆发酵过。假如这个饭店用的米浆放的时间长一点,无疑味道会更重。发酵的米浆油煎做成“Dosa”,再配上玛萨拉,这种馊味会被盖住,但是蒸成“Idly”,馊味则会很明显。这就跟不新鲜的鱼不宜清蒸是一个道理。
倒是喀拉拉邦有一种叫作“Vattayappam”的蒸米糕,味道跟中国的米糕几乎一模一样,没有发酵变酸,没有加玛萨拉,也没有甜得发齁。要知道这种味道“正常”的食物在印度可是非常稀有的,印度人会觉得没有加玛萨拉的食物都是没有灵魂的,所以这种食物很小众。
另外,很多中国人吃不惯印度长条状的籼米,而南印度这边专门做“Idly”用的大米应该算是一种粳米,外观为椭圆状。我试过用这种大米做饭,缺少米饭的香味,黏性也远远不如中国大米。到目前为止,我在印度吃过最接近中国大米口感和香味的,是克什米尔稻米。南亚著名的“Basmati”香米虽然是籼米,某些品牌的大米如果先浸泡,然后再多加点水煮,也有可能做出中国米饭的软烂口感。
印度三大系的饼——不发酵的全麦系、中东人带来的馕系、南印度的米饼系——都介绍完了,而中国版本的“印度飞饼”看似跟三大系都没有关系,那是不是可以认为印度真的没有飞饼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中国版本的印度飞饼其实有两种:一种是饭店里面表演的飞饼,通过抛甩把面饼做得很大很薄,然后折叠一下油煎,切成小块上桌;另一种是超市里冷冻的“印度飞饼”,用平底锅加热一下就能吃,那是一种薄而酥脆、层次分明的油煎面饼。
当我人生第一次在班加罗尔吃到“Parotta”的时候,我立马认了出来——这就是飞饼的原型啊!“Parotta”的制作原理和方法跟中国超市版本的“印度飞饼”几乎完全一样:将精白面粉加油盐(或鸡蛋)和面,做成油面团,将面团擀成面饼之后,再利用离心力将面饼甩大甩薄,做成一个类似于花卷的面团,把面团擀平之后在铁板上煎,从而制作出具有松脆口感、层次分明的饼。
后来我发现在印度除了圆形的千层“Parotta”之外,还有一种折叠成方形的手帕“Parotta”,无论是外形还是口感都跟中国饭店版本的印度飞饼无限接近。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国的飞饼会做得更大,用更多的油,做出来更松脆、更好看。中国版本的印度飞饼抛甩到空中这一形式,确实有可能是受到了北印度“RumaliRoti”的启发,也正是这种浮夸猎奇的抛甩表演,使得飞饼有机会崭露头角、风靡中国。要不然的话,中国有那么多种好吃的饼,飞饼的口味也并无特别惊艳之处,恐怕早已迷失在茫茫“饼”海中。
不过,我没有查找到关于“Parotta”这种饼的起源说法,只知道它最早在喀拉拉邦的马拉巴尔(Malabar)横空出世,如今在整个南印度都能找到,所以这种饼也叫“MalabarParotta”。“Parotta”这个词据说是“Paratha”在当地语言的异化,然而北印度的这种馅饼和“Parotta”无论是在制作方法上还是口味上都看不出有什么关系,或许是南印度人把“Paratha”这个词直接借用了一下。喀拉拉邦的“Parotta”要明显大于泰米尔纳德邦的,大约有十寸,一个就能吃饱,而泰米尔纳德邦的“Parotta”只有六寸左右,要两三个才能吃饱。
出于对精白面粉“Maida”“毒性”的恐惧,南印度人对“Parotta”很纠结:一方面是不大待见它,我南印度的哥们儿整天说这玩意吃多了“有毒”;另一方面,几乎每家路边饭店都有卖的,这说明当地人其实还是喜欢吃,但又不敢多吃,只在饭店里偶尔吃吃。我有时不想吃家里的米饭,就会打包几个当饭吃,一个月最多也就吃一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