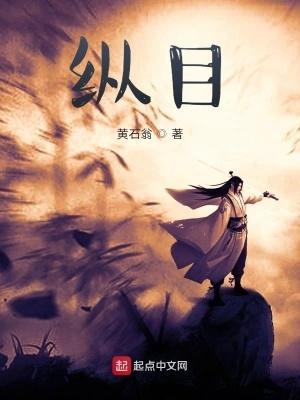奇书网>苔丝狄蒙娜 > 14 午夜洗礼(第1页)
14 午夜洗礼(第1页)
14午夜洗礼
八月的一个黎明,浓雾弥漫。夜间产生的浓厚湿气,在暖阳的照射下,逐渐分散,慢慢收缩,变成一团团,一簇簇,躲进低洼的山谷,藏匿于浓密的树林,直到最后蒸发干净,消失得无影无踪。
云雾笼罩,太阳看起来也与往日不同,显得奇异特别,好似有了五官人形,有了意识感知,要想恰如其分地把它描写清楚,非得使用阳性代词才行。他高悬于天,面貌如斯,与此同时,辽阔大地上,空无一人,这番情景瞬间便阐释了在古代为什么有太阳崇拜。你会觉得,普天之下再也没有比崇拜太阳更合乎情理的了。这个光芒四射的大火球就是一个生灵,头发金黄,笑逐颜开,神采奕奕,就像上帝,浑身上下充满了活力,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大地,仿佛地面满是情趣。
片刻,那光束便像烧红的通条,穿窗过隙,照射到农家小屋里的碗橱、五斗柜及其他家具上,撩弄得困意未消的农人无法继续赖床排遣倦意。
不过,那天早晨最艳的东西莫过于两根漆得通红的宽木条,通红的木条耸立在马泺村外一块金黄色的麦田边上。地旁边有台收割机,是昨晚运来的,准备今天使用。那两根红木条固定在另外两根木头支架上,就构成了安装在收割机上可以旋转的马耳他十字架。十字架上的红油漆,经阳光一照,越发红艳,好似浸在浓烈的**火焰中一般。
那片麦地已经“开镰”了,“开镰”的意思是,在麦田的四周,已经人工割了一圈,辟出了一条几英尺宽的小路,以方便马匹与机器开始下地干活儿。
通往麦田的篱路上已经来了两拨人,一拨是男人,另一拨是妇女,他们来的时候,东边树篱顶端的影子正好投射到西边树篱的中腰,此时,割麦人的头沐浴着朝霞,可他们的脚却还处在黎明的暗淡之中。他们走到最近那块麦田的栅栏门那儿,栅栏门两边各立着一根石柱,走进去,消失在麦田里。
一会儿的工夫,地里便传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像蚂蚱索爱求偶的动静。机器开动,开始割麦子了;从栅栏门往里看,只见三匹马套在一起,并排拉着前面所说的那台长长的收割机,收割机摇摇晃晃,慢慢前行;拉机器的三匹马当中,有一匹驮着一个赶马的,收割机的座位上坐着一个照看机器的,这个大家伙沿着麦田的一边向前开动,机器的收割臂展开,慢慢旋转着,一直开过山坡,完全消失在视野里。过了一会儿,那机器又以同样均匀的速度,从麦田的另一边慢慢开过来;在刚割过的麦茬上,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前面那匹马额头上那颗闪闪发光的铜星,然后是鲜红的收割臂,最后那个大家伙才完全现身在田间。
机器每收割一圈,麦田四周原本狭长的麦茬就加宽一档,上午时光慢慢流逝,未割刈的麦田面积在缩减。大小野兔、各类蛇虫、大鼠小耗都被驱赶着,向麦田中央更小的区域退缩,好像躲进堡垒寻求庇护似的,可哪里想到这只是暂时的避难所,等待他们的却是死亡的厄运。慢慢地,避难的麦田变得越来越狭小,后来这些小动物,无论原来是敌是友,都惊恐地挤缩成一团;收割机势不可当,一往直前;最后,剩余不到几码宽的麦子也倒在了它的铁齿之下,收庄稼的农人便棍棒齐下,乱石纷飞,一股脑儿将这些生灵统统打死。
收割机将割下的麦子一小堆一小堆地撂放到身后,每一小堆正好扎成一捆,一群人跟着机器,忙忙碌碌动手捆麦子——捆麦子的主要是妇女,但也有些男人,他们上身穿着印花布的衬衣,下身穿着长裤,长裤用皮带扎在腰间,这样一来,裤子后面的两颗纽扣也就用不着了,他们每弯腰捆扎,扣子便在阳光的辉映下闪闪发光,仿佛是他们后腰上长出了一双双眼睛。
但在那群捆麦人当中,还是妇女最能引起兴趣。女人一旦走到户外,不再像平日里那样,仅仅是家里的一件摆设,而是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浑身就散发出无穷的魅力。田间的男人只是一个人,田间的女人则是一道风景;她的身子仿佛没有了轮廓,吸收了四周环境的精华,与周围景物融为一体,变成了其中的一部分。
那些妇女——或者称其为女孩子更合适,因为她们大多都青春年少——头上戴着棉布的百褶帽,帽檐宽大下垂,用来遮挡阳光,手上戴着手套,保护双手,不被麦茬划伤。她们中间,有一个穿着粉红色短上衣,有一个穿着奶油色的紧袖长衫,还有一个穿着红色短裙,那短裙红得像收割机上的十字架。其他年纪稍大些的,都穿着棕色的粗布“套筒”或者罩衫——妇女在田间劳作时最合适的老式服装,年轻的女孩子都早已不再穿了。今天早晨,大家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转到那个穿粉红色棉布上衣的女孩儿身上,她身材最出挑,苗条婀娜,曼妙玲珑。可是帽檐却拉得很低,盖住了额头,在低头捆麦子的时候,一点儿也看不到她的脸,不过从帽檐下散落的一两绺棕褐色头发,大致可以推断出她的面容肤色。别的女人总是前张后望,左顾右盼,而她却低眉顺目,不显不露,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她却反倒招惹得人家偶尔投来关注的目光。
她不停地捆麦子,就像钟摆一样,机械重复,单调乏味。她用右手从刚捆好的一捆麦子里抽出一把来,伸开左手,轻拍麦穗,将这把麦子弄齐;然后弯腰俯身向前,双手将面前一小堆麦子拢到膝盖跟前,戴手套的左手从一大抱麦子下面插过去,同另一边的右手会合,就像拥抱情人一样将麦子抱在怀里,再将那把弄齐的麦秸用作草绳,两头拉紧,交错收拢,然后跪在麦捆上,将其捆扎结实。微风吹来,不时掀起她的短裙,她又不断地将其扯回去。在衣袖与暗黄色手套之间,一段手臂**出来,娇柔嫩滑,清晰可见。一天慢慢过去,劳作中,麦茬与麦芒多次划破她柔嫩的皮肤,手臂上流出了血。
劳作之间,她时而站直身子休息一会儿,把松散的围裙系好,把歪斜的帽子戴正。此时,可以看出她是个标志俊俏的年轻女子,鸭蛋儿脸,眼睛深邃黝黑,一头长发,浓密柔顺、平整丝滑,好像无论落于何处,都会紧紧贴服其上似的。她脸颊白皙,牙齿齐整,嘴唇柔薄,不大像一个乡下寻常女子。
这个女子正是苔丝·德伯菲尔德,或者叫德伯维尔。她或多或少有了些变化——既是原来的她,又不是原来的她;她眼下的处境,就像个他乡异域的客居之人,即使她对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了如指掌。在家隐居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她还是下定决心走出房门,在自己村上做些户外活计;村里一年中最大的农忙季节到了,无论她在屋里做什么工作,都比不上到地里收庄稼所得的报酬优厚。
其他妇女捆麦子的动作大体上与苔丝的一样,待捆好一捆,她们便像在跳方阵舞,从田间四面八方聚拢起来,把各自的麦捆靠着别人的,每十捆或者十二捆,竖放成一堆,或按当地人的说法,叫一垛。
她们吃了早饭,返回地里,又继续捆麦子。快十一点钟的时候,这时要是有人注意观察苔丝,就会看到她脸上显现出一副渴望期盼的神情,不时朝着山头观望,不过手里捆麦子的动作却丝毫没有放慢。临近十一点,在布满麦茬的坡顶上露出了一群孩子的小脑袋,这群孩子从六岁到十四岁不等,正朝这边走来。
苔丝的脸上泛起红晕,仍然没停下手上的活儿。
那群孩子中,年龄最大的一个是个小姑娘,身上披着一块三角形的大围巾,一角拖在麦茬上,胳膊里抱着什么东西,乍一看似乎是个洋娃娃,后来才看清是个裹在襁褓中的婴儿。另一个孩子手里提着午饭。收麦子的人都停下手里的活儿,各自拿出吃的东西,靠着麦堆坐下,吃了起来。男人还熟练地从一个瓷坛子里随意倒着什么,一个杯子在大伙儿当中依次传递着。
苔丝·德伯菲尔德最后一个停下手里的活儿,在麦垛的一侧坐下来,把脸扭到一边,躲开同伴。她一坐下来,就有一个头戴兔皮帽子、腰间皮带上塞着一块红毛巾的男人,从麦捆顶上递过一杯麦芽啤酒让她喝,不过她婉言拒绝了这份殷勤。午饭一摆好,她就把那个大孩子——她妹妹叫过来,从她怀里接过婴儿,她的大妹妹正巴不得放下这个小累赘,一交接完毕,便飞似的跑向另一个麦垛,和其他小伙伴耍了起来。苔丝的脸上再次泛起红晕,她偷偷扭过身,果断地解开上衣扣子,开始给孩子喂奶。
坐在苔丝身边的几个男人心生体谅,转过脸去,看向麦田的另一边;有几个默默低下头,自顾自吸起烟来;还有一个,在那里尽自愣神,念想着他的最爱,一双大手下意识地抚弄着那个再也倒不出一滴酒的坛子。除苔丝外,所有女人都一边理着弄乱了的发结,一边开始热烈地闲聊起来。
等婴儿吃饱了,年轻的妈妈便把他放到自己大腿上,扶他坐正,轻轻颠着哄他玩;她眼睛望着远方,表情忧郁冷淡,甚至是憎恶;突然,她又俯身下去,在婴儿的脸上狂热地亲吻了几十下,就好像永远都亲不够似的;这猛烈热切的亲吻里,满是疼爱,可又莫名其妙地掺杂了几分鄙夷与厌恶,这突如其来的亲吻吓得孩子哭了起来。
“其实,她打心眼儿里喜欢那个孩子,别看她嘴上净说些傻话,又是和孩子一起死了算了,又是啥的。”那个穿红裙子的女人说。
“过不了多久,她就不会那么说了。”那个穿米色衣服的人答道,“真是想不到,时间久了,那种事竟也能看得惯,心不乱啦!”
“我觉得,那件事可不是哄骗一下就成的,当初总得费些力气。听说,去年的一天晚上,有人听见猎苑里有人抽抽搭搭地哭,要是那时候有几个进去看看,说不定那个人也遂不了愿!”
“哎,或许是吧,可不管咋说,这种事,别人都没碰上,赶巧让她给撞上了,真是太可怜啦!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种事,得长得水灵俊俏的人才能碰上!丑姑娘保管一点儿事都没有——嗨,珍妮,你说是不是?”说着,讲话人扭头看向人群里一个姑娘,那个姑娘长得,要是说她丑,一点儿也不为过。
说苔丝可人怜爱,那是千真万确;她坐在那里,就是仇人见了,也不会不觉得怜惜。她的柔唇宛如一朵鲜花,一双柔媚的大眼睛,黑中带蓝,灰中透紫,竟辨不出到底是何颜色,索性将这些颜色调和在一起,再加上百十种其他色调,调成了色彩丰富的虹彩,一层一层,深浅不同,一抹一抹,浓淡各异,环绕在那深不见底的瞳仁周围。倘若她的家族没遗传给她稍欠谨慎这一缺陷,她便是一个完美女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