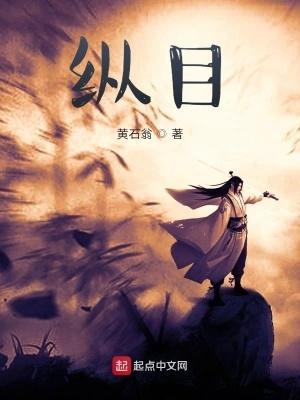奇书网>女主权谋文 > 第3章 深宫胡笳夕(第2页)
第3章 深宫胡笳夕(第2页)
刘启右手一挥,阔大的绛色衣袖如深红闪电划过空旷的大殿,他的声音越发高而响亮,像是一种郁积多年的热情在爆发:“秦灭六国,楚汉相争,战乱百年,关中到处都是横尸饿殍。而孝文皇帝,却宁愿委屈地与胡人讲和,也要让自己的子民好好休养生息,让天下人能过上几天太平生活。阳信,你知道先帝临终前,留了什么样的遗言给朕吗?”
阳信公主没有回答,她的眼睛向温室殿内的鸿羽帐后看去,那里,放着一幅八扇的素绢屏风,屏风上,有刘启亲笔书写的两排秦篆大字:
召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
只有十一岁的她,虽然不能明白这话里的深意,却隐隐觉得,这两句出自《管子》的话,大有暮气,四平八稳,没有什么激励的意思。
“孩儿不知道。”她低下了头。
阳信公主六岁时一个夏天的早晨,还在睡梦中的她,被人抱至前殿,与其他几十个孙儿孙女一起,拜见了祖父孝文皇帝最后一面。
记忆中,那是个脸色苍白的衰朽的老人,躺在打着补丁的布单下,有气无力地喘息着。他的眼睛中,从前的威严和冷漠**然无存,只残留着对生的强烈的留恋。听说他做皇帝,一辈子克勤克俭、兢兢业业,和自己的父亲性格相近,也同样劳碌而严厉。
刘启背过了身,面向殿后悬挂的汉文帝画像,神色庄重,幽幽说道:“先帝只说了十六个字:‘靡止兵革,宽政简税,克勤克俭,兴农兴商。’”
他抬眼看着侧墙上孝文皇帝那张被画工特意加工过的气宇非凡、神采飞扬的脸,顿了一顿,才脸色肃穆地说道:“朕登基已经五年了,五年来,朕无时无刻不将这十六个字牢记在心头。阳信,你是个在深宫长大的尊贵的公主,你不懂得战祸是多么可怕,不懂得老百姓是多么期待和平,民间有句歌谣,唱道:宁做太平犬,勿作乱离人。阳信,你能理解这首歌中的眼泪吗?你能闻见歌中的血腥气吗?”
十一岁的阳信公主沉默着,没有回答。
殿里越发显得寂静了,北风尖利地呼叫着,穿过外面的空廊和石道。
“可是,可是……”她打量着父亲凝重的脸色,犹疑着,仍然开了口,“一个国家的尊严不重要吗?父皇,我听说,前几次和亲,换来的和平都极其短暂。作为匈奴国开创者的冒顿单于,娶了两次大汉的公主,仍然不断侵袭雁门关和云中郡……他甚至在高祖皇帝死后,写来无礼的信件,侮辱了高祖的遗孀吕太后。他的儿子老上单于和孙子军臣单于,承传了冒顿的野蛮和背信弃义,和亲,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这是国家大事,不是你一个小小女子可以过问的!”刘启忽然打断了她滔滔不绝的述说,“阳信,今天你说了这么多,是谁教你的?是明台公主吗?”
父皇果然是个富有洞察力的君主,阳信公主不禁有些佩服。在刘启的厉声追问下,她无所畏惧地抬起头来:“是的,我刚刚经过明台公主那里,看见了她红肿的双眼,和绝望的表情。她的奉车校尉守在宫门外,递进来一封信,信上写着两句饱含着痛苦的话,父皇,你想听吗?”
“你说。”
“将相无计,弱女蒙羞。”
“放肆!”刘启不禁勃然大怒,竟有人敢这样指责和侮蔑汉家四代相传的大政方针!他的愚蠢和放肆令人不可原宥!“派人去查查那人到底是谁!”
“可是,父皇,我觉得,这八个字应该改一改才合适。”
“怎么改?”刘启冷眼看着这个最为机巧百出的女儿。
“君臣无计,汉室蒙羞。”
“阳信,你被宠坏了!”刘启“啪”的一声,掷下了手中的狼毫笔,墨汁在红砖地上四溅开来。
娇小的穿着大红锦袄的阳信公主,却向前走了一步,朗声道:“父皇,你为什么总是不肯正视这七十年未解的边患?”
她白皙的脸庞高高地抬了起来,流露出无法克制的愤懑:“匈奴寄来的国书上,抬头永远写着‘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致汉皇刘氏’,无礼已极!连这一回的求婚书上,也分明写着这句极为傲慢轻藐的致辞!父皇,难道您不觉得屈辱吗?”
阳信公主明净的眼睛里陡然浮上来一层抑郁,她的话语并不像是个孩子所说的:“孝文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老上单于带领全族人马,攻入朝那、萧关,掳走大量百姓和牛马,他难道不是大汉的女婿?老上单于年年扰边,他的儿子军臣单于在先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61年)继承了胡酋的位置,登基第四年,再次重复他父亲的战绩,分兵两路,由上郡和云中攻入关内,烽火一直烧到了长安城!父皇,你认真想一想,为什么高祖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三世,四十多年中,只有三个公主嫁到匈奴去,而父皇你登基不过五年,就已经将两个公主嫁作了匈奴人的新娘?还陪嫁了不计其数的丝绸、牛羊、金银铜器?是匈奴人的胃口越来越大了,还是朝廷的胆量越来越小了?正像晁错当年所说,匈奴入侵,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我们大汉士卒久安不战,畏敌如虎,已经成了匈奴人狼吻下的羔羊,他们每年劫掠所得,比和亲所得多好几倍,所以绝不会因为与大汉结下兄弟之盟、姻亲之好,就轻易放弃扰边与侵略。更何况,如果和平的代价是这种朝贡似的和亲,女儿以为,这种和平不可能长久。”
刘启怔住了,他从未考虑到这么多。多年来,内忧外患交相煎迫,让他一直认为,和亲才是抚平边患的最佳手段,而阳信这些幼稚而坦率的指责,却让身居高位多年的刘启一刹那间看清了汉匈和亲的真相。
没错,这种卑躬屈膝的和亲,就是朝贡,是媾和,是投降。
刘启登基不到四年时间,军臣单于先后两次求婚大汉,他几乎每年都要准备大量的回赐、嫁妆、贡礼给龙城的大汉女婿、外甥,他这个匈奴人的舅舅,也实在有点架不住如此无度的勒索了。
刘启用手托着额头,痛苦地听着这些朝臣们不可能当面相告的直率话语,良久,他才挥了挥手,道:“阳信,你去吧,父皇……会认真想一想你的话。”
“请恕女儿直言的过错。”阳信这才敛了敛衣裾,声音变得轻柔,“因为女儿一直以为,和平,不等于妥协;晏武,不等于软弱。汉家的军队,应该一直保持强大,才能给天下老百姓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
“阳信,你这孩子……只有十一岁吧,怎么会想这么多?连你的哥哥们也比不上。”刘启仔细地打量了她一眼。
从前,他只觉得女儿美丽大方、性格强悍,却没有发现她相当有见识。和亲,是几十年前汉高祖亲自定下的体制,四代皇帝都沿袭着旧制,与匈奴人保持着表面的和平,却没有人深入地想一想这北方边患的根本利害。
经女儿这么一说,他忽然想起了一件往事。
当年,匈奴汗国的一代开国帝王冒顿单于死后,他儿子老上单于继位。汉文帝按惯例将亲王的女儿嫁给他,并派了宦官中行说做公主的终身顾问,中行说不愿意一辈子待在艰苦的北方,坚决推辞,汉文帝只得采用武力强迫他去。临行前,中行说向送行的人含恨发誓:“既然把我流放到野蛮人那里,我一定要利用匈奴的力量来报仇。”
怀恨在心的中行说,到达匈奴后便归降了老上单于。他是个富有才智的人,未开化的蛮族得到他的力量,变得异常强大。中行说教大臣和贵族们学习书写、计算以及一些政治智慧,并利用单于的力量,给汉文帝寄去无礼的信件,口气十分傲慢。
就在十三年前,中行说还发动了十四万大军攻入长城,烧了皇帝的一处行宫,杀了边关守将,一直打到距长安一百多公里的地方。
此后,中行说将这种袭击变成每年的惯例,他们进入长城后抢劫杀掠一番便闪电般地撤离,令汉文帝头疼不已。
汉文帝唯有再次与匈奴和亲,他打算嫁一个公主给老上单于的太子,老上得到婚约后停止了袭击。订约四年后老上单于病故,新继位的军臣单于在中行说的劝说下,撕毁了婚约,再次发动了对大汉的频繁袭击,因此之故,汉文帝不得不在北方设了三个关防,派重兵把守。五年前,汉文帝病故,刘启登基,他派使者到匈奴去,好不容易才设法恢复了婚约。
缔约之时,刘启还曾庆幸过,他终于能够与匈奴保持一定时期的和平,好腾出手来对付国内势力越来越强大的藩王和宗室。而现在看来,匈奴人的胃口未免太大了,四年间,他们前后娶了两个大汉公主,并要求着越来越丰盛的嫁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