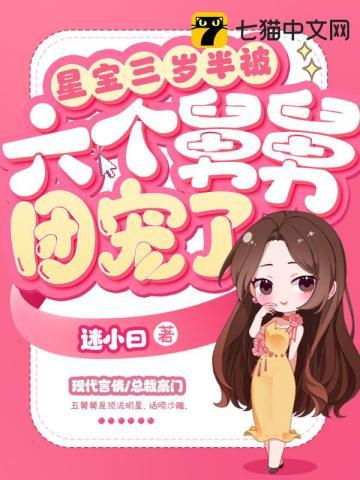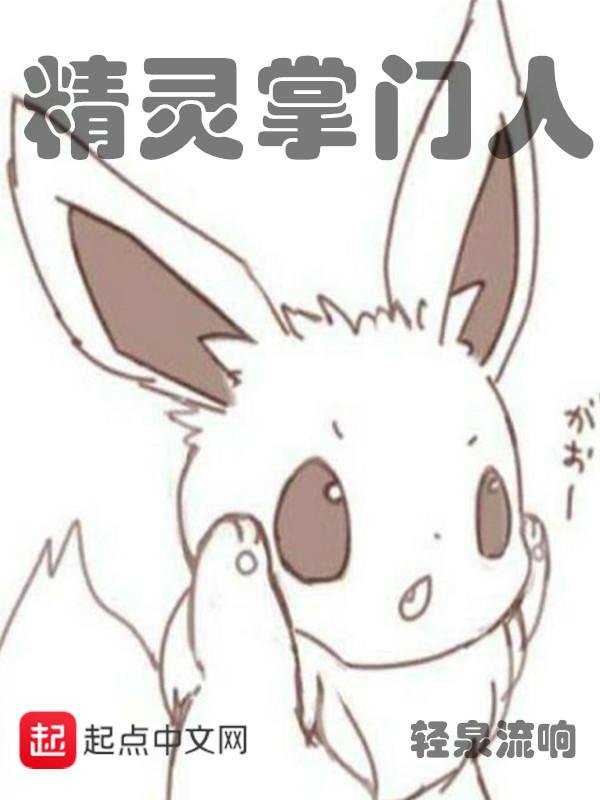奇书网>棠棣王朝讲的是什么 > 第22章 传国玉玺(第4页)
第22章 传国玉玺(第4页)
李存勖并不信佛,只是他的王妃刘玉娘因为感恩身世际遇,长期以重金供奉河东寺院,所以宫中僧尼出入不断,他对僧尼也另眼相看,见此异景,纳闷地问道:“大师是哪里的高僧,怎么识得本王?”
那僧人道:“贫僧是河北人,少年时在长安城大慈恩寺发愿出家为僧,师从方丈圆净。我师父十五年前坐化时,传给贫僧一个木盒,说是当年黄巢在大慈恩寺被擒获时所遗。后来长安被焚,贫僧四海飘零,挂单河中同州寺院。三年之前,这木盒夜里华焰闪闪、光照十里,同州大唐皇陵也迭见异象,贫僧打开此盒,有告老还乡的官员识得,盒中是当年和氏璧所刻的五龙传国玉玺……”
郭从谦走上前,惊喜地问道:“你便是传真?我与刘娘娘数次派人前去找你,却均无功而返,你如何却出现在这里?”
传真微微一笑,指着地下的大蟒道:“这几条大蟒,为睿宗皇帝桥陵、玄宗皇帝泰陵、宪宗皇帝景陵上的护陵巨蟒,出入之时,群蛇相随。去年贫僧行脚之时,发现蛇踪不断,似乎在引着贫僧向河东一带潜行,贫僧一路跟随蛇踪,终于见到了殿下……殿下,这是天意!这是大唐先皇们地下有灵,指点贫僧前来找到殿下!”
似乎是要赞同传真所言,数条大蟒同时点头向李存勖叩拜,竟似深通人性。
李存勖如坠梦中,似醒非醒。
如果说是梦,可眼前的大蟒与传真手中的玉玺分明历历在目,如果说不是梦,可这闻所未闻的神迹,让他一时不敢相信。
难道说他李存勖真的上应天时、下顺民心?
自五岁时起,众人皆赞他仪表非凡、天纵英才,可他以为那是众人要巴结奉承他父王;十岁入宫,昭宗皇帝亲赐他“亚子”之名,称他强爷胜祖,可他以为那是皇上要拉拢取悦他父王;这些年,他南征北战,战无不胜,从孤城绝地的晋阳起家,反败为胜,一举而得河朔、河中,可他以为那都是七哥、亚父与义兄们的鼎力相助……难道,就没有几分可能,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天命所归,本来就是重新扶起这大唐江山的中兴之主?
李存勖恍惚地望着面前慷慨陈辞的传真和尚与满心欢喜的郭从谦,心中没有太多的喜悦,更多的却是自我质疑与震惊。
书案上,五龙玉玺在简朴的木匣里闪着淡青色的莹光,螭钮上五龙相交,方正的玺印边镶着金边,遮住了一角残缺。
张承业颤巍巍地伸出手去,轻轻拿起玉玺,在印泥上轻沾一下,在一旁放着的白色宣纸上轻按,起印之后,纸面上赫然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李斯体鱼虫篆字。
张承业细细打量一番,轻轻放下印玺,跪地再拜,泣道:“没错,殿下,这正是我大唐皇帝的传国玉玺,当年长安光复之际,遗失于黄巢乱军,不想今日老奴还能复见此玺,我大唐河山恢复有日!殿下父子两度光复我大唐,诚为国家柱石!”
张承业预料得有道理,如今大梁早不是当年兵强马壮的大梁了,朱友贞左支右绌,但求自保。南方的吴越等自立已久的藩镇,看出晋王李存勖势不可当,均上表递交国书,愿称唐臣。大唐河山的恢复之日,已经不远了。
李存勖没有回答张承业的这番颂功之辞,他扫视了一眼殿外的银杏树,清荫之下,是刘玉娘这些年种下的牡丹。
四月,牡丹开得正好,到处一片金紫,霸府门前,遍地都是深红色、粉白色、鹅黄色、墨蓝色的牡丹花树,暮色渐渐深沉,牡丹奇丽的颜色却越发突显。
今年的花势,似乎比哪一年都旺。
这象征着李唐国运的奇花,在北都晋阳,开放得也一样兴旺。
远处,传来伶人的清唱声,是李存勖不久前刚刚填词的《水调歌头》,檀板渐起,琵琶的弦音变得繁密,戏子们的声音如谷底长风般清越动人:
赏芳春,暖风飘箔。莺啼绿树,轻烟笼晚阁。杏桃红,开繁萼。灵和殿,禁柳千行斜,金丝络。夏云多,奇峰如削。纨扇动微凉,轻绡薄,梅雨霁,火云烁。临水槛,永日逃繁暑,泛觥酌。
露华浓,冷高梧,凋万叶。一霎晚风,蝉声新雨歇。惜惜此光阴,如流水。东篱菊残时,叹萧索。繁阴积,岁时暮,景难留。不觉朱颜失却,好容光。且且须呼宾友,西园长宵。宴云谣,歌皓齿,且行乐。
暮色已浓,殿外,一种深蓝色的夜影弥漫开来,吞没了树丛与花园,令他心生忧凉。
父王气病而死,恋人断情出塞,十年河朔征杀,他得到的,就只能是“国家柱石”的虚誉、“光复功臣”的令名?
这江山、这城池,是他二十年来衣不解甲,手持禹王槊,舍生忘死、百战夺来,他为什么要甘心让给别人?让给一个来历不明的所谓大唐皇子?
李存勖沉默半晌,这才双手扶起了张承业,道:“七哥,孤十几年前承先王复唐遗志,励精图治,得有今日,不负先王与七哥之望。如今德胜南城深入大梁腹心,破梁只在朝夕之间,可是七哥,孤只想问一句,这复唐之日、定鼎之时,当以谁为大唐天子?孤受先王之教,承爵十几年来,不敢擅称帝号,至今在晋阳城奉大唐年号,可这河东军浴血十几年夺回的大唐社稷,到底该奉谁为主?还请七哥赐教!”
张承业听出他的话语有几分咄咄逼人,含泪道:“殿下浴血百战,着实辛苦不易。可殿下既受先帝赐姓,世食唐禄,便应尽忠国事。昭宗皇帝血脉胡昌翼,仍在徽州,有多位前朝老臣之言为证,不能算是来历不明。唐祚之亡,人神共愤,殿下,你起兵之际,打的是匡复唐室的旗号,天下归心,所以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倘若毕功之日,却……却贪恋权位,违背初心,先王在九泉之下也难心安……”
李存勖紧皱眉头,不悦地道:“七哥,孤受大唐皇帝赐给国姓,于今三世,难道还算不上大唐子孙?更何况玉玺之验,巨蟒之兆,众人有目共睹。倘若这大唐国运,真验在昭宗皇帝的后人身上,为何护陵巨蟒没有现身徽州?为何当年昭宗皇帝即位时,传国玉玺却迟迟没有现身?”
张承业惊讶地望着李存勖,这才看出李存勖心中称帝的决心早已坚不可摧,他正在不停地为自己寻找祥瑞和理由。
“殿下,这祥瑞之事,不可深信,老臣只怕……只怕这和尚与郭从谦、刘娘娘早有往来,暗中布置了群蟒朝拜的骗局。殿下须知道,自古至今,送呈皇帝面前的祥瑞多是官员们肆意编造出来、用以邀功请赏……”
“祥瑞可以编造,群蟒可以训练,可这传国玉玺,总不是假的!”李存勖不耐烦地打断了他,“七哥,真真假假,是是非非,本来难有公论。唐祚之亡,昭宗皇帝与积善太后死于非命,大唐皇子已经全都被朱晃叛党屠杀,这个所谓流落民间的皇子,又有谁能证明他是真是假?那徽州府的前朝老臣,难道就不可能是为图谋这泼天富贵而暗中布局、精心策划之人吗?”
张承业被他的一番诘问质疑得哑口无言,是啊,谁能断言徽州府的大唐皇子就一定是真的呢?
当年积善太后的确曾在迁都途中产子,可那个皇子是当场夭折还是下落不明了,谁又能确认?徽州府的那个胡姓少年,又能拿什么证实自己的皇子身份、令天下人信服?
“就算是这样,可殿下自幼读史,熟知掌故,当知秦亡之时,项羽入长安后并未曾称帝,而是自号‘西楚霸王’,大封诸侯,这才得百姓拥戴啊!暴秦失政,所以民间流传‘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义军奉楚怀王之孙、牧羊童熊心为新的楚怀王,才能于数载之间集聚义军、灭秦复楚,倘若项羽一心称帝,还能完成灭秦大业吗?”张承业的脸颊边,落下了两行浑浊老泪,“这复楚的旗号,项羽扛了一辈子,用了一辈子,所以他不敢称帝、不能称帝,不然的话,他在天下百姓的心中便不再是灭秦的英雄,而成了贪权的奸雄……老臣看着殿下自幼长大,但愿殿下爱惜羽毛名声,勿为眼前的名利所累!”
他今年七十五岁,来到河东二十五载,出长安大明宫之际,昭宗皇帝对他的嘱咐言犹在耳,他前来河东,是为大唐留一条后路,可如今大唐何在?河东军势不可当,梁军已经风雨飘摇,然而他的大唐真的恢复有望吗?